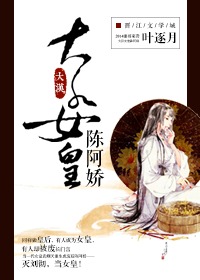大汉歌姬-第11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今天两更。
我喜欢这错觉,我喜欢这“冥冥中另有一股力量操纵”的假想,我喜欢古代人把一切不可思议归之于神明的习惯。
为什么圣旨会无缘无故灼伤了李末的手?为什么圣旨会无缘无故燃起那样奇怪颜色的火?为什么那火没有烧了圣旨,却仅仅是烧没了上面的字?
要想通这些并不困难,只一个可能。
那是神明在阻止,阻止我被册立为皇后。
为什么神明要阻止?我不是上苍钦定、凤自天降的廉子服吗?我既是凤凰托世投生,为何神明却不让我做皇后?
要解释这一点,也不困难。
廉子服是凤凰托生不假,但她却只得凤身,不具凤命。她得了凤身,故此会现五色霞彩,化生死劫难。可她没有那个凤命,所以她永远做不了皇后。她的存在,是上天赐给大汉朝的祥瑞,她只能是廉子服,独立的超然的,她沾不得世俗。皇后属于世俗,不过母仪天下,而廉子服却属于天下,以己之凤身,庇佑苍生。
为司马洛爱上的我,为司马洛深爱的我,为司马洛深爱到至死不渝的我,怎么可能只是悲哀地束手认命,抑或愚蠢地以死相抗?司马洛布的局,只有我能破解。这就是我的破解之法,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就像汉宣帝当初在祭天大典上的布置,就像司马洛于临华殿外的“霞光凤鸣”,所有这些看似不合常理的现象背后,自然有构成它发生的合乎常理的前提与策划。
为什么圣旨上会没了字迹?很简单,因为装有立后诏书的木盒被人调换了,调换后的木盒里,放着的本就是张空白的圣旨。如果李末没有灼伤手掌,没有扔了布帛,没有后来那蓝绿的火,打开来,那圣旨本就该是一片空白。
然而,李末灼伤,圣旨扔了,火起了,一切便水到渠成。看似神灵操控,其实始作俑者,非人,非神,只是一种形似于白蜡的化学物质。
欧洲中世纪,人们为炼金而疯狂。1669年,德国汉堡一位叫布朗特的商人在强热蒸发人尿时,虽然没有制得黄金,却意外地得到一种像白蜡一样的物质,在黑暗的小屋里闪闪发光。这物质暴露在空气中,久而久之,便会燃起神奇的蓝绿色火光,那绿火不会发热,不会引燃其它物质,是一种冷光。于是,他就以“冷光”的意思命名这种新发现的物质,叫做“磷”。
布朗特发现的,便是现代极为普遍的,白磷,世上燃点最低的物质,仅为40摄氏度。
尽管眼下还在正月,气温不过零上几度,却并不意味着白磷就不会燃烧。摩擦或缓慢氧化,包括人的手温,都有可能使它的局部温度达到燃点而起火。
我要求太皇太后召那炼金术士进宫,就是为了得到他的协助,助我从人的尿液中提炼白磷。只要掌握好白磷在空气中氧化达到燃烧所需要的时间,按照这时间将其均匀洒在那空白的圣旨上,偷梁换柱。
当李末展开圣旨时,接触到白磷颗粒,他的手温,便使白磷燃烧,他自然被灼伤。灼痛的本能反应,他自然会扔了手里的东西。然后,白磷达到燃点,绿火初现。而用作圣旨的布帛,它的燃点,远远高于白磷,所以当白磷燃尽生成氧化物,圣旨仍然完好无损。
说起来很容易,其中却是艰辛无数。那尿液蒸发时恶心的气味,白磷本身的剧毒和它动辄燃烧的危险 3ǔωω。cōm性,如何把握最佳的调换时机,让它在我需要它燃烧的时候燃烧,我忍了太多我不能忍受的苦,我经历了太多太多次的失败。
总算皇天不负有心人,这些苦,这些失败,到底换来了立后之典上那一幕的精彩绝伦。事后想想,也有些侥幸,倘若我不是从小就对化学很感兴趣,倘若中间随便哪个环节出了差错,结果会怎样?我不愿去设想。
好在,这一次,我不愿去设想的,老天也没有多此一举地替我去设想。一旦最难做到的,做到了,接下来的事情便是轻而易举。只要随便找个人,把那“有凤命、无凤身”的谣言传了出去,一传十、十传百,谣言便和上几回一样,变成了无法推翻的真理,就算真龙天子也不能将其推翻。
所以,我这一辈子都当不成皇后了,除非汉宣帝不顾神明不顾民心,执意逆天而为。可我知道,他不会这么做,一百个廉子服加起来,也不会令他做出一丝一毫可能会动摇江山社稷的举动。他是个英明的君主,英明的君主,向来是将大局放在首位,至于其它,即使是自己的意志,也只能屈居第二。
(注:觉得在这里有必要交代一下历史背景。两汉之时,盛行谶言。所谓谶言,那是一种类似于宗教的神学,某种有待应验的预言、隐语。在很多时候,它为动荡时事的政治角逐提供了一种便捷有效的舆论工具。比如,汉宣帝的前任,汉昭帝还在世时,因为他身体虚弱、膝下无子,于是在昭帝元凤三年(前78年)正月,传说泰山莱芜山南有数千人看见有块高1丈5尺,长48围的巨石,忽然自己竖立起来,插进地里8尺,下边还有3块小石为足。又传说,皇家上林苑中,有棵大柳树倒地枯死,又自己站起来复活了,上面还有小虫咬食树叶而成的文字:“公孙病已立。”这些传说,到底是真是假,自西汉至今,一直存在争议。但霍光之所以会扶持汉宣帝刘病已登基,这也算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所以我个人认为,由此可知,当时的人们,对那些荒诞的传说在很大程度上是深信不疑的。也有很多人,很自然地就会想到利用这些传说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也是我,一连四次设计像本章这种情节的灵感所在。之所以啰嗦这一段,也是想跟不清楚这段历史的亲们,分享一下。其实历史深究下去,真的很有意思。)
今天两更结束。汗,现在看看,真有点像在变魔术
我想,在汉宣帝的心里,应该是对我有所怀疑的。当李末将那张空白的圣旨对向了他,他立时便将目光朝向了我。
可他虽然怀疑我,却又不能完全相信自己的怀疑。毕竟,他亲眼所见,这一切实在匪夷所思,倘若真是我主导,那么他就不得不把我和“邪术”划上等号了。
第二天的晚上,汉宣帝驾临常宁殿,或者,在外人口里,在宫人内侍的口里,应该叫做“驾幸”才是。他摆出的阵仗,是要夜宿,夜宿在常宁殿我的寝室
我跪地接驾,本当慌张,却奇怪的平静。
汉宣帝赐我免礼,本当试探,甚而疑恼,可他却也是奇怪的平静。
我们两个人的平静,交汇出的,是相对无言。
宫人退出,关门声,响在这平静里,终于打破了这平静。
汉宣帝开口,话语里透出的,竟是过了承载极限的疲累。“子服心中,应当很欢喜吧?子服怕是古往今来,第一个因当不了皇后,而欢喜的女子。”
疲累的汉宣帝,是我的软肋。选择着措词,最委婉的措词,“陛下,事已至此,子服欢不欢喜已不重要。”
“重要?”宣帝抬头看我,那对眸子,是飘浮在云里的月,颤颤巍巍的,仿佛随时会跌下云头,跌落人间。也许他是很想跌落人间的,化作一片湖,如果我愿意做那湖心的一朵清莲。
“不知子服信或不信,朕便如同做了一场梦,总是害怕梦醒,到此刻梦醒了,朕反倒轻松了。”
“陛下,”
我唤他,他却打断我,走近我,他伸手,触着我发鬓,他把那闪烁的眸光流连在我的发鬓,却不去接触我的眼神。
“子服,朕轻松,却不甘心。朕不甘心,这当真是天意么?难道不是,有人蓄意而为?倘是蓄意而为,那么普天之下,有这等智谋心机的,非子服莫属。子服,朕便是输也要输个明白,你告诉朕,你是怎样做到的?你在诏书上,究竟动了什么手脚?”
如果,不听那内容,单是这口吻里的温存,你会以为,他是在对我说着情话,不需要动听的句子,只是这语气,这声调,便是让人沦陷真心最好的武器。
只可惜,我已无真心可沦陷,我听得出,这温存后面,那故意的示弱,以及诱供的企图。
“陛下抬举子服了,陛下当真以为子服会妖术么?陛下当真以为子服能瞒天过海,愚弄圣听么?陛下问的,未免可笑。”
温存在瞬间僵硬,然后,我感觉到了头皮拉扯的疼痛,却是汉宣帝扯下了我束发的簪子,扯散了那样式繁冗的发髻,长及腰间的头发如瀑布披泻开来。
不知道为什么,有一刹那,就好像战场上叫人夺去了盾牌的士兵,长发披肩的我,面对着汉宣帝,竟生出几分女人面对男人的软弱。
这种软弱,令宣帝脸上,那征服的保护的欲望,越发地明显。很矛盾,他既要征服我,又要保护我。矛盾交织在一起,却是伤害,抛却所有顾忌的伤害。
他这是打定了主意,宁愿先伤害了我,再来用以后的日子治愈我的伤处。
把玩着我的一缕头发,继而去摩挲我的双肩,那因后倾的衣领而裸露在空气中的皮肤。
“是啊,朕的确可笑,一个做了朕七年夫人的女子,从良人做到婕妤,差一点做了皇后的女子,朕竟从未得到过她。传扬出去,朕怎能不遭天下人耻笑?”
凑向我颈项的唇,柔若春风拂面,揽在我腰际的手臂,却强势而霸道,至于颈侧那呢喃耳语,则是绵里针的冷酷尖利。
“子服,你以为朕当真一无所觉么?你心里存着什么样的想法,动着什么样的脑筋,朕比你自己还要清楚。朕虽然想不通你究竟使了何种手段,但朕可以肯定昨日的变故定然与你有关。廉子服,你尽管赢了朕这一次,可你别忘了,你依然是朕的婕妤。你既是朕的婕妤,那么朕便可以宠幸你,你就必须侍候朕!”
第二更会在中午上传。今天会追加一更。
那嘴唇的触感,臂膀的禁锢,贴合的身体,耳畔的声音,每一样都真实得不能再真实,却偏偏不能挑起我真实的反应。也许我同样过于疲累了,疲累的躯壳圈不住散漫的灵魂,魂魄已脱体而出,飞向那高处,司马洛口里“比翼天高”的高处。
“就是今夜陛下得到了,也和以往没什么区别。陛下能得到的,本是陛下不屑用强得到的;陛下想得到的,将是陛下用尽了心也永远不能得到的。”
我早就看出,在汉宣帝的心里,有一条底线,一条道义上的人格上的底线。不管爱恨将他如何扭曲,却始终不能扭曲他本性中的那份磊落。这可能就是我,一而再,再而三,吃定他的原因。今晚也不例外。
如我所料,汉宣帝立刻推开了我,甚至是带着嫌弃的,嫌弃的,也许是我,也许是他自己。
他把我推得老远老远,像是要把我推离他的世界,推离他的记忆,他后退着,我又一次在他清秀的面部轮廓上刻下了刀痕,他无意识地退到床边,绊了一下,顺势跌坐在床上,颤着那刀痕。没了征服,没了保护,唯有伤害。
“廉子服,朕,给了你最后的机会。你既不肯珍惜,便是你自作自受。如此,你就准备孤寂一生,老死在这未央宫里吧!”
他伤害我,我却要弥补他。我走向他,一步一步,他却因我的靠近而厌恶,厌恶地倒头就睡,睡在那枕上,面朝里,将脊背决绝着,隔离了我。
我不在乎他的隔离、他的决绝,我只想了结,了结他的爱恨,对我的爱恨。
走到床前,我跪着,我知道他就算看不见,也会感觉得到,我是在跪着。
跪着向那决绝的脊背说:“陛下得不到的,子服何尝能得到?子服想得到的,也是永永远远都不能得到了。倘是陛下认为子服辜负了背叛了皇恩,子服也已经付出了代价,孤寂一生、老死皇宫的代价。陛下就算得不到子服,但子服这辈子陪着的,就只有陛下而已。”
决绝的背,松垮下来。或者,这松垮里,还有失望的成份,或者他是在用厌恶隐藏他的期盼,期盼我会在最后回心转意,走过来乞求他原谅,抱住他,与他同衾而眠,与他共枕鸳梦。
大概吧,这是我第几次,让他失望了。记不清,数不过来了。
然而,从今往后,我却能百分百地笃定,他是不会再存有任何幻想了。这是我从他的背影里,解读出的讯息,一如我的初衷。他终于对我死了心,他想要的,我没能给他,但是我却给了他平衡。得到平衡的他,应该不会再把谁当作我的替罪羔羊了吧,从此不会有谁再被我连累。
结束了,一切都结束了,这就是结局吗?望向窗外,窗外,无星无月,黑到辨不出蓝的天空。
“陛下,恐怕还未曾想到,自今日起,陛下是不能宠幸子服的。子服已非陛下的夫人如此简单。有凤身无凤命,这样的女子,倘若怀有陛下的子嗣,倘若诞下陛下的子嗣,太子该如何自处?只怕储君之位,从此纷争不断。”
不错,这就是结局。我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