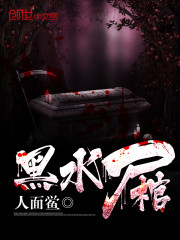黑水尸棺-第4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就看见我师父在坩埚里倒上了一些水,点上火,趁着坩埚里的水还没沸起来,我师父又从橱柜里拎出一个铛子。
第五十八章 尸油、蓍草、尸蜡
铛子,在南方可能少见一些。这东西在我们那又叫作鏊子,摊饼用的,形状就是一个黑色的厚铁饼,上面微微隆起,很多摊煎饼果子的也是用它来做饼,只不过他们的鏊子,顶面大多是水平的。
之后师父又拿来一个黄白色的蜡块,对我说了声:“尸蜡。”
师父家一直没通煤气,烧得是木炭,当时厨房里的木炭不多了,师父就让我和梁厚载出去拿一些回来。
点上柴,烤热了铛子,师父就将尸蜡一点一点抹在铛子上,又在尸蜡中添了些水。
受到鏊子的灼烤,上面那些混着水的尸蜡很快变成了一张薄薄的油纸,我师父将整张油纸揭下来,又从我这边拿走青钢剑,将它切割成一个一个的小方块。
看着那些切割后的方形油纸,我突然觉得很眼熟。
就听我师父对我说:“你记住了,摊油纸的时候,鏊子不要太热,不然很容易糊了。尸蜡和水的比例是一比三。”
我点了点头,可还是想不明白师父到底在干什么。
这时坩埚里的水已经沸,师父将一滴铜甲尸的尸油滴进去,又拿起一根蓍草,也放进了坩埚里。炉灶上的坩埚总共有三个,第一个坩埚里只放了一根蓍草,第二个放了三根,第三个我师父直接抓了一大把放了进去,每一个坩埚里,都滴进了一滴尸油。
师父一边晃动着那些坩埚,一边对我说:“放一根蓍草,是用来稳固阳气,放三根,可以补充阳气,放进十二根,则可以让阳气勃发、再生。”
我一直盯着那些坩埚看,就看见蓍草碰到尸油以后,竟然在一瞬间就融化了,刚开始,草汁把沸水染成了淡绿色,可没多久,绿色散去,竟然显现出一种很新鲜的奶白色。
梁厚载凑到我耳朵边上,悄悄对我说:“道哥,我突然有种特别不好的预感。”
其实不用他说,我大概也猜出来我师父在干什么了。
这时我还听见仙儿在笑,她那笑声,好像是为了什么事在幸灾乐祸。
坩埚里的水汽蒸发以后,里面就生下来了一下奶色的、黏糊糊的东西,我师父把三个坩埚里的东西倒进粗口坛子里,等它们冷却下来,变得稍微硬实一些了,又用木槌不断地打。
没多久,它们就被我师父砸成了四四方方的奶块,然后我师父又用油纸把这些糖块依次包了起来。
奶糖,这就是我师父经常给我吃的奶糖!里面竟然有尸油!那些油纸竟然是用尸蜡做的!
小时候我吃完糖,还竟然把那些油纸咬在嘴里玩。我的天哪,好恶心!
可我师父好像一点都不觉得恶心,一边包着糖纸,还一边对我说:“屯蒙这一脉做出来的蓍草本来是筮卜用的,分阴蓍和阳蓍,这些是阳蓍,上面的阳气太重,不能直接吃,要用尸油来调和。过去你吃糖的时候觉得苦,其实是蓍草的阳气汇入丹田,那时候你尝到的是蓍草的苦。在你阳气过剩的时候,尸油的阴气进入气海,你尝到的那股甜味,就来自这些尸油。”
我的个天,这些奶糖里的香甜,竟然是尸油的味道!当时我就有种冲动,恨不得把这些年吃的糖,全都吐出来。
梁厚载也吃过我师父的糖,他现在的脸色,也是铁青铁青的。
说实话,我想很多人可能不能理解我和梁厚载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反应,毕竟邪尸身上的那股味道,也不是每个人都闻过的。
可我师父没看到我们两个的表情,还在继续说着:“之所以用尸油来配蓍草,就是因为这两种东西不会破坏对方的所带的炁。这些蓍草还能祛除尸气,只留下尸油中的阴气。”
说着说着,我师父又回想起了过去发生的一些事情,竟然笑了起来:“第一次碰到你和胖墩那天,我给胖墩的就是一块普通的奶糖。还有你种棺那天,给你吃的不是这种糖块,是尸丹……”
我实在是听不下去了,忍不住打断我师父:“师父,你先别说了。”
尸丹是什么东西我还是很清楚的,那玩意儿比尸蜡、尸油恶心多了。
我师父转过头来看我,才看到我和梁厚载的表情,可他依然笑着说:“你们可不要觉得这尸油脏,去掉尸气以后,邪尸的尸油和尸蜡,可是这天底下最干净的东西。”
师父说这些话的时候,我就忍不住开始干呕了。
仙儿却露出头来,不怀好意地朝着我笑,看样子她早就知道那些糖是用什么做的,可既然知道,为什么不告诉我?
有时候吧,我真的觉得仙儿挺惹人厌的,真的!
我师父把做好的糖放在口袋里,又对我说:“做糖的手法,你要牢牢记住,以后你收了徒弟,也要一代代把这门手艺传下去。还有厚载,你们那一脉的传人,往往是阴气过重,阳气不足,这门手艺我今天也交给你了,你要好好记着。”
梁厚载的脸色不好看,但还是很认真地点了点头,之后他缓了缓,才又说道:“可是柴爷爷,尸蜡这东西,不是很难收集的吗,尤其是这种纯净的尸蜡。可你刚才拿出来的那一块……”
说到这里,梁厚载似乎又想起了那块尸蜡的样子,于是就说不下去了。
我师父还是笑呵呵的:“正好了,今天晚上我要去乱坟山收一些尸蜡,你们就跟着一起去吧。”
说完,我师父又朝着客厅的方向喊:“老陈来了吗?”
就听见客厅里传来了陈道长的声音:“嗯。”
他是什么时候来的,我怎么一点都没察觉到?
就在陈道长回应我师父的时候,从客厅方向还飘来了一股淡淡的烟草味。
我师父也闻到了味道,脸上的表情立即变得紧张起来,赶紧跑了出去。
我跟着师父来到客厅的时候,就看见陈道长正抱着我师父的旱烟,小口小口地抽着,还一脸享受的样子。
我师父冲过去,伸手就抓住了烟杆,很不爽地朝陈道长吼:“老东西,又偷我烟!”
陈道长也攥住了烟杆了另一头,同样很不爽地说:“你个老柴头,我不就是抽你口烟吗,哎呀,你看看你那个小气样!”
陈道长的力气显然没我师父大,我师父只是用力一拉,就把烟杆抢了过来,陈道长就眼巴巴地看着我师父的烟杆,一脸的不情愿。
看他们两个那样子,我也真是无语了,就跟两个小孩抢玩具似的。
我师父又问陈道长:“东西你准备好了吗?”
陈道长没回应我师父的话,只是反问:“三尸诀的抄本,你什么时候给我?”
我师父指了指茶几:“你眼白长了,这是什么?”
当时三尸诀的手抄本,就放在那个茶几上。
可陈道长看了三尸诀一眼,却没伸手去拿,反而还在说:“那个么,你先把烟杆给我。”
我师父干脆把烟锅灭了,又问他:“东西准备好了吗?”
谁知陈道长竟然威胁起了我师父:“你给我烟杆,我就准备好了,你要是不给我,自己看着办吧。”
我师父也是被他弄得没脾气了,很无奈地把烟杆递给了他,这下陈道长才高兴了,从怀里掏出一把灵符,说:“三十张符,给你。”
看我师父和陈道长,两人的关系似乎非比寻常,虽然也说不上来这种关系是好还是不好,总之就是不一般。
可有件事我一直觉得奇怪,那就是我师父几乎从来不会主动提起陈道长的事情,有时候就算我问起来,我师父也是打打马虎眼就过去了。
可有时候,我说起陈道长脸皮厚的时候,我师父却会狠狠瞪我一眼,每次都会说:“你懂什么,陈道长就是这样的人,不拘小节。”偶尔我师父也会说,其实陈道长才是一个有大慈悲心的人。
以至于在那段时间,我一直都对陈道长充满了好奇,总感觉他现在的样子,似乎是刻意表现出来的,在他身上,说不定也是有很多隐秘的。
那天,陈道长又问我师父要了一小袋烟叶,才乐呵呵地跟着我们一起去了王庄。
从我住的地方到王庄,还是有一段距离的,到村口的时候天色已经快要黑下来了。
我师父看了看表,却说时间还早,就问附近的乡亲要了点蔬菜和猪肉,在乱坟山的小房子里做起了饭。
其实我本来是想去看看我大舅的,可我大舅去了外地,这会家里没人。
我记得那段时间,村里好像是在搞有机蔬菜出口,我大舅虽然腿脚不好,可因为小时候在金行做过帮工,眼皮子活泛,也擅长和人打交道。刚开始,村里的做的出口生意,都是我大舅和村里的干部一起去谈,大舅也因为这些生意赚了点钱,后来干脆自己包了几块地,又雇了几个工人,做起了自产自销的买卖,日子渐渐富了起来。
我师父说,我大舅能富起来,还是因为我们家破财。当初我们家的财运虽然被挡了,可这一路财运,原本是行大运,虽然被挡了,可最终还是要惠及亲人,于是这道财路就落在了我大舅头上。
第五十九章 阴脉
前几天大舅临出差钱还给我妈打了电话,问我妈要不要带东西回来,也正因为这,我才知道大舅当时不在家。
吃过饭之后,我师父和陈道长就开始不停地看表,我和梁厚载无聊得要命,还要为做作业的事担心。来王庄的时候,我们两个走得急,都没带书包。
我就试探着问我师父:“师父,咱们什么时候完事啊?我作业还没写呢。”
我师父一听,就知道我在想什么,他先是“哼”了一声,之后又说:“今天不用做了。”
听到我师父的话,我心里就乐了,可脸上却不敢笑出来,我回头看了眼梁厚载,他也是面无表情,不过我知道,他心里肯定也乐开花了。
那时候的我和梁厚载,说不上厌学,可就是不愿意做作业,我们两个对作业这种东西,好像都有种与生俱来的反感。
我也是回想起那一段时光,才明白,其实这样的反感,肯定不会是天生的。想想我们两个,每天连一丁点空余的时间都没有,练功、上课、作业、练功,每天的时间都被我师父安排得满满的,换成是谁,多少也会吃不消的。
可即便是这样,在长大以后,偶尔还是会缅怀那时候的日子。
直到土房里的老挂钟敲响了九点的钟声,陈道长才对我师父说:“亥时了。”
我师父点了点头,从桌子上拿了一个空玻璃瓶,又来到土炕前,抓着炕头用力一掀,整张床板竟然被我师父掀了起来。
要知道,土炕这东西,大多都是一体成型的,可我师父家炕,上面的水泥板竟然是盖上去的。我也是这时候才意识到,师父家的土炕之所以一直都没通炉子,是因为这样的炕,是没办法烧热的。
我满心好奇地跑过去看,就看见床板下面,是一条黑乎乎的暗道,暗道里的石阶有些都已经残破,显然已经有些年头了。
从这条暗道的伸出,还不时传来轻微的流水声,下面似乎有一条河脉。
陈道长一边迈开腿,走进暗道,一边对我和梁厚载说:“这地方,过去是个古墓的入口,荒废很多年了。”
他说话的时候,在暗道里还响起一阵悠远的回声。
我师父让我和梁厚载先进去,他则走在最后面。
进了暗道之后,流水声就变得清晰起来,潮湿的凉气迎面而来,让我忍不住打了一个冷战。
师父将托着床板,将它重新盖严实了,才走过来,拍拍我的后背,说:“扣上扣子,小心别着凉。”
我这才发现自己正敞着怀,赶紧把扣子扣上。
床板被盖上之后,光线先是变得非常暗,可等我的眼睛适应了这种黑暗之后,又能朦胧看到一丝光芒。这些光芒是从周围的石壁上散发出来的,可它们又十微弱,只有在极暗的情况下才能看得到。
走在前面的陈道长敲了敲石壁,叹气道:“过了这么多年,这些夜光石也老得发不出光了。”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语气非常寂落,让我感觉,他好像是在说他自己。
师父拉着我的手,又让我牵好梁厚载,之后就带着我们慢慢向前走着。
暗道很长,大概有一百多米的样子,在暗道的尽头,是一大片湿漉漉的河床,和暗道周围的石壁一样,河床上也不断散发出微弱的幽光,仿若一块无比巨大的璞玉。
而我之所以知道这里是河床,是因为,河脉涌动的声音,就来自这片河床的边界。
我做梦也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