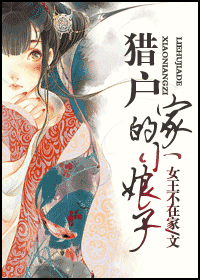地主家的傻儿子-第5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好了,时候不早了,咱们快些回去吧,免得多生是非。”
没等他多想,钱玉已经转了身子,吩咐钱珠,“去扶少奶奶起来,咱们快些入城,否则要赶上禁严了。”
“是。”钱珠忙抹抹泪珠站了起来。
看来少爷还是喜欢少奶奶多些,钱多喜滋滋地想着,又听钱玉道,“回城后去找个鳏夫,给他一笔钱,让他诸如清明此类时节来这边给他们烧烧纸钱。”
“哎!”钱多高兴地应了一声,起身后又朝着淳于敷瞪了一眼。
哼,想当咱们少奶奶,你可做春秋大梦去吧!
淳于敷不在意地笑了一笑,默然随着女眷上了马车。
日头慢慢向西山沉落,一辆马车后跟着牛车也在夕照余晖下,吞然进了青阳城。
作者有话要说: 我要解释,我前几天没更新原因是因为我去亲戚家吃饭吃坏了胃,调理几天才好的,新年了,大家要注意身体啊,另外,晋江新开了个防盗功能,这是晋江系统自带的,不是我放的防盗,我只是利用一下,不要再骂我了。
第72章 第72章
回到宅院时,酉时已过,吩咐厨娘做了些饭菜送到书房内胡乱吃了,又让丫头们将打来烧好的水倒进浴桶里,钱玉便遣散了留在书房侍候的丫头们,关上了房门。
宅院外不时传来老蜩的叫声,在如火的夕阳余晖下,徒添人不少的烦絮。
正是新夏,天有些闷热,又遭遇了这一系列变故,她心里烦躁得紧,出了一身的热汗,难受得她只想跳进浴桶里,再不出来才好。
想着,她解自己衣裳绾带的手便又快了几分,方拉扯下外裳,门外却传来一阵“笃笃”的敲门声。
扯着衣裳的手一顿,“谁?”
“是我,淳于敷。”
淳于敷?这个时辰了,她来做什么?
钱玉皱眉,疑惑间,还是穿好了衣裳,伸手整了一下冠带,淡淡道,“进来。”
“吱呀”一声,门开了,身量高挑的女人拖着长裙慢慢走了进来,带上了门。
她脸上的污垢已经洗清,油灯下,愈发显得她脸上那一道狰狞疤痕可怖非常时,她深邃的五官也不禁使人眼前一亮。确是胡姬貌美遮华盖,妩媚多情倾楼台。
淡淡暼她一眼,钱玉便移开了眼,“你来做什么?”
“公子此话不妥,难道公子买了明珠后,便抛诸脑后,随意丢弃了,却不怕明珠暗投他家么?”
把自己比作明珠,这话未免狂妄。钱玉淡淡看她一眼,“你是怪我不识明珠,还是太过夸耀自己?你们胡人,都是这般不识礼数的?”
“过谦反致损,汉人不解其害,只一味谦让,却是谬之极。家父平时教养文施时,便如此说。”淳于敷大方地一展衣袖,笑了,“公子既留下文施,想必也是做好了安置文施的打算,文施不愿做闲人吃闲饭,致人传些流言蜚语,那文施为何不可先来找公子,让公子告诉文施,留下的条件是什么呢?”
这番话,却伶牙利齿地不似只知舞刀弄剑的胡地生养出女子说的了。钱玉面无表情望她一眼,“文施?”
“这是家父为我取的表字。”淳于敷淡淡一笑,“家父极喜爱汉人文俗,平常看些古籍时,便与家中子弟一一取了字。”
她这一句话倒是点醒了钱玉。乡绅士族间,女子笄而字,字而字,便是及笄后被夫家迎娶过门时,夫君为她取表字,这才算是承认她的主母身分。
说起来,木雪嫁与她也有段时候了,她竟忘了与她商量取字了。
不过,果然胡人常为江表汉人不耻却是无误的,这淳于敷老父僭越为自己女儿取了字不说,她自己这个时辰了,竟还单独敲响男子房门,若是传出去,怕就要被人戳破脊梁骨了。
“本公子已然想妥了,你在府里便充个西席,与夫人做伴之余教她认字,每月例银与府内一等丫头相等,如何?”
“西席先生?”淳于敷听了,淡淡挑眉一笑,“你是让我为木……木姑娘做师傅?”
“怎么,你不愿意?”对她不周的礼数直皱眉,钱玉冷道,“若不乐意,那……”
“不,乐意之至。”忙打断她的话,淳于敷微微一笑,双手一捏裙摆,在原地转了个圈,裙摆便飘逸地飞了起来,让她有如翩翩起舞的文蝶一般灵美。
“不瞒钱公子,文施身上的衣裳便是木姑娘所赠,木姑娘温柔大度,能与她授课,却是文施的荣幸。”
“嗯。”钱玉淡淡点头,“既如此,我明日便唤丫头与你们收拾个屋子作授课之所。”
淳于敷微微欠身,“多谢钱公子。”
“不必。”钱玉板着脸说完,看她问完了话却站在原处还没有离开的意思,不禁又皱眉提点道,“时候也不早了,淳于姑娘不去休憩么?”
淳于敷微一掩唇,娇俏脸上现出一朵笑容,“呵呵,钱公子这是赶人么?”
钱玉不为所动,“孤男寡女,夜间共处一室总归不妥。”
孤男寡女?她以为这钱小公子不过是在书房看会儿书便回房睡下的,如今听话头,竟是与木雪分房而睡么,难道她们夫妇不和?
这个想法在脑内过了一遍,淳于敷嘴角浮起一抹不易察觉的笑,“那倒是文施不懂礼数了,文施这便告辞,不打搅钱公子歇息了。”
钱玉干巴巴地回,“姑娘也去好生歇息吧。”
淳于敷略一点头,退了几步,便回身出了房门。
灯笼的光照亮了廊回的路,淳于敷噙着微笑不紧不慢地往客房走,拐廊处忽而撞上提着灯笼的木雪。
“啊,真巧。”淳于敷挑挑眼角,微笑望她道,“木姑娘怎么这般晚了,还不睡下,提着灯笼,这是要去哪儿?”
木雪提着灯笼淡淡看她一眼,“淳于姑娘这么晚了,不也没睡么?”
“呵,倒是文施僭越了,文施这便去睡下,还望木姑娘能以自个儿身子为重,早些睡下才是。”淳于敷提着裙摆,轻飘飘从她身边走过,贴着她耳边道,“放宽心,我可不会愚蠢到想出生米煮成熟饭这种计谋,我不过是去向你那夫君讨个差事,而他也干脆答应了,以后,咱们便以师徒相称了,木姑娘。”
说完,她笑着花蝴蝶一般飘走了,木雪捏着灯笼柄的手紧了紧,在原地站了片刻后,什么事也未发生一般,继续往前走去。
好容易侯着淳于敷走了,钱玉松了口气,慢慢解完了外衣,只留件小衣,满足地抬起腿想要踏入浴桶边的木凳上,忽然一阵锥心地疼从右边小腿处传过来,让她站不稳跌在地上。
“嘶——”
石虎那一刀太狠,都见了骨头了,她当时忍着疼只勉强拿茅草束住腿止了血,后来又暗中唤钱多去买了药,正经医治却是没有的。
看来今儿个是不能好生沐浴了。
钱玉皱眉,叹息着撑着浴桶边的椅子站了起来,没挪几步,门又笃笃被人敲响了。
以为是淳于敷又有什么事折了回来,她忙扯了件外裳盖住自己,冷着声道,“进来。”
门轻轻一声响后,一阵脚步又响起来,愈来愈靠近她。等了好半天没听见身后人说话,钱玉不耐烦地摆手,“有甚么事,快些说,淳于姑娘习惯胡俗,恐怕不知汉人若是抓住了孤男寡女共处一室,会如何惩处了。”
“你……还好么?”
“淳于姑娘岂不是明知故问,方才我们不是见过,钱玉好好的不劳姑娘费心!”
担忧自己如今衣衫不整身分会被看穿,钱玉心烦意乱之下没听出木雪的声音,愤然指责时,不意一个转身却见是她,顿时语塞,“……怎么是你?这么晚了,你……你过来做什么?”
木雪不答,安静把手里灯笼吹灭,放在一边,挽起袖子,走到浴桶跟前,“你右腿受了伤,不能洗浴,实在难受就擦擦吧。”
钱玉瞪大眼睛,“你怎么知道我受了伤?”
“你走路时倚重左边身子,步伐都是一深一浅轻飘飘的,我只当你是右边身子伤到了,后来是陈将军告诉我,你伤到了右边小腿,怕你伤了筋骨,便给了我一瓶药,又教了我一些跌打断伤的粗浅医术。”
木雪淡淡说着,从袖中掏出一个白瓷小瓶,望着她,“我替你打水,你先擦擦身子,小心别碰上水,擦好后,我再替你上药。”
钱玉却不大高兴,“哼,这可真是风水轮流转,上次你受伤我照顾你,这次我受伤你照顾我,咱们可算是扯平了——你是不是打着这样的主意才过来替我看伤的?”
木雪看都没看她一眼,拿起浴桶边木盆,替她打了水,搁在书房屏风后头,“快去吧。”
钱玉别别扭扭地撅嘴望她,她却没什么反应似的在收拾浴桶,挫败之下,她只好一跳一跳地单脚跳到屏风后头,脱了衣裳擦身子。
木雪收拾好东西,等了一会儿,她似乎终于勉强弄好了,跳着步子又从屏风外出来,乖觉地跳到榻上坐下,偷吃东西被主人抓到的灰鼠似的,一双黑黢黢的眼睛滴溜溜地盯着木雪瞧。
真是个不省心的主儿,明明在外头看着可靠,怎么一回自家院子就变了孩子王一样蛮不讲理。
叹着气走至她身边榻沿坐下,木雪小心托着她右腿看了看,一尺多长的一道口子,开在腿肚子上,皮肉翻卷着,隐隐露出了些白骨,好在虽说伤得深了些,却是险险避开了脚筋,不然,可得有天不怕地不怕的钱小公子受的。
怜惜地看着那一道伤,木雪倒了一些药在手心,“疼么?”
钱玉眼珠子滴溜溜转了一圈,可怜兮兮道,“疼。”
在她怜惜神色更重时,又忙道,“你给我吹吹就不疼了。”
这下就是傻子也能知道她心里打得什么算盘了。木雪瞥她一眼,没说什么,不紧不慢按着手心的药膏便敷上了她的伤口。
“嘶——疼疼疼。”钱玉疼得眼泪花都冒出来了,她就不该在弱势之下起歪心思的,看,遭报应了不是?
无视她噙着泪珠的眼睛中透出的控诉,木雪一面把药膏均匀抹在她伤口上,一面淡淡道,“这叫清肌膏,只有把伤口外头坏死的肉清掉,才能给你缝伤口,你就暂且忍忍吧。”
第73章 第73章
钱玉咬了唇;把头埋在榻上的一条薄锦被里,嘟嘟囔囔道,“哼,陈老头也忒坏;好生生的伤凝脂玉膏不给你;却把这让人疼的药送你;明摆着欺负咱们人生地不熟;是个轻客商人!”
要是陈季延听见她这话,定是要气得吹胡子瞪眼了:不识好歹的小子,这可是千金从后梁商人手里买过来上等的膏药!
所幸听见她说这话的只有木雪;看她不识好歹的还在背地里评头论足,也不多说什么,只是默默替她擦好药后;又掏出随身带着的针线包;取出一根小拇指长短的针,在油灯底下淬了淬。
钱玉耷拉着脑袋懒懒地趴在榻上装死,耳边听见脚步声;知道她是起了身又回转回来;不由奇怪把头从榻里探出来;“你做什么?”
“替你缝伤口。”木雪面无表情地说着,亮了亮手中捏着的一根针。
油灯里的灯芯嘣出几滴火花,不知是否看错,总觉得晕黄油灯光亮下,眼前的女人神情莫名的有些可怖。
望着那长而尖锐的针,钱玉抖了一下身子,瑟缩地下意识要往榻上逃,“你……你轻点……本少爷虽说不是怕疼怕苦之人,可若是身上留疤……呜呜……”
没等她说完,木雪便按住了她的小腿,丢给她一个小白瓶,“怕疼就先喝这个。”
“这是什么?”
“酒。”
“说了不是本少爷怕疼了。”钱玉嘟囔一句,还是垂头丧气地接过酒瓶,仰起头咕嘟咕嘟灌完了后,意犹未尽地呷呷嘴,“这酒味儿不错,不酸微甜,就是时候不久,不够醇——哎,我怎么不记得咱们院里有这样的酒了,你从哪儿弄来的?”
木雪不回她,只定定看她片刻,方才伸出一根手指在她眼前,问她,“你知道这是几么?”
“二,你当我是孩子啊!”钱玉不满地把眼前的手推开,歪着头觞眼看她,“不过你怎么总是在我面前晃悠啊?”
看来这是醉了。
木雪这才放下心,一边摁住她,一边按照陈季延对自己说得缝伤口的法子小心给她剔了些腐肉,再慢慢地拿起绣花针替她把那长到骇人的伤缝起来。
房里安静得很。以至于木雪秉气凝神,手下小心翼翼地穿行时,能清楚听见针穿过钱玉皮肉时“刺”的声响。
那酒也是陈季延给她的烈酒,据说是用齐国边关的曼陀罗花做成,有迷醉人的功效,托了它的福,钱玉如今已经醉得不省人事,一团水一样瘫软在榻上。
许是疼得厉害了,在每一次走针时,她会下意识颤颤身子,小腿痉挛一下,嘴里微微呻/吟一声,“疼……”
“疼你还逞强,不知道自己是女孩子么。”念叨她几句,木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