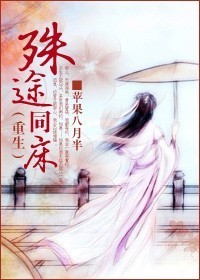同床异梦-第3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他出生在祖国南边的边陲小城,从小生活的地方,离边境不远。他对父亲印象模糊,因为进出他家的男人不少,不知哪个才是父亲。这些男人过来,都遮眉挡眼,弯腰驼背,进了母亲的房就不出来,母亲将他与弟弟锁在卧房,他抱着弟弟,小声给弟弟唱歌。弟弟只比他小两岁,但脑子不好,每日只知吃喝哭,鼻涕流到嘴边,只会狼狈伸舌:“哥哥……我怕。”
“别怕”,谭大学着外面妇女抱小孩的姿势,艰难拖着弟弟,帮他擦掉鼻涕:“哥哥在呢。”
大门被一脚踹开,母亲披着半透明的睡袍,斜倚在门边,她指间夹根吸管,管头上一颗圆球,日光下泛着幽幽水汽。她砸吧嘴,颇为满足地吐息:“收拾东西,明天带你们出去玩。”
莫明恐慌爬上心头,谭大抬脚想向后躲:“妈,带我们……去哪?”
弟弟只听懂了“玩”,他在谭大怀里挣出手,咿咿呀呀挥舞,团子脸乐成一朵花。
女人嗤笑一声,目光转向谭大,蜻蜓点水扭开:“明早六点,跟我走。”
她转身离开,不想面对这个儿子,甚至不想承认,这个孩子由她所出。他早熟太过,三棍子打不出闷屁,像极了那个男人。
那男人有老婆有小孩,但对她一万个好,每次与她见面,都满脸疲态,诉说家里的苦。老婆与他没共同语言,女儿又不学好,初中便辍学去酒吧调酒,和不同的男人开房,还被他抓过现形。
她心疼男人不易,被连哄带骗,连生两个小孩,苦心盼着男人离婚。但生了二儿子后,男人来的突然少了,她每次问,对方都支支吾吾,眼神乱飘。她心中苦闷,去迪厅借酒浇愁,不慎喝了杯加料的酒,从此染上了瘾头。
这东西只要沾上,便会越陷越深,无法自拔,直到被其吞噬。
她后来才知道,那杯加料的酒,是那男人的老婆和女儿,联手给她下的套。
但她早已醉生梦死,沉浸在无法停歇的痛苦,与片刻的欢愉中。过去种种譬如昨日死,再提不起折腾的心思。
她花钱如流水,越来越续不上需要的货,最终她无法忍耐,走火入魔似的在她的上线,金三角一个粉头的带领下,带两个儿子乔装打扮,穿过了边境。
当时的边防远没现在严格,她没有正经工作,上瘾后更与寥寥亲属断了联系,这么一走便像人间蒸发,从这座小城中,彻底消失了。
但人间蒸发……本就是个不详的预兆。她在新家只待了两年,某次剂量注射太多,一针下去,带她离开了尘世。
谭大正从外面劈柴回来,把柴禾放在她床边,起身看她一眼,愣住了。
她颓靡躺在床上,嘴角满是未干的白沫,肋骨排排紧贴胸腔,枯黄的发四散飘落,盖住半张脸。
他僵硬走上前,帮女人合上了眼。
弟弟在外面玩累了,扑进门来,大声喊饿,谭大几步扑过去,一把将弟弟抱起,带出了门。
这个家的“男主人”,在傍晚时回来了,他看看并排蹲在外的兄弟俩,没说什么,只一瘸一拐走进门,用草席子把女人一裹,就地掩埋。
夜半时分,他蹲在埋葬女人的土堆前,用一柄小锉刀,狠狠磨手里的珠子。
谭大坐在旁边,看着面前的土地。
在这里,人的命……还不如草芥。
他旁边的这位“男主人”,死活不肯种罂粟,腿被砍掉一截,从此只能瘸腿走路。
然而,他却在母亲来后,默许了母亲的示好,与母亲在同一个屋檐下,过了两年日子。两人一个出门劳作,一个在家抽吸,竟也相安无事。
“这个,给你”,长久的沉默后,男人动了,他晃晃手腕,把手里东西塞给谭大:“拿着,给你。”
“这是什么?”,谭大抬头,缓缓收紧手指。
“凤眼菩提,珠中有佛眼,法力最强”,男人难得偏过头,与谭大对视,咧嘴笑了:“人有八苦,痛苦时多念佛,会有福报。”
或许这男人,把自己仅剩的福报,都剥给了他。
他们很快被卷入一场武装斗争,男人中了两枪,伤重而死。弟弟也受了伤,因伤口感染,发起高热。
他抱着弟弟,疯跑去各处求药,屯药的商人看见他的脸,都对他连连比划,用磕绊中文重复:“钱。”
谭大没有钱。
“男主人”不种罂粟,只种些简单的谷物,家中仅能温饱。
谭大跪在地上磕头,一家家跪过去恳求,直到弟弟煞白着脸,攥紧他的手,才含泪罢休。
弟弟很快病势沉重,到后来烧坏大脑,看不清东西,临走之前,只拼命把手抬起,哽咽摸他的脸:“哥哥……长什么样……忘了……”
“忘了,也没关系”,谭大抓住弟弟的手,摸过眼睛,摸过鼻子,摸过嘴唇,他眼泪蜂拥而出,沾湿弟弟的脸:“哥哥帮你记着。”
哥哥帮你记着,你因贫穷而死。这世上的一切,包括生命与健康,都为有钱人准备。
谭大自小把弟弟带大,为弟弟付出的心血,比为母亲多出百倍。
他后来认了贾沙当阿爸,又遇到与弟弟相似的查谦,便把查谦带到身边,寻个能逃的机会,带他逃回了国。
查谦身手了得,但语言天赋为负,他连母语都说的困难,汉文更是如同天书。
买语言磁带给他,查谦又不爱学,谭大只得租来录像带,让他从早到晚,循环观看。
边陲小城气温变化大,雨季也久。还未入秋,天边便雷声阵阵,瓢泼的雨在云中沉坠,即将降落。
某个乌云遮天的夜,查谦正趴在床上学舌,木门吱呀一声,一个人大手大脚进来,停在床边,对查谦咧嘴。他一口牙参差不齐,黑黄交接,笑容令人作呕:“嘿,小子,谭大在哪?”
“我在这”,厨房门被推开,谭大端着盘炒饭,冷冷出言:“谁找我?”
一道惊雷闪过,雷光撕裂两人面容。电石火光之间,谭大知晓了那人的身份。
是母亲曾经的“供货商”之一,就是他牵线搭桥,让粉头带走了母亲。
那人凑近两步, 也看到了谭大,他喜出望外,连声笑道:“头听说你回来了,让我来跑一趟。最近来了新料,你妈是个好虫,你也不差。头说了,事成了,这个数。”
他吐了口唾沫在指上,指头捻的啪啪作响。
查谦看了谭大一眼,手在被窝里摸索,悄悄握住刀身。
谭大对他眨眼,拉开厨房的门,对那人道:“几几分?进来谈。”
那人有些踌躇,背影发僵。谭大笑道:“怕什么?就这点胆量?”
房门在查谦面前关上,关住了两人的身影。
雨越来越大,呼啸击打窗棂。
三分钟后,门板一动,查谦听到一声闷哼。刀刃入肉,喉管被切,筋脉像被横上菜板,一刀抹穿。
垂死挣扎时力道极大,薄板被震的咯咯作响,窗上映一道乌黑的影,长而尖锐,从门缝探出。
暗色的血从门缝蔓出,像盛开的罂粟,一丛丛一束束,争先恐后向外涌。
门板被一脚踹开,谭大走出门,把炒饭递给查谦:“你吃。”
炒饭依旧冒着热气,中间一颗上洇一滴血,分外惹眼。
血腥意外浓烈,查谦挑掉那饭粒,无从下口,只得放到一边。
谭大已在收拾那人身体,查谦连忙上前,与他一起,将人塞进尼龙袋里。
两人拖着袋子,出门走了很远,到一片丛林里,在瓢泼大雨下刨挖。血腥与土腥混杂,查谦正奋力刨土,谭大突然叫他:“查谦。”
查谦抬头。
谭大定定看他,在雨帘里,如同一座雕塑。
落在脸上身上的不再是雨,而是冰刃,从上而下飞落,将查谦砍成数片。
查谦不着痕迹向后挪,谭大乐了:“怕我灭口?”
查谦止住动作,轻轻摇头。
谭大看他半晌,弯下腰,推土进坑:“有些东西,你可以卖,但不能沾。沾了,人就废了。”
查谦慌忙点头,谭大又道:“事办完,连夜收拾东西,和我去钱源。”
两人处理好后续,偷偷换了身份,连夜奔赴钱源,到达目的地后,谭大逡巡一段时间,下定决心,一头扎进地下钱庄交易。
钱源市属于中国最南,四面环水,港口众多,有两面与邻国接壤。当时本土货币正处于贬值期,许多人想兑换外币,苦于没有渠道。在当时的钱源,做这行多以家庭为单位,诸多小作坊挤挤挨挨,散兵游勇各自为战。
谭大观察一段时间,着手开始挨家挨户商谈,试图将小作坊聚成团队。他初来乍到,只是个毛头小子,吃闭门羹吃到腿软,但他不放弃,依旧挨家挨户谈判。他语言天赋高,学东西快,很快能与人交流,不少人让他去做翻译,他能和人谈合作就谈,谈不了的,也不切人客户,口碑慢慢累积。
就这么一来二去,渐渐有人与他合作,一家两家,三家四家,人数越来越多。十年间,他的团队发展很快,几乎垄断钱源的地下交易市场,不少人想换钱出境,都要先遣人来拜他码头。
查谦一直跟在他身边,做个尽职尽责的保镖,他那样忠诚顺从,像一条听话的犬。
谭大的生意顺风顺水做了十年,直到他听到线人的消息——他曾杀人的事,东窗事发了。
说来也是可笑,因他生意做的够大,且从不刻意躲闪,竟然逃过了警方的排查,甚至在警方的眼皮底下,大摇大摆过了十年。
正值风口收紧,上面严打的厉害,谭大正做下一步打算,沈达腾派人找到了他。
“沈总的意思,这次大头都给您”,那人给谭大倒茶,茶叶在滚水里打转:“沈总在外面也有不少产业,只是咽不下这口气。”
“沈总家大业大,胸襟如此狭窄?”
谭大点起一根烟,吞云吐雾。查谦在他背后站着,垂头不发一言。
那人又起身倒茶,好言相劝:“沈总说,您的事,谁也保不了,他能保。事成之后,保您远走高飞,谁也找不到您。”
谭大嗤笑一声,碾灭了烟:“四六开。”
那人一愣,没想到谭大如此直接,他僵直脊背,试图据理力争:“谭总,那个对饵子催债的陆喜,歪打正着,正好是您的人。您做这单易如反掌,四六开,是不是有点……”
“做生意,讲究诚信”,谭大敲敲茶杯,让人给他添水:“我的诚意够了,沈总的,我没看到。”
那人无法,只得起身告辞,约好转天再和他谈。
那人前脚刚走,查谦忍不住开口:“谭大,真的,要接这个?”
谭大抬眼看他,以手比枪,顶在太阳穴上,轰的一声。
查谦一抖,身体被拉回罂粟花海,腥甜与恶臭冲入鼻端。
查谦咬牙低头,不再多言,谭大却道:“木屋旁边,新修了一座医院。”
查谦愣了片刻,才反应过来,谭大说的木屋,是他们还在三不管时,所居住的地方。
如果这所医院当年就有,那谭大的弟弟……
“查谦,我告诉过你”,谭大把杯放回桌面,稳稳吐息:“没有钱,你什么都做不了。”
查谦沉默半晌,沙哑开口:“有些钱,是,别人的。”
“有些人的钱,赚的太容易,时间长了,就忘了赚钱的目的”,谭大把玩掌心佛珠,凉凉开口:“劫富济贫,不正是你的座右铭?”
……
' 有大地狱,号极无间。又有地狱,名大阿鼻。复有地狱,名曰四角。复有地狱,名曰飞刀。复有地狱,名曰火箭。复有地狱,名曰夹山。复有地狱,名曰通枪。复有地狱,名曰铁车。复有地狱,名曰铁床。复有地狱,名曰铁牛。'
……
音箱中传来的声音,将思绪拉回,谭大轻踩油门,把车速降下,停在花鸟鱼虫市场。
这市场在淮山和洋海的交界,不到五点便人声鼎沸,里面卖鱼的卖猫的卖鸟的,应有尽有。刚进大门,就见一群人围在那斗蝈蝈,这群人分成两派互相叫骂,筹码稀里哗啦向中间甩,层层汗味汹涌而来。
谭大拨开人群,慢悠悠向里走,再向里是两排鸟笼,长相各异的鸟在笼中呼号,这时上笼的都是新货,是前夜刚从林网捡来,展给第一批玩家的。
受伤的都被丢了出去,余下的这些翎毛漂亮,叫声清脆。然而骤然从广阔林中,到了这矮小笼子,再清脆的叫声也唤出沙哑,声声犹如泣血。
笼里飞满四散的羽毛,鸟身与笼子相撞,格外刺耳。
谭大一人走进鸟场,卖主远远看到他,立即一拍脑袋,扔掉手中烟卷,笑脸迎上:“爷,看点什么?”
谭大抬眼,四下扫了一圈:“都是新货?”
卖主点头哈腰,连连凑前:“两小时前刚收的网,烂的都扔了,剩的都是好货。您听这响儿,多脆生。”
笼里的鸟扑腾更厉,翅膀几乎扇出细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