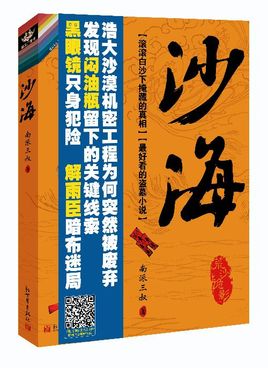情爱笔记-第4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嘴巴上,却始终不肯开口。卢克莱西娅用舌尖施加压力时,她依然不张开牙齿。就在这个时候,透过睫毛和从前额上流下的密密汗珠,卢克莱西姐看到了那个不久前消失、目光锐利的青年在上方、靠近天花板的地方,在一架梯子的顶端保持平衡。他半躲在一架写有中文的雕漆屏风后面,半竖着尖尖的耳朵,眼睛里燃烧着激动的亮光,嘴唇冷酷地掀起,手里拿着一根长长的炭笔,在一张雪白的优板纸上,疯狂地画着她的形象,他和她们的形象。实际上,他像一只猛禽,蹲伏在剪子形的梯子上端,观察和测量着他们,用长而有力的线条描绘他们,那对残暴但是灵活之极的小眼睛从纸上跳到床上,从床上跳到纸上,全然不睬周围的一切,冷漠地对待窗于外面利马的万家灯火和他本人的荫茎,它早已冲破裤子纽扣的束缚,仿佛充气的皮球一样不断地变大变粗。此时,他飞蛇般地在卢克莱西娅上方摇来晃去,保持着平衡,用他那高大独眼巨人般的一只眼欣赏着她。这并没有让她感到惊讶和有什么了不起。她骑在“马”上,感到满足、陶醉、激动、充实,一面时而想着阿尔丰索,时而想着利戈贝托。
“你怎么还在跳啊?没看见我已经She精了吗?”赛马的家伙带着哭腔说道。半明半暗之中,他的脸色枯槁如灰。他像顽童似地在出怪相。“运气真糟,总是发生这种事情。正是舒服的时候,我就射了。我憋不住。没有办法,一点办法也没有。我找过专家,他让我去洗泥巴浴。屁用不顶。洗了以后让我胃疼、呕吐。又去按摩。也是不顶屁用。我去维多里亚区找一个巫医,他把我放进一个泡着草药、臭烘烘的大浴盆里。有什么用吗?一点没用。现在我来得比过去还快。他妈的,为什么这么命苦呢?”
他叹息一声,便啜泣起来。
“哥们儿,别哭了!你的怪念头这不是办成了吗?”阿黛丽塔一面安慰他,一面把跨在他头上的那条腿收回来,然后在这个嚎啕大哭的家伙身边躺下来。
显而易见,赛马的家伙和阿黛丽塔都没有看到埃贡·希勒或者是他的替身在他们上空一米高的地方、在梯子的顶端保持平衡,他借助那根轻轻晃动在床上方的巨大荫茎保持重心的稳定和不至于跌落下来;在昏暗的灯光下,那根荫茎炫耀着自己娇嫩而红润的皱褶和快乐的毛细血管。他和她肯定也没有听到埃贡·希勒在说话。卢克莱西娅听到了,而且清楚之极。
他咬牙切齿地反复在说,好像一个喜欢尖叫和好战的疯子:“我是胆小鬼中最胆小的一个。我是属于上帝的。”
()好看的txt电子书
“表姐,休息了。你还在干什么?戏已经结束了。”阿黛丽塔亲热地对她说。
“不能让她俩走!先揍她俩一顿!你不能让她俩走掉!揍她俩,揍她俩,狠狠地揍!”
这自然是阿尔丰索了。不,不是那个集中精力忙于打草稿的画家。是那孩子,她的继子,利戈贝托的儿子。他来了,也在那里。是的。在什么地方?在房间的某个地方,他被这个神奇房间的黑影隔离在某个角落。卢克莱西娅太太已经冷静下来,缩成一团,不再激动,恐惧地用双手捂住Ru房,看看右边,又找找左边。终于,她发现他们都映照在一面月亮形的大镜子里,她自己也在里面,仿佛埃贡·希勒笔下模特儿的复制品。半明半暗的光线并没有破坏他们的形象,而是更清楚地看到那父子二人坐在一起——父亲宽宏大量、满怀热情地望着她们;儿子亢奋之极,天使般的娃娃脸由于狂叫“揍她俩”而变得通红——坐在一个好像悬在床前上方的包厢沙发里。
“就是说利戈贝托先生和阿尔丰索也露面了。”胡斯迪尼婀娜说道,口气生硬,明显地表示失望。“这种事没人能相信。”
“父子二人坐在一起,一直看着我们。”卢克莱西娅太太肯定地说。“利戈贝托非常规矩,善解人意,又能容忍。可是那孩子却无法克制自己,像往常一样地调皮捣蛋。”
“太太,我不知道您怎么样。”胡斯迪尼婀娜突然打断了女主人的故事,一面起身一面又说:“我现在可需要来个冷水浴。免得又度过一个不眠之夜,因为太激动了。和您谈这些事情让我非常高兴。可是让我感到有些困惑,觉得浑身充了电一样。您要是不相信,那就把手放在我这里,您会感到猛烈的颤动。”
蠕虫的黏液
虽然我绰绰有余地知道您是个糟糕的必需品,没有您,集体生活就可能过不下去,我还是得告诉您:您代表着我对社会和我自己厌恶的一切。因为,自八至少万年以前开始,从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从早上8点到下午6点,除去一些奴隶般的活动(招待会、讲座、开幕式、大会)我不可能逃避,否则会威胁到我的生存,我也是一种官僚,尽管我不在国家机关,而是在私营企业工作。但是由于您和您的过错,在这25年里,我的精力、我的时间和我的才能(我曾经有过一些)绝大部分都被办理各种手续。管理企业、写申请、打报告、完成您用来说明所挣工资理由而编造的程序和给您的屁股加油的办公室所吞食了,仅仅给我留下一星半点的自由去发挥积极性和从事可以称之为创造性的劳动。我早就知道保险业(我的职业)
与创造性劳动相距遥远,如同在恒星宇宙中土星和冥王星之间的距离;但是假如您这个制定规章的灾星、办理公文的毛毛虫不把这个距离变得天壤之别,那也还不至于令人头晕目眩。
因为即使是在保险业和再保险业这个荒凉的不毛之地上,也可以激发出人的想象力并且发掘出智慧的动力,甚至产生快感,条件是:您得被囚禁在那张令人窒息的规章制度的密网里,——这些规章制度都是用来说明这个臃肿的官僚集团存在的必要性,而这个集团已经使得行政管理部门爆炸并且制造出无数为诈骗、抽头、倒卖和盗窃辩护的理由来——不能把保险公司的工作变成一种粗俗的常规,如同琼·迪科莱制造的那些复杂而快速的机器一样,它们转动起链条、滑轮、轨道、铲头、火勺和活塞,最后生产出一个小小的乒乓球来。(您不知道迪科莱其人,知道他对您也没什么好处;尽管我可以肯定:即使你们在路上仍然相遇,您也可能由于采取种种预防措施而轻视这位雕刻家作品所发出的尖锐讽刺,因此不能理解它们的含意,而他是能理解我这番话的当代少数艺术家之一。)
如果我告诉您:在我刚刚获得律师资格,在司法界占据一个微不足道的位置之后就来到了这个公司,在这25年里,我已经升到经理的级别,当上了领导成员,掌握了相当一部分公司的股份,那您就会说:既然有这么好的条件,那我还有什么好抱怨的呢?我是不是太忘恩负义了?莫非我生活得不好?难道我没有踏进秘鲁社会这个有别墅、汽车、一年可以去欧洲或者美国旅游度假一两次、可以舒适地生活和享有五分之四的同胞做梦也不敢想象的安全的小圈子中吗?这一切都是千真万确的。确实由于这个事业上的成功(你们不就是这样说的吗?),我能够把自己的书房摆满图书和画册,它们帮助我抵御眼下占据统治地位的愚昧和鄙俗(也就是说抵御您所代表的一切);我能够建立一个自由和想象的飞地,在那里我每天、确切地说每个晚上,我可以排除粗俗的常规、不讲信用的惯例、由您组织并赖以生存的阉割他人个性、强调群体化的活动所产生的毒素;我能够生活、真正的生活,能够成为我自己,给居住在我铁门外的天使和魔鬼打开门户——由于您的过错,就是您的过错——他们不得不在白天隐藏在大门外面。
您还会说:“既然您如此仇视办公时间表、公函、单据、法律文书、协议书、投诉书、许可证和申辩书,那为什么一直没有勇气耸身一摇摆脱这一切去过真正的生活、您那想象和充满欲望的生活,而且不仅是在晚上,也在上午、中午和下午?您为什么把自己多一半的生命让位给同时与您那些天使和魔鬼一道奴役您的官僚动物机器呢?”问题问得好——我自己也多次提出这个问题——,但是,我的回答也总是这样的:“因为这个自由想象、欢乐和充满欲望的世界、即我唯一亲爱的祖国,如果不摆脱物质的匮乏、拮据、经济的困扰、债务和贫困的折磨,那就不能存在。美梦和愿望是不能当饭吃的。如果不解决物质问题,我的生活就会贫困,就会变成对生活本身的嘲讽。”我不是英雄,不是大艺术家,不是天才,因此怀抱着创作一部可以拯救我脱离苦难的“作品”的希望是不能安慰我的。我的理想和才干只限于区分——在这方面我比您强,偶然机遇给您创造的条件把您区分伦理和艺术的感觉减少到“零”的程度——周围种种可能之中我的爱和增、使我生活变得美好和丑恶、愚蠢的东西,使我得到欢乐和痛苦的事物。为了绝对具有经常分辨这些矛盾选择的条件,我需要经济上放心,而我这份被繁琐公文污染的职业提供了这一放心,这个职业就是如同蠕虫吐出黏液那样由您制造出来的可以致人死命的瘴气,而且它已经转化为全世界都在呼吸的空气。想象和欲望——至少我的是如此——需要起码的一点的宁静和安全才能表示出来。否则的话,我的想象和欲望就会萎缩死去。假如您从这里就推论说我的天使和魔鬼是不动情的资产阶级,那是一句精确的真话。
前面我用过“寄生性”这个说法,您可能会发问我是不是有权利使用它来反对什么人,既然我是一个律师,从万年以前就把法律应用到保险专业上来了——而法律是官僚阶级赖以生存的基本食粮和第一个官僚产物。是的,我有这个权利;但仅仅是因为我用它来对付自己,对付我那官僚分子的一半。说实话,最糟糕的是,这个合法的寄生性是我的第一个专长,是为我打开贝里乔拉——对,这是个使公司当地化的可笑名字——保险公司大门的钥匙,是帮助我获得最早升级的关键。那个从他上第一堂法律课开始就发现所谓的法律在很大程度上是片密不通风的原始森林,专家们总是要从乱子、阴谋、规章、诡辩中牟取私利的家伙,将来怎么能不成为巧妙玩弄法律条文的人呢?律师这个职业与真理和正义毫无关系,而仅仅与炮制不容争辩的假象、与无法揭开的狡辩和圈套有关系。的确如此,这是一种根本性的寄生活动,为爬到顶峰我做得很有成效,但是我从来没有欺骗过自己,明白自己是个依靠他人的无自卫本领、软弱无能得以生存的脓疮。与您不同的是,我不打算成为一块《社会的柱石》(请您查阅乔治·格罗茨这幅画也是没用的,因为您不了解这位画家,或者更糟的是您仅仅知道他画的那些表现主义的漂亮屁股,而不是他对魏玛时期德国您那些同行致命的讽刺画);我知道自己是个什么东西,也明白自己的所作所为,我看不起自己的这一部分,其蔑视程度与看不起您身上那些毛病有过之而无不及。作为严守法规的律师我所取得的成就,便来源于这样的验证——法律是一门与道德无关的技术,它为那个掌握得最好的恬不知耻的家伙服务——以及来源于我的这一发现、也是早熟的发现:在我国(是不是在全世界都如此?)法律制度是个互相矛盾组成的网络,每种法律或者具有法律效力的规定在网中都可以反驳批准或者取消它的其它法律或者规定。所以我们大家总是在违反某种法律和总是针对某种秩序(实际上是混乱)在犯罪。正是通过这个迷魂阵,您令人眼花缭乱地再细分,增加,复制,再繁殖其它法律条文。正是因为有了这一切,我们当律师的才能有饭吃,其中有些人——我的过失——才能发财。
这样一来,尽管我的生活是一种坦塔罗斯式的苦难,是一场我生存中的官僚累赘为一方和我个性中秘密的天使与魔鬼为另一方之间的每日精神上的搏斗,您却从来没能战胜过我。
面对从星期一到星期五、从上午八点到下午六点所做的一切,我始终保持足够的嘲讽去蔑视这份工作并且因从事这份工作而蔑视自己,为的是业余的全部时间可以给自己赔礼和补偿、解放和使自己更有人性(具体到我的情况,这意味着不与他人搭帮结伙)。我可以猜想出您会心里发痒,即好奇,并且会怒气冲冲地发问:“这小子每天夜里都做些什么因此得到了免疫力和摆脱了俗气?”您想知道吗?由于我现在孤身一人——就是说,与妻子分居了——我便阅读和欣赏一些画册,浏览和补充这些带书信的笔记,但最重要的是我想象,做梦,建设一个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