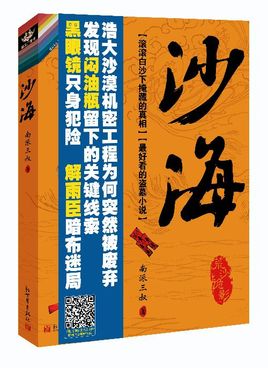情爱笔记-第2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但是,锡拉丘兹的朋友和对手,所有这一切让我感到自己是个不正常的人。那时候,这个想法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因为有许许多多的人——我担心是大多数——还没有把人与人是不同的思想同维护我个人独立的要求联系起来,而仅仅是同社会应该惩罚调皮鬼的思想联系在一起。被当做传染病患者、即排除于正常人之外,让我觉得这是最大的灾难。直到后来我才发现这个癖好之中也不都是怨恨,其中有些癖好是快感的神秘源泉。比如,姑娘们的膝盖和臂肘就是之一。我的有些同学喜欢漂亮的眼睛,细高或者丰满的身条;胆子再大的,还喜欢胳臂和细腿。只有我才想起来专宠膝盖和臂肘,现在我可以毫不羞愧地在我笔记本的秘密深处供认这一点:姑娘的膝盖和臂肘要比她们身体的任何部分都更有价值。这话是我说的,绝对不否认。滚圆,但不过分隆起,富有曲线、绸缎般光洁的膝盖,光润,没有皱纹,令人心安,手感柔软,具有再生石膏的海绵特性的臂肘,这两个部位让我感到焦虑和亢奋。看到这两个地方,抚摸着它们,我就感到幸福;如果可以亲吻它们,我就飘飘欲仙了。您是不会有机会这样做了,但是如果需要卢克莱西娅出来作证的话,我亲爱的她可以告诉您我度过了多少时光——如同儿时站在耶稣受难像前——怀着陶醉的祈祷心情欣赏着卢克莱西娅那完美的膝盖和那举世无双、光滑如玉的臂肘;我亲吻着这两个地方,像调皮的小狗患一样啃咬着心爱的骨头,沉浸在陶醉之中,直到舌头麻木或者嘴唇痉挛又让我回到庸俗的现实中来为止。
亲爱的卢克莱西娅哟!她身上的优点很多,但是我最感谢她的是这样一个优点:理解我的弱点和善于帮助我实现我的梦想。
正是由于这个癖好,我不得不经受一次反省。天主教行动组织里一个非常了解我的同志,注意到姑娘身上最吸引我的东西是膝盖和臂肘时,便提醒我:你心里有某种坏毛病了。他喜欢研究心理学,这把事情弄得更糟,因为他出于正统,希望人类的行为和动机应该与教会的道德和教育协调一致。他谈到了种种异常现象,说出了“物恋”和“物恋癖”这两个名词。
如今我觉得这是词典里最可以接受的两个词了(您、我以及一切敏感的人都属于有、“物恋癖”的人);可是在那个时代我听起来就等于是“道德败坏”和“令人不齿的恶习”。
锡拉丘兹的朋友,您和我都知道:“物恋”不是像皇家学院大词典中吝啬地解释为:“对物的崇拜”:“物恋”是人类个性表达的一种特殊方式,是男女设计自己空间的一条渠道,是运用自己想象力和反群体精神的一种方法,是争取自由的一种手段。我很愿意跟您坐在锡拉丘兹城外乡村的某处小房子里,我想象那周围一定有湖泊、松林和白雪皑皑的小山,咱们一面喝着威士忌一面倾听着干柴在壁炉里的劈啪声,我给您讲述发现“物恋”在个人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是如何具有决定意义的,此事发生在我对社会乌托邦思想失望之际,——这种思想是要集体建设幸福和美好的生活,或者是要把任何道德或者艺术价值人格化——,发生在从有信仰列不可知论的过渡时期,以及现在支撑我精神的信念中:根据我目前的信念,既然男女没有乌托邦思想就不能生活,那么实现这一思想的唯一现实方法就是把这一思想从社会转移到个人的天地里去。不破坏许多人的自由,不以可怕的共同名称消灭个人之间美好的差异,一个集体就不可能为获得完美的形式而组织起来。反之,一个孤立的个人——按照他自己的欲望、癖好、恋物、怨恨或者喜爱——则可以建造起一片接近那生活与愿望相符的最高理想的独特天地(或者像圣徒们和奥林匹克冠军们那样实现最高理想)。当然,在某些得天独厚的情况下,一次幸福的巧遇——比如,精子和卵子相遇并受孕——可以让一对男女用互补的方式实现他和她的梦想。肯尼思·廷南就属于这种情况(我刚刚从他那善解人意的遗孀写的传记中读到),他是个记者、剧作家、评论家、歌舞演员、一个不够严肃的从业人员、秘密的Se情受虐狂,一个偶然的机会让他认识了一位仍然从事性虐待行当的姑娘,也因为她羞于当众乞讨的缘故;这样一来给二人提供了快乐的机会,他和她每周在金斯顿市内的一处地下室里玩上两三次:她拍鞭子,他挨鞭子——一种让二人有升天感觉的浑身发育、发紫的游戏。我尊重这种游戏,但不实践这种结果必然是红汞加药膏的玩艺儿。
既然是讲故事——这方面的有成千上万——我就忍不住要说一说卡奇多·阿尔尼亚的性欲令人想入非非甚至得了圣比多病(精神病)的故事。卡奇多是让人接受保险动嘴皮子这个职业中一流好手。这个故事是——在一次我不能不参加那种国庆日还是圣诞节令人讨厌的酒会上,他坦白交代出来的——说他看见一位裸体但是脚踏高跟鞋(用针做的后跟)的女人在抽烟和打台球。这个形象,他认为小时候在什么杂志上看到过,一下子与他早期的勃起联系起来了;从那时起就成为他性生活的指针。可亲可爱的卡奇多哟!当他和一个会计科的黑发而又活泼的姑娘结婚时,我敢肯定她有能力帮助他。我干了一桩带有淫亵念头的勾当:以贝里乔里保险公司的名义——我是经理——赠送他一套标准台球,一辆搬家运输公司的卡车在婚礼的当天把一应俱全的球案、球杆和台球卸在他家里。人人都觉得这个礼物太荒唐了;但是从卡奇多的眼神和感谢我时流出的口诞来看,我知道是搔到痒处了。
可爱之极的锡拉丘兹市的朋友,热爱腋毛的先生,赞扬种种癖好和怨恨不能是没有限制的。应该承认限制,如果没有限制,罪恶就会泛滥,就会倒退到原始的兽性中去。但是,在这个属于个人天地的幻觉领域里,在同意游戏和游戏规则的成年人中,为了他们能够互相开心,一切都是应该允许的。这些游戏中有许多让我感到非常恶心什(比如,会引起放屁的奶糖,在法国风流的一百年里,人们特别喜欢这种奶糖,尤其是萨德侯爵,他不满足于虐待妇女,还要求她们用臭屁把他轰得头晕脑胀,这的确是事实,如同这个世界里的任何差异都应该受到尊重一样,因为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更好地表现人性难以捕捉的复杂性。
您爬上女邻居的屋顶去欣赏和赞美她的腋毛是不是侵犯了她的人权和自由呢?当然是!
是不是应该以社会共处的名义对您进行谴责呢?哎呀,哎呀,当然应该!可您早就知道这个道理并且冒了险,您早就准备为窥视女邻居的腋毛而付出代价了。前面我已经说过:我不能模仿您这种过分的英勇行为。我对尴尬处境的看法和对英雄主义的蔑视,实在太强烈了,除了我动作笨拙之外,也不敢登上别人的房顶去看一个没有遮掩的女性身体上的圆圆的膝盖和球形的臂肘。我天生是个胆小鬼,这可能仅仅是合法的病态本能,仅促使我为自己的癖好、怨恨和种种恋物的毛病找到一个适合在众所周知的正当范围内的壁龛。胆小会剥夺我好色的宝贝吗?当然会!但是我目前掌握的,只要能捞到相应的好处,就足以让我努力去做了。
希望这三个月您觉得短暂,梦中的腋毛森林,由红色、发黑、柔软、蚕丝般毛发组成的街道,您在其中骑马、游泳、跑步、乐得发狂的梦境能够减轻您铁窗下夜晚的沉重。
女教师的内裤
堂利戈贝托睁大了眼睛:女教师的内裤在那里!丢在楼梯的第三和第四个台阶中间,蓝色,闪光,有花边线,带着诱惑和诗意。他像着了魔似地颤抖起来。尽管已经躺在床上好大一会儿了,黑暗中他倾听着涛声,大脑沉浸在流动的遐想中,无论如何不能入睡。直到那个夜里,那个电话又一次响起来,粗暴地把他从梦中唤醒。
“喂,谁呀?”
“是利戈贝托吗?是您吗?”
他辨认出是那位老教授的声音,虽然老先生是用手捂着话筒并且压低了发育。他们在什么地方?在高级大学城。哪个国家?美国。哪一州?弗吉尼亚。哪个大学?州立大学,那座由托马斯·杰裴逊设计的、有白色柱廊、漂亮的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大学。
“教授,是您吗?”
“是的,是的,利戈贝托。可是,清说得慢一点。对不起,我吵醒了你。”
“没关系,教授。您和卢克莱西娅老师共进晚餐的情况怎么样?吃完了吗?”
尊敬的法学家和哲学家内波姆塞诺·里卡的声音破碎成象形文字般的口吃。利戈贝托明白他在利马夫主教大学读书时的法律系的哲学老师一定出了什么严重的事情,老先生是来弗吉尼亚大学参加一个研讨会的;而他是在这里读研究生的(攻读立法与保险),所以有幸给老师当向导和司机,他陪老师去蒙地塞约,去参观杰裴逊纪念馆和马纳萨斯国家战地公园。
“‘利戈贝托,请原谅我打搅你。可你是这里我唯一能信任的人。因为你是我的学生,我又了解你的家庭,这几天你又这么殷勤周到……”
“老师,您用不着客气。”年轻的利戈贝托鼓励老人说。“是不是出什么事情了?”
堂利戈贝托在床上坐起来,被一串有倾向性的笑声所震动。他觉得洗澡间的门随时都会打开,卢克莱西娅太太的身影会像图画一样地出现在门口,她身穿一件那种梦幻式的精致内裤:黑白相间,刺绣制品,有洞眼,丝绸花边,针脚细密光滑,紧紧裹住大腿根,故意突出荫毛,几根小小的荫毛从内裤边缘试探性地——不听话,轻佻地——露出来。那条不可思议地躺在楼梯上的内裤就属于这一类,仿佛是卡塔卢尼人胡安·庞塞或者罗马尼亚人维克多·布劳内尔超现实主义图画中挑逗性的东西;而堂内波姆塞诺·里卡这位好人和天真汉必须从这个楼梯上到自己的宿舍去;在这位老师七年中给他们上过的值得纪念的法律课中,他经常用自己的领带擦黑板。
“利戈贝托,事情是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我遇到一件麻烦事。虽然我好大一把年纪,可这种事情我一点经验也没有。”
“老师,是什么事情?您说吧!别不好意思。”
为什么不让老师下榻在假日饭店或者希尔顿饭店呢?其他主席研讨会的人不就是住饭店的吗?为什么让他住在国际法女教师的家中呢?一定是出于对他声望的敬重吧。或者是因为他和她多次相遇在法律系?相遇在国际代表大会、讨论会、圆桌会上?或许是合作起草过渊博的论文,里面充满了拉丁语词、大量的注释和令人窒息的书目,发表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希宾根或者赫尔辛基的专门杂志上?实际情况是:尊敬的堂内波姆塞话没有去住假日饭店那无人情味的塔楼里,而是在卢克莱西娅老师那舒适、既朴素又现代的小住宅里过夜。利戈贝托非常熟悉那里,因为这学期他和她一起参加了第二学年的国际法研究班;他有好几次登门拜访给她送去作业或者还给她热心借出的大量法规。堂利戈贝托闭上眼睛,他感到毛骨悚然,因为他又一次看到了那位法律女教师离开时优美的形象、苗条的身影和按节奏摇摆的臀部。
“老师,您好吗?”
“好,好,利戈贝托。实际上,是一件蠢事。你会笑话我的。可是我已经说了。我一点经验也没有。我犹疑不决,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小伙子。”
他不需要说下去了;声音在颤抖,仿佛他要沉默,而话语是用产钳夹出来的一样。他一定是在出冷汗。他敢把发生的事情告诉这个小伙子吗?
“你瞧,事情是,从那个会议办的那种招待会上回到家里以后,卢克莱西娅博士在她家里准备了一顿小小的晚餐。只给两个人准备的,对,这也是她的友好表示。一顿非常亲切的晚餐;我俩喝了一小瓶葡萄酒。我是不习惯喝带酒精的饮料的;这么一来,可能我的全部发昏,就是从上脑袋的眩晕开始的。显而易见,是那点加利福尼亚的葡萄酒作怪。是的,有些后劲。”
“教授,您就别拐弯抹角了。告诉我出了什么事情!”
“等一等,等一等。你想想看:吃了晚饭又喝了那瓶葡萄酒以后,那位女博士还坚持我们再喝一杯白兰地。当然,出于礼貌,我不能拒绝。可是,小伙子,那时我头痛得眼睛直冒金星。那是酒精在燃烧。我咳嗽起来,甚至我想:酒精会让我失明的。确切地说,我一定出了什么可笑的事情。孩子,我躺倒就睡着了。对,对,就在那个大沙发上,那个既是客厅又是书房的大沙发上。等我醒来的时候,也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