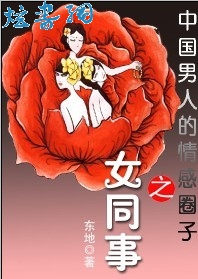中国版越狱九号房-第3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最后,请独眼给我们训示。”
独眼不懂帮主的“训示”是哪里学来的,印象中只有国民党的军队才说训示。独眼想奋力一搏,话就一定要出口:
“我们能关在同个号房,就是缘分。我们互相帮助,彼此和睦相处。我希望若干年后,同处一个号房的日子能给我们留下美好的回忆,就像战友一样。”
独眼的话无趣地戛然而止,因为此类话对九号房太陌生了,大家起了疑心,演说无法打动任何人,盯着他的全是警惕而木然的眼神。独眼有点难堪,小如却抓紧时机宣布:
“摊被。”
躺在通铺上的时候,孤独就在小如身边。围绕新娘的离去,大家纷纷发表高见,九爷满以为小如肯定有一番高屋建瓴的话别之词,结果他自始至终保持着沉默。帮主得知新娘虽然于看守所是二进宫,却没有踏进过监狱的大门,浑身是劲。帮主十分权威地教导新娘:
“走在路上如果遇到干部,无论干什么都要放下,为干部让路,最好能鞠上一躬。要尽快加入积委会,争取当组长。对老乡一定要义气,不然就苦海无边了。”
这些话新娘听起来恍若异邦,基本上还是理解了,就差个“积委会”。
帮主解释说:“是‘积极分子委员会’的简称,表现好有关系的犯人才能加入。”
“还有,”刀疤插嘴说,“千万别搞同性恋,干部最恨这个,熬不住了就自摸。”
早晨的铃声骤然响起的时候,外面的天空还是黑的,有人在监窗外沿路喊“起床”,却见不到干部的身影。大家衣服刚穿好,小鸟就来开监了。里间的铁门打开,帮主给了独眼一个眼色,独眼蓦地站起来,指挥说:“帅哥,拎尿桶。”
()
帅哥愣住了,张皇地看看小如,小如面无表情;又看看新娘,新娘忙着收拾东西;再看看九爷,九爷在悠闲地梳头。看来是大势已去了,这么悲观地想着,帅哥只好重操旧业,将尿桶拎出号房铁门外。
牛刀小试的独眼决心乘胜追击,以巩固既得战果。交通正在叠被子,独眼踢踢他高高撅起的屁股,指示说:
“把上面最好的那条用塑料袋套了,换给新娘带去漳州用。”
“不敢当不敢当,”新娘按住交通的手说,“无功不受禄嘛。”
“我说了算。”独眼言辞间豪迈十足。
这么一逼,新娘只好说实话了:“你说了不算,这条新被子是小如的,他可没开腔哪。”
黑脸看在眼里,稀饭分到手,黑脸主动把粥面上的十几粒黄豆如数拨到独眼的饭碗里。独眼舒心地笑了,调羹一搅拌,它们就同自己的黄豆融为一体。黑脸欣慰地看到,独眼空荡荡的左眼皮爽快地跳了几下。
送走了新娘,独眼觉得自己已经是牢头了,讲武力,九号房谁是对手?早晨的太阳刚刚晒到西墙,独眼大大方方坐在水桶上,叫黑脸站在身边,用报纸为他扇风。
独眼的牢头梦做到中午就破灭了,因为午睡时出了一件咄咄怪事。大家刚睡着,就被帮主石破天惊的尖叫声惊醒了,帮主边叫边跳,像一只野猫的尾巴上被绑上了点燃的鞭炮。帮主的痛苦十分怪异,只见他双手插进裤头,从情形上看好像是在抠屁眼,身体歪向一边上蹿下跳。帮主没说是怎么回事,也就没人能够帮他的忙,各自抱开被褥让出一块地方让他去跳。帮主改了口,不光是尖叫,而是以尖叫的刺耳喊“报告”。
指导员如期出现在监窗口,帮主不等他问话抢先汇报了:“有人用风油精抹我的屁眼。”
第74节:九号房(74)
九号房笑得像炸开的锅,指导员别过脸,从抽动的肩峰可以看出,他在心花怒放。等指导员严肃下来,九号房的声浪也平息了。指导员恢复了严厉的面孔:
“谁抹你的屁眼了?”
帮主委屈地说:“不知道,我睡着了。”
“那你总该知道谁有风油精吧?”
帮主指证九爷说:“他有。”
“唔——”指导员奇怪了。
九爷轻轻一笑,不置可否。帮主气急败坏,说话就语无伦次了:
“查房,一查房就查出九爷了。”
九号房新一轮的大规模查房开始了,指导员亲自带领一个班的武警战士开进九号房,从摸索被褥到抖开所有包裹,从撬开每一块床板到人人过关搜身。挖地三尺不见得有金银财宝,战士们个个汗流浃背,除了留下一片狼藉他们一无所获。
指导员命令全体人犯靠墙站好,伸出双手让他逐一嗅过,嗅完一遍,指导员重复再嗅嗅独眼的手。
“右手好像有风油精的味道。”指导员请武警班长参与鉴别,班长凑过去一皱鼻子说:“就他,没错的。”
独眼大惊失色:“冤枉哪指导员,我根本没见过什么风油精。”
指导员勒令独眼交出风油精,“那是玻璃制品,严禁带进号房的。”
独眼慌不择路,脱光上衣、退下裤子,再翻出全部口袋。“我手上怎么会有风油精的味道,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班长用电棍捅捅独眼赤裸的肚皮威胁道:“你交还是不交?”
独眼举手做投降状:“战友战友你别急,我也是当兵出身的,立过三等功,这只眼睛就是抗洪抗没了,不信你问问指导员。”
班长收起电棍,将信将疑地看看指导员。
“我这里只有在押人犯,没有什么抗洪英雄。你是医药公司的吧?”
这时,九爷说了一句话,这句话仿佛在指导员心中敲下一枚钉子,坚定了他从严处理独眼的决心。但在独眼和其他人听来,九爷说的不过是一句家常话。
()
九爷说:“他就是叶月的新丈夫。”
指导员点点头,没说什么,露出焦黄的鸦片牙笑了一笑。
帮主不要闻手,因为他是受害者,武警一进来,他就冲到水池边脱掉裤子,忙着给自己洗屁股了。交通被指导员嗅过手,出来外间可没闲着,接过帮主手中的勺子给他浇水。
尽管有指导员在场不好随便打人,在撤出九号之前,班长还是找到了泄愤的对象。帮主趴在地上,光溜溜的屁股朝天翘起,交通正一勺一勺地往肛门处冲水。班长拉开交通,电棍抵在帮主的肛门,一通电,帮主就像挨了一棒的落水狗那样,一声怪叫撞向了地板。班长还不解恨,一脚踩在光屁股上说:
“弟兄们累得半死,你倒会享福,让人洗屁股。”
有一个重要的情节被所有的人忽略了,九爷在开口说话之前,将含在嘴里的那瓶风油精吐在手心。
由于惊魂未定,整个下午九号房都悄无声息,当大家被开门声吸引,才发现九爷站在铁门背后,胸有成竹的样子。
进来的小鸟抱了一副木铐和一把扳手,指导员手握门闩,喊“吕崇军”。独眼只穿短裤走出外间,指导员说,“穿上长裤,戴木铐就不好穿了。”
此时,独眼才领会,带来的木铐是为他准备的。独眼穿好长裤,迟迟不出来外间,躲在里间的角落抗议说:
“我根本不懂风油精的事,你问帮主,他会相信是我抹的吗?”
帮主帮腔说:“每一个都有可能,就是独眼不可能。”
“吕崇军,你老老实实出来戴木铐。”指导员站在铁门边高声斥责,“我知道你当过兵,可你当的是猪倌兵,你打得过武警吗,要不要叫几个来跟你过过招?”
独眼还是不服,“我没有犯错误,为什么要受惩罚?”
“我从不冤枉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你戴上了我就告诉你为什么。”
独眼走出外间,小鸟示意他坐下。小鸟用扳手旋开木铐的镙帽,扣好独眼的脚腕,再用扳手旋紧。独眼坐在地上大声嚷嚷,“戴好了,告诉我为什么?”
手持扳手的小鸟从指导员身边溜了出去,指导员对独眼的态度很不满意,“叫个鸡芭毛,先戴一个月再说。”
指导员锁好铁门,打开送水送饭的方孔说:“吕崇军,你知道什么是杀父之仇、夺妻之恨吗?”
独眼恍然大悟,“叶月离了婚跟我自由恋爱,我夺谁的妻了?王苟这是公报私仇。”
“不关王苟的事,是我要罚你。”指导员说,“叶月是多好的姑娘,你害得人家做——害得人家坐牢。”
小如不得不重新调整铺位,因为由两块厚木板拼成的木铐至少有四十公分宽、一米长,大约十五斤重,必须安排两人的位置独眼才能平躺。睡在门边的刀疤十分乐意为独眼服务,不等小如布置,就自觉地挪开了,并且喜气洋洋的。
第75节:九号房(75)
包括小如在内,九号房的许多人没有见过木铐,因此,观察独眼的生活成为九号房的新内容。显然,独眼没有戴过木铐,没几天,他的脚踝就肿了。面露关切的首先是小如,这就帮助了独眼,因为帮主、刀疤之流有的是办法,只是没有得到小如的暗示。帮主撕开一条破被单,绞成一股绳,固定在木铐的两端,然后挂到独眼的脖子上。这样,独眼叉腿走路时,木铐的圆孔就不至于摩擦到脚踝。刀疤则准备了两个残破的口杯,独眼平时坐下或要躺下睡觉,把口杯塞到木铐底下垫着,以减轻脚面的负担。独眼经常抚摸耻处,大发牢骚:“脚合不拢,腿根就发酸。”
帮主当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但他能干什么呢,独眼被木铐锁住了,刀疤是随风倒的骑墙草,其他人整天巴望着九爷赏赐几块肥猪肉。帮主纂改了《烛光里的妈妈》,企图以歌声引蛇出洞:
“王八,我想对你说,话到嘴边又咽下;
王八,我想对你笑,眼里却点点泪花。
噢王八,九号房的王八,你的风油精哪里去了。
噢王八,九号房的王八,你敢做怎么不敢说话。
噢王八,九号房的王八,你的腰身倦得不再挺拔。
噢王八,九号房的王八,你的眼睛为何失去光华?
王八呀,老子已知道,你永远都是一只缩头的王八。
()免费电子书下载
噢王八,相信我,老子自有老子的办法。”
很多时候,帮主的歌是冲着九爷和小如唱的,九爷置若罔闻,情闲气定读自己的书。帮主不厌其烦地唱,到底是谁抹的风油精,我他妈的偏要唱他个水落石出。果然,真人露相了,是人,总有不堪侮辱的那一刻。不可思议的是,站出来认账的居然是三棍子打不出个屁来的黑脸。
“你别唱了,风油精是我抹的。”黑脸走到帮主面前说。
帮主的歌声戛然而止,改口为骂人。“黑脸,真是狗仗人势啊。”
“我们单挑,如果输了就闭上你的狗嘴。”
整天挨打受气的黑脸要跟帮主单挑,大家兴味盎然,噢的一声围拢过来。小如心惊肉跳,转头看外间的九爷,九爷摆出事不关己的派头,仍然在读他的书。
“来吧走狗,你死到临头了。”帮主咬牙切齿,脱去外衣摆开阵势。
黑脸拦腰扎住衣角,准备迎击格挡。帮主比黑脸高出半个头,但黑脸的弹跳能力非常强,蹦来蹦去的,帮主无法估算距离。帮主用钩拳逼近,左右开弓乱打,出手慢而且没有暴发力。黑脸把拳贴在耳朵上,保护脸部侧面;尽量缩着头,将左右肘关节贴在腹部两侧,以阻挡帮主的躯体侧钩拳。这样,看起来黑脸处处被动挨打,事实上帮主没占什么便宜。帮主气咻咻的,很是着急,改用直拳连续猛攻。黑脸的身体舒展开来,用格挡频频拨掉帮主的直拳。帮主的体力明显不支,混合连击一出现,黑脸就知道他求胜心切了。灵巧的黑脸总是在帮主快要打着的瞬间,采取滑身阻挡迅速躲避。
为了体现公正,双方都没人助阵,两人打到哪里,哪里就退出一片空地。通铺的床板被踩得咚咚响,体现了他们决一雌雄的坚定决心。机会终于来了,这时帮主犯了一个错误,他抬腿踹了黑脸一脚,侧脚面落到黑脸腹部已是强弩之末。黑脸双手捞住了帮主的脚腕,帮主失去平衡,胳膊可笑地挥舞着。黑脸伸出右脚,扣住帮主孤立的左脚跟,借力往前一送,帮主就仰面躺倒了。黑脸把捞住的那条腿抬到肩上,一个侧身,右脚就踩到帮主大腿根部的耻处。帮主大叫一声,弓成一团就地打滚,黑脸扑上去拳脚交加,帮主早就连防守之功都丧失了。
刀疤从帮主身上扯开黑脸,“点到为止。”他说。
不料,大获全胜的黑脸跑到角落号啕大哭。“他太欺负人了。”黑脸悲恸万分,反复哭诉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