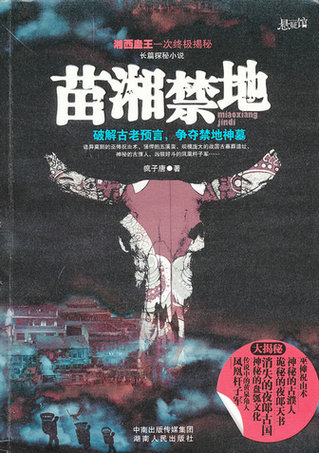活人禁地-第9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端上来之前,又往茶水里加了六七勺白糖。冲着老头yīn森森地一笑,把茶杯递了过去。
那老头见此情景,连话都没说,撒丫子就往外跑。一家人都不明白怎么回事,等反应过来想追的时候,那老头已经不知跑到哪里去了。
自此之后,老太太依然不吃不喝地在chuáng上坐着,几天以来连一分钟都没睡过。虽然她不像前几天那样大吵大闹了,但一个年近70的老人这样熬下去总不是办法。眼看她头发脱落,面皮松垮,怕是再有一两天的就要被活活的折磨死了。
热合曼也是有病乱投医,到处跟人打听哪有能治这种怪病的人。这天问到了一个和他仅有几面之缘的汉族朋友,此人名叫李强,因为比热合曼大了不少,所以热合曼便尊称他为李哥。
那人说这种事找到我就算是找对人了,从你描述的症状来看,你母亲这病肯定是鬼上身了。我正好认识一个神通广大的半仙,在兰州那边降妖无数,应该能把你母亲身上的小鬼赶跑,你就踏踏实实的放心吧,我这就给你联系。
那李哥办事倒很麻利,当时就和那个半仙约定了时间,傍晚时分找个地方见面,其他的事情见面再聊。
虽说热合曼不是汉人,但维汉两族hún居了数十年,他多少也懂得一些汉人的处事方式。他知道对方约定这个时间就是要吃饭的意思,但连日来的huā销已经让他负重不堪,无奈之下,他只好选择了这个自己比较熟悉的小餐厅,因为他和老板有些交情,可以先行记账,等有钱了再还给人家。
后面的事自然不用热合曼再说了,我们都是亲眼所见的。
然而此时我的心里却犯起了难,按照热合曼的描述,他**得的怪病真的有点像是鬼上身,我虽然不太相信世上有这种离奇的事情,但回想起当初和谷生沪在鬼宅的那一晚,也不由得对此事多生了几分疑虑。
如果答应热合曼对她母亲施救,我对这种怪力乱神的事情的确是一窍不通,根本就不知道应该如何处置。可如果撒手不管此事,失去了一个好的向导不说,单单是这个可怜的老人也让我感到于心不忍,如果再这样持续下去,她的生命恐怕真的就要走到尽头了。
我忽然想起了我的护身符,当年面对谷生沪身上那看不见mō不着的东西时,这护身符似乎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也不知这次能不能行。
在这样的时刻,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王子,于是我提起护身符在他眼前晃了几晃,口中问道:“秃子,你说这东西能管用吗?”
自打刚才王子就一直沉默不语,他可不是在低头沉思,而是面有得sè地扬眉而笑,一双小眼都快眯成了一条缝,两个嘴角也咧到了后脑勺。他听我这么一问,更是显得神气起来,摇头晃脑地答道:“管用倒是管用,只不过你这东西的劲头儿太猛了,你想想谷胖子当时是个什么状态?那老太太的身子骨能受得了吗,最后非得给折腾死不可。”
我看他的神情间倒是有着几分泰然自若,弄不好他这王半仙儿真有什么好主意也说不定。于是就催促着让他有话快说,别跟我这儿人五人六的找骂玩儿。
王子又得意了一会儿,这才缓缓讲道,照这意思看,这老太太应该不是普通的鬼上身,鬼上身不是这种症状,虽然也会抽风似的吓跑乱撞,但绝不会说出那些乱七八糟的胡话来,也更不会满世界的逮(鸡)吃。
以他多年来的经验分析,老太太这病应该是中邪的一种,按西方的说法叫恶灵缠身,按中国的俗称,那就叫撞仙儿。
什么叫撞仙儿?这事儿得先从这个仙字说起。按行话来说,所谓‘狐黄白柳灰’,这就是五仙。实际上就是狐狸、黄鼠狼、刺猬、蛇、老鼠这五种特殊的动物。这五仙与其他动物不同,上**华,下接地气,最容易修炼成精。成精以后,一般人便招惹不起了,于是就被人们奉为神仙,也就有了五仙的说法。
当这种动物修炼成精以后,如果有人招惹了它们,它们最直接的报复方式就是上身。先是把人弄得疯疯癫癫地折腾一溜够,然后再慢慢地把人耗死,直到对方咽气以后,这才从(肉)身中脱离出来,或是继续修炼,或是继续害人。
如果说老太太有偷(鸡)这种行为的话,那就基本可以断定了,她这病九成九就是撞仙儿。那你们再好好想想,哪种动物是最喜欢偷(鸡)吃的?
我和大胡子对望一眼,异口同声地低声答道:“是黄鼠狼?”
◇◇◇◇◇◇◇◇◇◇◇◇◇◇◇◇◇◇◇◇◇◇◇◇◇◇◇◇◇◇◇◇◇◇◇◇◇◇◇◇◇◇◇◇◇◇◇◇◇◇◇◇◇◇◇◇◇◇◇◇◇◇◇◇
感谢水⊙火的月票,非常非常感谢。。。
更多到,地址
正文 第一卷 冰川圣殿 第一百二十一章 天篷尺
第一百二十一章天篷尺
黄鼠狼偷(鸡),基本上八十年代以前出生的人都应该听说过,或者是亲眼见过。小的时候我家里虽然没有养(鸡),但我家老爷子却养了几十只信鸽,工作之余最大的乐趣就是鼓捣这些东西。
当时我家所在的那个大杂院里居住了大约有百十来户人家,养鸽子的不止我家老爷子一个人,还有两个鸽友也养着大量的信鸽,要是论起数量来,我家的鸽子应该算是最少的。
有一年,我家那一带黄鼠狼闹灾,大批的黄鼠狼满街游窜,到了夜里,一双双碧幽幽的眼睛随处可见。从我家到厕所的这点儿距离,少说也能看见四五只黄鼠狼在夜sè中横蹿竖跳,胆子大的都不避人了。我从小就听老人们讲过一些关于黄鼠狼的邪事儿,所以在那段时间里,我晚上连厕所都不敢自己上了。
这黄鼠狼灾闹了没几天,院子里的家禽就被咬死了不少,再过一段日子,另外两家的鸽子就开始络绎死去,直气得那两户人家暴跳如雷。
我家的鸽子笼是修在房顶上的,因为高度足够,所以一时幸免于难。我父亲当时大为幸灾乐祸,大赞自己当时的决策正确,把鸽舍修建在高高的房顶,量那些小黄皮子也跳不到如此的高度。
可他的庆幸仅仅维持了两天,第三天头上,当我家老爷子再次去房顶打扫鸽舍的时候,发现我家那六十多只鸽子在一夜之间全都被咬死了,连一只活的都没剩下,这种夜行动物的残忍简直到了无法形容的地步。
那两个鸽友既伤心又气愤,和另外几户人家合计着要想办法把这些黄皮子全都弄死。我家老爷子伤心yù绝,本来也想参与此事,但我妈却死活拦着不让他去,说这些东西都是仙儿,咱可绝对招惹不得,到时候会遭报应的。
就这样,院里的一些居民开始自发的组织起灭除黄鼠狼的行动队来,下毒的下毒,设套的设套,还有一些年轻的小伙子则拿着锄头镐把满院溜达,滋要是见着黄皮子就往死里打,一个月下来,那些碧幽幽的光点就这样慢慢地消失了。
到了最后,那两个养鸽子的人活捉了一只硕大的黄鼠狼,那体型就跟几个月大的小豺狗似的。有人说这是所有黄皮子的头头,只要它一死,其他的黄皮子就不敢再来了。
那俩人觉得仅是打死这只黄皮子难消心头之恨,就把它的所有指甲全都剪掉,然后锁在笼子里一直关着,直到它被彻底饿死才算解气。
可在那以后的一年时间里,院子里凡是参与过灭除黄鼠狼的人全都生了几场大病,有发烧的,有痢疾的,有脑淤血的,甚至还有突然失明的。
而那两个养鸽子的人,则在不久之后相继死去。一个是骑摩托撞在树上飞出去戳死了,另一个死得更加离谱,喝完酒以后,摔进了路边的臭水沟里,居然给活活的呛死了。
我妈听说这事儿以后,菩萨保佑这句话就一直挂在嘴边上。她说要不是当初拦着我爸没让他跟那俩人合伙儿,保不齐现在咱娘儿俩正在你爸的坟上烧纸呢。
自打那次的事情发生以后,黄鼠狼这种动物就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子里,此时听到王子问起什么动物喜欢偷(鸡),我脑海中立时便回忆起童年的影像,顺嘴答音地说了声:“是黄鼠狼。”。
王子点了点头,继续说道:“不错,我估mō着就是它,行话里叫黄大仙儿。不过要我看啊,刚才这老头儿还真不是个普通的骗子,他好像是有那么点儿手艺,只不过就是手艺不太到家,没使唤好,玩儿现了。”
我问他此话怎讲?王子说按照惯例,如果有人撞仙儿了,有两个办法能解决此事。最普遍的办法叫送仙儿,就是和上身的仙儿盘盘道,看谁的道行深。假如这黄大仙儿怕了此人,就会自动离开,该上哪儿猫着上哪儿猫着去。
不过看情形老太太身上这只黄大仙儿可不好对付,它给那老头儿沏了杯糖茶,这就是送客的意思。言外之意,就是我不惹你,你也别招我,我先给足你面子,如果敬酒不吃的话,下一步就该动真格的了。
还有另一种办法,那就是直接招呼,不用虚头八脑的攀比什么道行,上来就练,谁输了谁躺下。
我听他说得这么玄乎,心里有些不太相信,我问他:“你这都哪儿学来的?你怎么知道沏糖茶就是送客的意思?”
王子说我爷爷可是正宗玄门弟子,这种事儿我打小儿就见怪不怪了,糖茶送客的场面我曾经亲眼目睹过两次,你说我打哪儿学来的?
然后他摆了摆手让我不要打断他,接着转头问热合曼说:“我问你,你母亲的腋下是不是起了一个大包?大概有拳头大小?”
热合曼一听之下连连点头:“对对对是有一个(肉)球的嘛,比拳头大的多啦,不知是个什么东西,就这两天才发现的嘛。王大哥,这(肉)球是什么?”
王子冲我一撇嘴,满脸得意之sè,接着他解释说:“狐黄白柳灰,每种大仙儿附体的时候,身体上都会有一个拳头大小的(肉)球凸起,这就是这帮仙儿的仙灵所在。狐狸上身的时候,(肉)球的位置在脖子上。黄鼠狼上身,(肉)球就在腋下。刺猬上身,(肉)球是在后背上。蛇仙儿上身的话,(肉)球是在肚子上面。而这耗子要是上身了,嘿嘿……那(肉)球就长在最难发现的地方——ù裆。”
热合曼已经被王子白话得五体投地了,连声央求道:“王大哥,三位大哥,你们……一定要去救救我的妈妈嘛,只要你们能把她治好,我给你们当羊当牛也行的嘛”
王子摇头苦笑道:“是当牛做马,不是当羊当牛,说不好就别瞎说。行了,现在也不是探讨这事儿的时候,咱抓紧时间到你家里瞧瞧去吧,能救不能救我说了也不算,得见着正主才能知道。”
我和大胡子虽然不知道王子这厮到底有没有那份儿本事,但本着济困救人的原则,还是默许了他的说法,答应去热合曼的家里看个究竟。
从餐厅出来的时候,已经是晚上9点多了。正在路上走着,我突然惊奇地发现,这里的天还是亮的,明晃晃的太阳依然悬在西边的天空上,就和北京晚上7点左右的亮度差不多。
我敲了敲我的手表,一切正常,不像是有什么(毛)病,于是转头问王子说:“秃子,看看你的表几点了,怎么这儿的天还是亮的?按理说早该天黑了呀。”
热合曼马上解释说:“你的表没有问题,我们这里嘛,和北京是有时差的,差不多是两个多小时。天最长的时候嘛,到11点的时候天才会黑。”
我茫然地望着天空叹了口气,心中暗暗纳罕,中国的地大物博可真是难以想象,同一个国度,两个不同的城市间竟然能有这么大距离的时差,这又岂是西方小国的民众所能体会得到的?
热合曼的家距离我们吃饭的地方并不算远,几个人边走边说,不大会儿的工夫就走到了他家门前。
这是一种在喀什当地随处可见的普通民房,通体金黄,全是用泥巴和胡杨木建造的。由于当地的土质特殊,所以这种貌不惊人的房子反而比一般的砖房要结实许多。著名的高台民居就是以这样的建筑形式,在风雨和时间的洗礼中平平安安地度过了六百余年,迄今为止依旧屹立不倒。
在热合曼的介绍下,一家子二十余口人全都非常恳切地央求着我们,虽然他们大部分都不会说汉语,但从他们的表情也能看得出来,老太太的病对于他们来说是无比重要的大事。
我趴在王子耳边小声说道:“王秃子,看着这些人的眼睛,他们可都拿你当活神仙了。你这出戏可千万别唱砸了,不然的话,我都没脸走出这门儿了。”
王子此时倒突然变得严肃了起来,他点了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