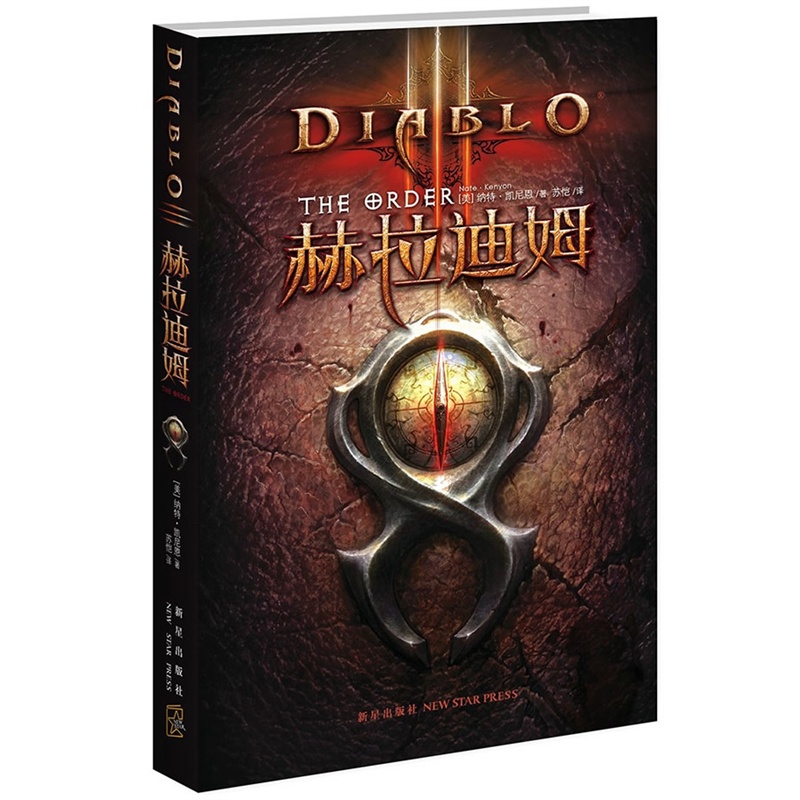赫拉克勒斯十二宗疑案-第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他摇摇头,亲切中带着无奈。
“亲爱的阿喀琉斯,是不是一定要有流血,一件罪行才值得关注?”
“当然不。可我一点都没看到值得关注的事。说真的,我只是浏览了一下主要标题。”
他探究地望着我。
“我觉得您心里烦着呢,朋友。”
“但有人正急急等着春回大地,跟他相比,我还不算心烦。”
“您在韦奇伍德的艺术多餐具公司,是不是有些要操心的事?”
“不,这方面一切顺利。”
“心里有何不快?”
“没有。”
“那,”他又说,其逻辑让人绕不过去,“这么多年来我用心栽培您的观察力——我得承认,并不那么容易——也够可以了吧。就凭这一点,您本该注意到这件奇怪的事……”
他再度拿起报纸,将它在我膝上摊开,用粗胖的食指指着一篇文章:
斯捷普内:奇特的酗酒者斗殴
我狐疑地抬头望着他,心想他对这样一些小事也注意起来,心情未免太消沉了吧。
他似乎明白我在想什么,不大客气地反驳道:
“您先读读吧,然后再作判断。”
说着,他起身走到壁炉那儿,背对着我,专心欣赏起那九个装饰在壁炉台面上的大理石美女。
我带着困惑,开始读这文章。
伊莱亚斯·扎金托斯堪称自然界之伟力:他全身肌肉隆起,脖颈粗如水牛,浓密乱眉下的眼神仿佛凶煞……料想无人胆敢向他挑衅。此人系一水手,希腊克里特岛出生,现时正在伦敦码头打短工,其人办事以一顶三,先后雇主均表满意;唯有品行不佳,曾招惹多宗法院官司。该人生性易怒,脾气暴躁,身为一家之主却并不称职,生活放荡、好酒,晚间多赴东区贫民窟乌瘴小酒馆消磨时光,混迹一群相投者间。他来此发号施令,确属名副其实之山寨大王,但凡招惹他者,莫不肋骨断、牙齿落、胳膊折,似此不可悉数。然上周五,此人终遭遇更强高手……
当晚十时许间,有一衣着怪奇之男子走进“红种人”酒吧大堂。此人若现身西区的摄政王大街,恐会更加惹人注目;然而此时此地(斯捷普内),他置身各种国籍、偶尔亦有异国装束之水手中间,却并无多少顾客觉得刺眼。只见他身披狮皮,狮嘴上颌蒙住头颅,恰如一鸭舌帽遮住眼睛,故其面容上部无法看到。目击者一致肯定他是年轻男子,模样健壮,身躯高大,步态自信,但更多信息仍付阙如。斯时众人或仅将之视为一怪诞非洲猎手而未予注意,然此人却忽向扎金托斯发话,后者正同屋内一酒吧女快活调情。一众顾客莫不瞬时惊呆。“噫,克里特肥仔,现时汝至此何为?汝应守家,与汝糟糠之妻并一众细仔相依为命。放下此一本分姑娘,速速逃命,休要惹本大爷火起心头!”
对扎金托斯而言,此话何止挑衅。他初时惊愕万分,复又一阵大笑,似因其侮辱过甚,反不必大动肝火。只见他微打酒嗝,对身旁女伴哂道:“小亲亲,莫非本大爷尚在梦中……似这等瘦弱孬种,竟敢对本大爷如此说话,真让人孰不可忍!莫非他酒意未过,又或者刚从疯人院跑将出来……”而那瘦小之人则接着又道:“罢矣,肥牛,且留着汝这身肥膘,莫待本大爷将汝打成肉酱!”水手闻此,怒不可遏。只见他巨拳挥舞,猛吼一声,耸身而起,直直扑向对方。而那身披狮皮之人亦早有准备,两人势不可免,开始进行决斗。围观众人均觉此陌生人力量不足,虽尚算结实,又颇见机灵,但面对克里特水手的超常宽肩,却委实难以应对。那水手当时正稍有醉意,又被激起狂怒,出手自无余地。初时,陌生人以其灵巧身法,数次闪过对方猛击,众人犹暗暗揣想,生恐他只是暂时性延缓结局,迟早总会被对方击中,届时必将倏然倒地,长眠不醒。众人同时觉得,纵其人出手反击,亦只能收效甚微………须知那希腊水手体魄巍然,又久经艰危困境,生性好斗,寻常人莫之能敌。然事态大出意料!只见该狮人进退得宜,拳拳直奔水手面颊,招数准确之余,力道更不同凡响。“真神力也!”众观者惊叹不止。
再说那两人赤手空拳相搏,狮人不动则罢,动则招招攻向要害;克里特水手惊骇莫名,慌乱之间,眉弓又遭重击,那拳印深可见骨,红润的胖脸须臾肿胀流血,继而两眼模糊,失足倒地,正欲起身再战,而对方拳势未休,最终动弹不得,惨被制服。狮人停手之后,便向输家说道:“克里特公牛,本大爷早就知会过你,此一教训足矣!望汝辈日后循规蹈矩,休要再上歧途。噫,且容本大爷送汝返家……”此人说着俯下身来,揪起大块头对手头上那浓密蓬乱的黑发,一直拖过厅堂,当众扬长而去。观者无不目瞪口呆,直至数分钟后,方有几人壮胆去屋外一窥,而斯时自是人影无踪矣。
次日上午,扎金托斯太太来到白教堂镇警署报案,正是她提供了狮人的些许情况。那狮人确将其薄情丈夫送回,然则又是何等一副模样!不省人事,血流满面,牙齿全无,下巴歪斜……面目全非矣!扎金托斯太太坦承此事同她不无干系。事出两星期前,她下班回家,路遇该身披狮皮之年轻男子。男子上前搭话,不安而关切地询问其因何伤心若此。她辛劳一天,身心俱疲,未作犹豫便敞开心扉,称家中育有五子,抚养不易;丈夫不管不顾,日甚一日,夜不归宿更是寻常,而回家之际,又往往满身酒臭,廉价香水的味道刺鼻,且动辄对其拳脚相加……狮人对此深表同情,尽力劝慰,并允诺插手此事。扎金托斯太太从未想过此人说话当真,更未料其方法如此。
“善哉!此一公牛被弄服帖啦!”斗殴当夜,狮人前来将她唤醒,并告诉道,“料想他不致再行骚扰众生,定会斯文做人矣。”说完便向她打个招呼,转身而去,将一动不动的克里特水手丢在门口。
狮人所言不虚。他对那克里特水手一番猛揍,使其长期、甚至彻底挥别花天酒地。其体力纵然恢复,亦将留下此番际遇之惨酷后果:他一耳失聪,面目吓人,满口无牙,伤痕遍体粼粼,尤以脑力衰退至深。据医生所言,此人恐再难嚣张打斗,而必会温顺如绵羊、驯服若大象矣……
本文付梓之际,此一离奇“伸张正义者”究系何人,犹自无法确定,然警方仍抱持信心,盖此类以暴力摆平争端之举,实属团伙头目间常见之事。适此社会阶层之中,人物个性受酒精所累,嗜暴力成性,仿佛弱肉强食之丛林世界,粗野几成兽性。一众野兽傲然自恃,相互搏杀,直可凌驾王国法律之上。吾等深信,众警探定能早日将此狮人现形大白,俾置其身于囹圄,严加看管,直至其有意悔改,熟习基本之良好行为准则云云。
“好啦,您对此有何看法?”我刚刚读完,欧文·伯恩斯就急切地问道,“真令人奇怪,不是吗?”
“您是说这个‘伸张正义者’干预此事?”
“还用说吗,阿喀琉斯!这个利他主义者将她那薄情丈夫领上正路,帮了这不幸的家庭主妇一把。”
“可方式这样野蛮,人们不禁会想,这仅仅是出于对正义的关心吗?”
欧文恼火地朝我丢了一眼。
“写这文章的人没有文艺修养,那你想的和他一样喽?可怜的小记者囿于偏见,缺乏理智,在脑瓜迟钝方面,我可要爽爽快快地给他发个棕榈叶大勋章呢!文章标题所讲不确,结论正好相反,酒精跟这件事毫无关系!(他叹了口气,往后抹了抹半短的头发,转身对着一尊优美的美女神像。)你啊,我亲爱的缪斯,告诉我,人们为何只看到自己同胞行为中的恶?为何他们面对美时,要这样固执地蒙住自己的脸?(他探询的目光停到我身上。)这打抱不平的神秘人物,将这蛮汉打倒在地,难道就不具有某种雅致?难道就不是有他独特风格的一位艺术家吗?”
“这个呀,欧文,您讲得有点过头了。”我不无恼火地插话道,“恐怕这只是您的唯美主义吧,它让您在这次悲惨的斗殴中看出一种出色的、高尚的行为。不然,就是您这段时间脑子缺乏运动……”
“也许。无论如何,所有目击者都对这种干预、那样的‘神力’感到震惊啊。”
“记者夸大其词了,您说呢?您可是天天都抖搂这种事的。”
“就算是吧,阿喀琉斯,可又不仅仅是这样啊。您注意到没有,这个打抱不平者说了:‘行啦,您这头公牛给弄服帖啦!’……从一个身披狮皮的人来说,就让人觉得奇怪了,不是吗?”
“您什么意思呢?我觉得这么讲完全切合当时的实际情况。”
“也许是,但这当中有一种巧合,我觉得它非常出人意料……”
“一种巧合?什么巧合?”
欧文蔼然一笑,望着我。
“您让我失望呢,我的好阿喀琉斯。这情况对一个稍有学识的人来说,应该是一目了然的,特别是你们这种人……”
“我?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您的名字是阿喀琉斯,我的朋友。您看,一个名字也像姓氏一样,应当为它感到自豪并对它负责!”
我恼火了。
“好吧,”我生硬地答道,“我自认猜不出。”
他像一位吹毛求疵的教授,摇摇食指表示不屑一听。
“猜猜狮子嘛,阿喀琉斯,猜猜狮子!要点就在这里!我再说一遍:一个男子,身披狮皮,看来热爱正义……”
“欧文,您马上给我说清楚,不然我真的要生气了!您知道的,阿喀琉斯性急,虽然看上去是位平和的绅士和农场主,可有时也会发火的。”
“您快猜中啦,阿喀琉斯,您就要猜中啰!”
我深深吸了口气,用手在桌上重重一拍,也不管是否会弄坏我朋友的茶具。他担心地身子一抖。这时我脑中突然悟到什么。
“该死!”我叫道,“我想起来了!我曾读过一则社会新闻,里面就提到这样一个人!”
“好极了,”欧文说道,对排列在壁炉上的那些小雕像感激地一笑,“您向谟涅摩绪涅的姑娘们说声谢谢吧,她们刚才使您想起这件事了。嗯,我也记得这事,正因如此,我相信这次干预不可能是简单的偶然事件。”
“对,当时那被扼死的少校事件很让我吃惊……”
大侦探皱了皱眉。
“被扼死的少校?您大概搞错了吧!受害者不是军人。另外,他是被匕首刺死的。”
“我说的我有把握:有人把他扼死,随后偷走了他的狮皮。”
他脸上显得有些惊讶。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嗯,好几个月了。是去年秋天,好像是九月份。”
他把手指掰得“咔咔”作响,摇了摇头。
“那我们谈的就不是一回事了!我所想到的那件事发生在一月。去年九月呢?我想起来了,我正在比利牛斯山中小住,所以我不了解这些情况……”他勉强压住自己的兴奋,续道,“该死,阿喀琉斯,快给我讲讲这事!”
“那得到我家里去。我记不清所有细节了,不过我好像在哪个卷宗里还保存着这篇文章……”
欧文兴奋地用手抓住我胳膊。
“好啊,我们去吧!我们下楼,一见到出租马车就上去。我必须马上了解这故事,哪怕它会证明事情其实很平常。”
“平常?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我可以向您保证。”
“那更好啦!但说真的,我不信它在异常怪谲方面会超出我的经历。您想想看,为了矫诫受害者,凶手光明正大地完成了一桩功绩,而且没有先例,纵然是对一个受过锻炼的运动员来说,也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
“那您得知道,在扼死少校这宗案件里,凶手曾有个不可思议的举动,奇怪得连调查人员都大惑不解!”
我没发觉欧文·伯恩斯早就穿好大衣、戴上圆顶礼帽了。他很不耐烦地抓住我的胳膊。
“快,阿喀琉斯,我们赶快!您在吊我胃口呢!您知道我受不了神神秘秘和故弄玄虚!”
2
夜色渐渐降临伦敦,一个年轻女子走进了肖尔迪奇一家其貌不扬的咖啡馆。她不到二十五岁,身形瘦长,深褐色的长发随意飘拂在一件天鹅绒上衣上,上衣曾有过它美好的时光。她脸庞秀丽,轮廓柔美,肤色白皙,跟这个人们印象不佳的平民街区显得不大般配;但是,她清澈的双眸却冷漠、呆板,倒让人觉得和周围工厂那些了无生气的厂房比较相称。这双眼睛并不忧郁,但可以说是已经看破了红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