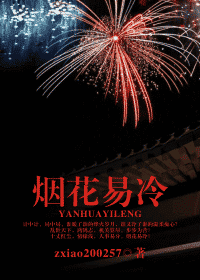烟花不堪剪-第2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卫清远静静地凝视远方,那窗外的风景四季变幻,从翠意盎然到天地间一片浅浅的灰色,没意季都有每一季的美丽,像一帧帧永不退色的画卷,而即使我们的眼睛时时盯着,眨眼的那瞬间,{炫=书=网}终有一些画卷从我们眼前飘过,再也不见。
他额头上有淡淡的灰色,他在微笑,唇角上扬的弧度带着苦涩的味道:“我就是再天真,也不至于妄想,爱可以分享,人可以独占。”
我们都是红尘俗世间最平凡不过的普通人,所以我们只能拥有最普通不过的爱情,谁都有秘密,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隐匿的城。
平安夜,初夏居住的这座城市四处弥漫着节日的欢腾。公寓书房的落地窗,正对着整个热闹纷呈的大学,绚烂的烟花,从肆意喧闹的青春年华中四处升起,在深而远的夜空中,一朵朵盛开,然后光焰寂灭。我们总是追寻这种极致的美丽,比如转瞬即逝的美好青春,比如飘荡在空中纷纷而下的落樱,再比如只开一瞬的烟花;然而,正是这种美丽提醒我们生活的美好,值得我们为之坚持下去。
手机铃响了,背景是喧闹的人声和哄笑声,有年轻的男孩子在电话那头大声地喊:“倪老师,我爱你!”
电话里传来重重的拍头声,有人斥骂:“白痴,要你告白嗳,起码要说,初夏,其实我默默地注视你很久了。”旁边立刻有人驳斥:“废话,才不能这样说,什么默默地注视,怎么听着都觉得像变态追踪狂,你们想吓死倪老师啊。要这样说,夏儿,你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让我无比的心醉,我的心里只有你,再也容不下其他任何人。我把我的心思折成纸飞机,它雪白的的翅膀能否在你的天空留下划痕……”后面的话语她没有听到,被巨大的呕吐声给掩盖了,有人大声喊:“服务员,能否多拿几个垃圾袋来,不行了,洗手间爆满,没有地儿给我们吐了。”
电话这边,初夏笑到肚子疼,她几乎说不出完整的话来,哭笑不得:“喂,你们几个,起码要把告白的话商量好了啊。”
一开始说话的男孩抢到了话筒,声音里带着哀嚎的哭腔:“倪老师,你就接受我的告白吧,否则我就得绕餐厅跑三圈大声喊‘我欲求不满’。”
初夏善良地安慰学生:“年轻人,多经历点儿磨练是应该的,去吧,声音放大点,反正你也不会傻气到把校徽别在衣领上,大家都可以假装不认识你。”
手机刚挂上,新的电话进来了,她心中一动,按下通话键,沈诺在电话那头温和地笑:“跟谁讲电话呢,我一直被提示占线。”
她笑着抱着大大的维尼熊窝在沙发里头:“在听我的学生们商量着如何向我告白,我才能一口答应。”
他很有耐心地谆谆善诱:“那商量出来了没有,如果有结果,我可不可以要求收购所有权?”
初夏嗤之以鼻:“你想得美,哪里轮得到你,我是老师!他们要是敢吃里爬外,我把他们的期末成绩统统算79分,算绩点的时候哭死他们。”
沈诺咂嘴:“那可真狠啊,这不是明摆着不想让人家孩子好好回家过年嘛。”
“你还知道啊。”初夏揪维尼熊的耳朵,声音是她自己都惊讶的爱娇,“所以你不能充当罪魁祸首,陷人家可怜的学生于水深火热之中。”
沈诺还想说什么,电话被人抢走了,响起的,是一个爽朗的老太太的声音:“初夏啊,怎么不跟诺诺一起过来过圣诞。”
其实根本就不算老太太,最多不过五十几岁,只是初夏一想到教授,就是那种精神抖擞满头银发的形象。她本能地紧张,结结巴巴地解释:“那个,妈妈,我要上课。”
沈妈妈很满意她的口误,立刻宽宏大量地原谅了她:“没关系,以后总有机会的,我们飞回去过春节也行。”
这厢初夏却是想咬掉自己的舌头,她无比纠结地揪小熊身上的毛,都是你,都是你,一点儿预防针也不给我打,奇兵突袭的,电话那头就变成了你妈妈。她脸烧得通红,其实公寓里只剩下自己,不会有任何人看到自己的窘态,可她还是恨不得挖一个洞钻进去。从脚底心升起的害羞的情绪,心在扑通扑通的跳,仿佛沈诺就站在自己的面前对着自己不怀好意地笑,你在叫谁妈妈啊?
她觉得浑身都发烫,开了厨房的窗子,兜头扑进来的冷风,她也不觉得冷,因为只有凉风才能让她滚烫的脸颊慢慢冷却下来。窗外是满满的黑,因为地段偏僻,她居然可以看到星子,极冷的天气,天鹅绒一般的夜幕上,缀着大颗大颗水钻一般的星子,晶莹剔透,璀璨夺目,那般低,仿佛触手可及。初夏突然想起极年轻的时候在杂志上看到的一句话:伸手摘星,未必如愿,但亦不会因此而脏了手。
对面响起轻轻的咳嗽声,有人在看着自己。每一层楼有两间公寓,两间公寓的厨房是相对着的。对面公寓里住着的人是秦林。其实他们最近很少碰到,因为在家里有白露坐镇,连只苍蝇都别想飞进来,何况是白小姐视为敌人的秦林。而到了学校,其实他们的学院相隔甚远,大学老师又不是天天呆在办公室里,自己科研任务又繁忙的要命,真想制造偶遇,其实还挺不容易。秦林暗暗感慨,虽说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可倘若明月照沟渠,那么自己也无能为力。
秦林站在对面看着自己,背景是满屏的黑色,深黑的色调。光是唯一的颜色,从路面竖起的路灯和天上亮晶晶的星星,从某个不知名的侧面照过来,落在窗户旁,像一支粗糙的笔,画出了他的轮廓,眉眼不清。只那一点明亮,使黑更黑。
“初夏,”他在黑暗中出声,语调温和,不带半点儿戾气,“你现在,跟以前,很不一样。”
她愣了一下,有些不明白他具体所指的是什么。
“这些天,我一直在思考,偶尔也会想,倘若没有从前,我们只是未曾相识的陌生人,在这座城市相遇,成为同事、邻居,那么我未必会输给沈诺。有的时候,相遇的太早未必是好事,开始的太早,那么经受的考验就更多,而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来得及做好准备,去理智正确地处理这些事,所以到最后,我终于失去了你。其实折回头来找你时,我就已经做好了被拒绝的心理准备。苏鑫说的没错,你是个有感情洁癖的人,你永远无法接受背叛和欺骗,这些会让你信仰的美好分崩离析,轰然坍塌。对不起,因为是我,所以让你受到了伤害。你是如此的相信我,我却最终辜负了你。”
初夏沉默,隔了半天才开口:“苏鑫找过你?”
他苦笑:“何止是找过,还狠狠揍了我一顿,叫我离你远一点,不要再打扰你的生活。看来,我毁掉的不仅仅是你对我的爱情,还有苏鑫对我的尊敬和钦佩。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悲剧不是破坏掉原本美好的世界,而是一点点的建立起美好,然后再亲手,一点点地毁坏掉给你看。那些原本是自己亲手创造的美好最终却在自己的指尖溜走。”
“苏鑫以前很崇拜你的,视你为偶像,所以他才会反应这样激烈。对不起,我替他向你道歉。”初夏低低地叹了口气,“听说你下个学期会去C市的分校区。”
幸福就像花期
“嗯,跟中科院的一位师兄合作争取到了一个项目,分校区很重视,提供了相关设备,开过年了,我就过去。”秦林点了支烟,冷风中,红红的一点烟头,像一簇小小的火苗,一明一灭。
“祝你好运,还有,C市早晚温差大,你要自己注意身体。”
秦林无声地笑,黑暗中,他的眼睛有温润的光芒:“谢谢你,像一个老朋友一样关心我。”
他没有戳穿,初夏永远不可能再把他当成一个老朋友,他不会从她心中消失,会收藏在一桢旧匣子里,那里面存放着的,全是一些泛黄的老照片,时光悠悠,青春渐老。
她不会关心他的感情生活,她不会热心地替他介绍女朋友,她也不会跟他喝酒吃饭互相抱怨自己的恋人;时间洪荒中,他们终于成了擦肩而过的最熟悉的陌生人。
所以,所以,他不会告诉她,他最终还是跟高婉分开了,因为不想一错再错,因为他也终究是骄傲的人,不愿意凑合着过。
所以,所以,他不会告诉他,那天晚上,他跟沈诺促膝长谈,那些说过的话,他永远不可能再说。
你看你看,无物结同心,烟花不堪剪。
这一年终于快要走向尾声,新一年的钟声就快要敲响。时间啊时间,我们用力地奔跑,终有一些什么,在我们的身后遗失殆尽。
初夏收到了家里的电话时,她正在教室里监考,手机在口袋里不停地震动,她不好意思地走到走廊外接听电话。走回教室时,她面容平静看不出半点端倪,她机械而有条不紊地收拾自己的东西,微笑着告诉同事:“家里有点儿事情,我得赶紧回去一趟,麻烦你了,我这就去考务处请假。”转头看教室里奋笔疾书的学生,还不忘叮嘱:“大家好好考试,别想旁门左道的事情,放心,老师不会让你们过不好年的。”
走到学校的林荫道时才发现自己的腿是软的,每一个迈出的步子都虚浮的厉害。初夏觉得冷,她想不起来学校的校巴通常都停放在哪儿,她得走过去。快放假了,这块儿正整顿交通,校门口连辆黑车都找不到,二十分钟才来一班的公交车哪来能满足得了大学城的需要。只有到了市区,她才好找车去车站,这样她才能买到回家的票。其实要怎样去车站,她都不敢肯定。这座城市每一天都在变换着她的容颜,日新月异的都市,她不知道车站是不是在老地方,她已经好几年没有回过家,连家门的方向都记忆模糊了。
秦林的出现可谓及时雨,他是来学校办理相关手续,准备年后就转战下一个战场。迎面走来的女子面容平稳,然而她已经绕着一个花坛转了三圈,他不知道初夏发生了什么,不过他知道肯定有什么不对劲。她终于走出了那片花坛,直直地穿过她身畔,秦林开了口叫住她:“初夏,有什么事情吗?”
她看人的眼神很茫然,慢慢地摇头:“没事,我能有什么事情。就是你能不能告诉我,我们学校的校巴都停在了哪儿?”
秦林眼睛在抽筋,校巴通常都停放在学校西边的那一片水泥地上,而她一直都在往东边跑。
他终于叹了口气,伸手拽她的胳膊:“走吧,你去哪儿,我送你。”
“不用,真的不用,你自己忙你的去吧。”
“我不忙!”他唯一忙着的事就是应付她极力想要挣脱的手,“初夏,你现在的样子,我怎么放心你一个人去乘车。”
她终于放弃了挣扎,老老实实地坐进了他的车里,因为还在学校里,拉拉扯扯的,被学生跟同事领导看到了都不好。秦林是什么时候买的车?她不知道,其实她一直在刻意回避关注秦林的事。鲁迅先生说《红楼梦》: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而她的举动只有谨小慎微,以免稍有不慎,便会被秦林领会错误意思,于是两厢尴尬,大家都陷入无谓的痛苦。
一路开得不快,其实并非交通高峰期,完全可以开的更快点儿。可是路程有限,秦林不想这一程这么③üww。сōm快就结束。他不知道初夏有没有注意到他的车子是甲壳虫。她18岁生日时喝高了酒,抱着他的脖子大喊大叫,将来一定要找一个帅哥做她的专属司机,然后开着送给她的甲壳虫游山玩水。那个时候他们常常做白日梦,未来是怎样,清风逐明月,雨后的城市,恬淡如水,月在云中。
“好了,就在这里放下我便可以。”她出声打断了他绵延逶迤的思绪,微笑着把手放到车门把手上,好像下一秒钟就会在人潮汹涌中消失不见。
秦林久久的没动,他手握在方向盘上,努力压抑着眼底的情绪:“你起码要告诉我,你到底要去哪里,我起码要把你送到安全清楚地目的地,我才能安心离开吧。”
初夏镇定自若:“就是这儿啊,我不过突发奇想要逛逛街而已。壹时代正打折呢,买了衣服好过年。”
他不能非法禁锢别人的人身自由,只能眼睁睁地看她一步步远离自己的视线。秦林没有就此离开,他开着车,小心翼翼地跟在她身后,看她伸手拦了的士,上车,绝尘而去,他紧紧跟上。这座城市的路况他也谈不上多熟悉,在英国开惯了左行道,回国陡然转为了靠右行,他跟踪的很狼狈。好容易,车子停下,那幢灰蒙蒙的建筑在冬天虚弱的太阳下泛着清冷的光,像是一双冷漠傲然的眼睛,睥睨地看着那些来来往往神色匆匆的旅客。秦林认得这里,这是他往返过无数次的汽车站,没想到,这么些年,它的位置还是没有变换,只是更老了,更破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