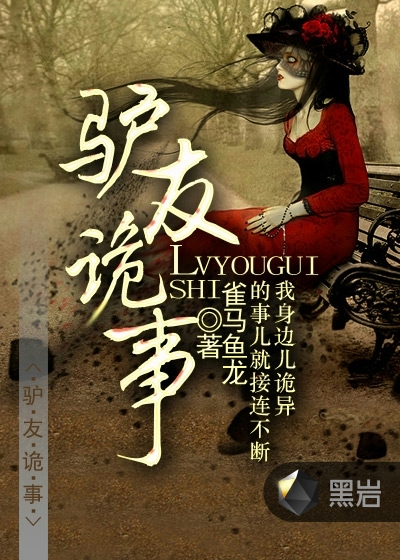阿莲的故事-第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远离家门,让两个弟弟在无声的筷子夹动间流露出难舍之情,血脉相连的亲情。我故作轻松地在全家人面前笑出声来说:长大一岁就是不一样,可你们正是长身子的时候,好东西该你俩吃。
小弟年纪小,终究控制不了自己,将饭碗往桌上一丢,头埋在桌面上,发出呜呜的哭声:姐姐别去了……别去了。大弟的眼睛也红了,偏过脸去,面朝着大门。我赶紧给身旁的小弟擦眼泪,安慰说:姐姐是进城找工作,又不是不回来了,哭鼻子真没出息。小弟一听,哭得更响,朝着父亲吼道:都怪你,不让姐姐复读。父亲望着小弟,脖子上的青筋暴出,面对儿子的无理指责,眼看就要发作,我和母亲都紧张起来,急忙把小弟拉到门边躲开。父亲端着酒杯的手在发抖,最终将酒倒进嘴里,眼睛红红的一句话也没说。
这顿午饭吃得很不是滋味,父亲喝多了,躺在床上吐了好几次,我守在他旁边给他端水擦脸,不时给他捶着后背。父亲消停后,将脸朝向墙面,挥手让我走开。
下午,同行的几个姐妹过来看我,顺便跟我说起到北京做保姆应该注意的细节,从家政公司介绍雇家,到第一次上门后如何应付试用期,甚至说到怎样给婴儿冲奶粉,讲得面面俱到,个个经验十足。可在我听来,那是纸上谈兵,我对保姆的理解仅停留在字面上,其他一无所知。内行听门道,外行看热闹,我只觉得她们说得头头是道,很是热闹,却感觉不出保姆两字的真正内涵来。
热闹了一个下午,冲淡了上午家里的凝重,母亲和弟弟们的脸上也露出了笑容,变得轻松了。随后她们叮嘱我路上该带些什么东西,就各自回家准备明天的行囊了。
吃晚饭时,气氛又沉闷下来,父亲没再喝酒,将盘子里的一只鸡腿夹给我,叫我吃下。在家人的关注下,我顺从地嚼起那鸡腿,我实在嚼不出什么滋味来,不争气的眼泪顺着脸颊流淌着,我在哽咽中嚼着那只鸡腿。
这是我在家的最后一顿晚餐,天一亮,我就要离开家的怀抱了,一阵难过涌上心头……
母亲也哭了,我印象中的母亲很坚强,是个典型的农村妇女,任劳任怨,跟着父亲过着清贫的日子,含辛茹苦抚养三个孩子,从没半句怨言。为了这个女儿,她只哭过两次,都是因为上学的事,自己再苦再累她能忍受,可她不希望女儿将来也跟她一样,在庄稼地里过完辛劳的一辈子。在我考高中时,母亲哭过一回,央求父亲让我继续上学,父亲妥协了;夏天放榜我没考上,父亲决定不让我复读,母亲又哭了,一开始也是央求,后来自暴自弃的我也站在了父亲这边,母亲擦干泪水对我也不再指望了。这第三次的哭泣,是母女难以割舍的痛,我搂着母亲瘦弱的身子一同洒泪,两个弟弟在旁也抽泣着。
作为一家之主的父亲再也端不住了,哽咽失声,说女儿是个懂事的孩子,作为长女不要怪父亲,父亲没别的本事,只知道种田,以后的路长着,得靠女儿你自己走了。我伏在父亲的肩膀上放声大哭,父亲让我再次感受到山脊一般的力量,是他支撑着我,安然度过了18个春秋。我就像立在他肩膀上的小鸟,在展翅欲飞的瞬间,产生了对未知世界的恐慌,让我更加眷恋着他的温暖与慈祥,我任由滂沱的泪水流淌在父亲的棉袄上,此刻的自己像一个孤立无助的小女孩儿,生怕在回首时,再见不到那雄健的山脊。父亲是座山,默守儿女的大山再贫瘠,也能长出青草和树苗。
阿莲的故事 5(2)
此刻的我,只感到背后的山轰然倒塌了,让我步履蹒跚。
母亲擦着眼泪帮我收拾包裹,又拿出针线来将600元钱缝进我内衣里,那是我出外闯荡的全部财产。她又从衣柜里找出自己一直没舍得用的新围巾,放在我床头上,嘱咐我明天出门戴到脖子上,外面风大天寒。
等收拾完后,一家人又坐到一块儿说起话,我一再叮嘱两个弟弟要听父母的话,好好读书,姐姐不在家,学习要自觉,不要像姐姐这样,考不上大学去给人做保姆,要努力做人上人。
母亲将我拉进房间,她最担心的还是我的身子,知道女儿有多年痛经的老毛病,北京冬天那么冷,碰冷水病情就会加重了。母亲拉着我的手不时抖动着,又抹起了眼泪。我只能劝慰母亲说,自己会照料好身子的,每月一次也痛习惯了。
因为一早就要出门,我提前上床睡觉,不休息好,明早一旦起程就没有安宁的时候了。这也是姐妹们对我的经验之谈。睡在床上,我将枕头边的那本《平凡的世界》放在胸口上,明天起床放进背包里,陪我一同起程。
我将自己对文字的全部爱好都浓缩在这本书上,它也是我离开家乡后唯一的精神食粮,以后的岁月里,我时常在夜深人静时翻开它,一字一句地咀嚼着生活的苦涩,它成了冷漠都市里唯一跟我亲近的朋友。
阿莲的故事 6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同行的姐妹们在胖婶带领下,敲开了我家门。就要出门了,一家人围着我千嘱咐万叮咛,母亲说,要是不如意就赶紧回家。父亲像无数个父亲一样,在女儿离开身边时,最担忧的还是人身安全,他那焦虑的皱纹间,无声地隐藏着无尽的牵挂。弟弟们让我一到北京就给家里写信。千言万语在这短暂的分别之时,总也说不完。还要赶很长的路,同行的姐妹都催我动身,胖婶劝慰我父母说,到了北京,到处是老乡,说出巢湖话就有人帮忙,莲子先住在我那里,把心搁在肚子里吧。
一家人站在屋前跟我挥手道别,依依难舍,母亲紧赶几步,将用布包着的荷香蛋塞到我背包里,嘱咐我路上饿了吃。
在我最后回首时,父亲背过身去,蹲在门槛边,我感到那身影一下子衰老了许多,我的视野模糊一片……
我像一只刚孵化出的小鸡崽,畏怯地尾随在胖婶她们身后,望着她们大步流星,风风火火的样子,我感到莫名的紧张,她们所追逐的世界,在我眼里一片空白。就这样,几个人在路边拦了辆三轮车,一路颠簸着到了县城,再从县城改乘中巴到了巢湖。中巴上人满为患,我们上去时,根本找不到落脚的地方,男人女人们拥挤在一块儿,倒也暖和,似乎也感觉不到窗外卷进来的寒风。汽车吐着浓烟,摇摇晃晃地开在公路上,而车上人好似都习惯了这种摇摆,七嘴八舌地说着话,都是老乡,都是赶往巢湖,也都是奔向北京。
()免费电子书下载
司机一边开车还一边开着玩笑说,明年他把车直接开进北京去,省得你们转车麻烦。
有人立刻起哄说,等你的老爷车开进了北京城,只怕我们在北京赶上过下一个春节了。
就这么一路哄笑,一路颠簸着到了巢湖。
巢湖火车站不大,人却非常多,小小的候车室早已挤不下如潮的人流,全跑到了站台上等车,都在翘首盼着那辆专列的到来。说是保姆专列,那只是个虚名,实质都是民工,因为巢湖进京的民工太多,才有了专列,又因为民工中保姆最有特色,才有了保姆专列的名堂。
这名堂不小,至少引来了不少记者的相机,也有几个摄像的穿梭在人群里寻找着最佳镜头:民工的脸都带着节后残余的喜庆,更多的是焦虑之色。
我的心情由一路紧张化作了激动,为人群而激动,也为站台而激动,望着那无垠的铁轨,我的脑海已翻腾开来,掀开波涛绵延在北上的疆域里。
火车开动了,我的心儿早飞出窗外,迎着呼啸的北风,好似车轮一般滚热。车里很闷热,像个闷罐子塞满了人馒头,到处是行囊,到处是人头,我从未见过这样的阵势,人压人,脚踩脚,动弹不得。我们被挤在车厢连接处的门边,呼出的气流翻滚在车厢里,让人透不过气来。我蹲在地上,趴在背包上,借着人腿缝隙透过的一点光亮,望着倒退着的田野,我用圆珠笔在笔记本上记录下这一刻……
这段话是我日记本里的开篇,看到这样的文字,我的思潮又似车轮卷回了那个年代,那辆列车,那密不透风的、密匝成捆的人腿,那倒退的田野……
激|情翻卷下的文字,毫无章法,随心所欲,有期盼,有惶恐,更多的是好奇。很快我便无法动笔了,那点光亮被蒙成了黑暗,耳边只有“哒哒”的车轮声,世界都成了黑暗,唯有轰然的声响在告诉人们,列车急速行驶在轨道上。
蹲在我对面的是胖婶,她是我们这群丫头里的长辈,一路像家长似的照顾着我们,生怕被人群冲散。此刻她却打起了鼾声,仿佛躺在床上,酣然入梦,四周的挤压好像与她无关,头靠在背包上,鼾声不停。
从小村到县城,再进巢湖,直到现在才算得上起程了。一路奔波到现在,我也累了,将笔记本塞进包里,学着胖婶的样子,也想睡一觉。可我怎么也睡不着,嗓子干渴得难受,四周的气味更是让人恶心,我很想立起身来透口气,可重压在身上的是个男人的膝盖,根本动不得,我忽然感到心慌、窒息,就快晕厥的感觉。一瓶矿泉水递到我手上,胖婶头也没抬,咕哝一句让我喝点水,就好了。我一听赶忙喝了一口,真是管用,慌乱的心很快便又平静了下来。胖婶又让我闭上眼睛,想点别的事,别老想着火车动静,那样会闹心。我尝试了一下,趴在那里想着我印象中的北京城,想到了天安门,感觉自己化作一纸风筝,飘出车窗,迎着呼啸的北风,一路飞向北国的那片神奇的土地……
阿莲的故事 7(1)
火车出了合肥站,基本是水泄不通了,一瓶矿泉水在我手里也早成空瓶,燥热让我浑身冒起了冷汗,我后悔没听胖婶的话,上车前没脱去笨重的棉袄,闷得我全身发痒,胸罩都浸湿了。我将脸贴近车门缝隙处,贪婪地呼吸着外面刮过的寒风,好冷却压在心头上的焦灼。我半跪卧姿势俯在背包上,僵硬的双腿阵阵酸麻,身子稍稍晃动,脚就好像踩在了漏电的电线上,动弹不得,痛苦不堪。
我努力想站起身子,活动活动近似爆裂的筋脉,可后背被一个坚硬的膝盖压着,似泰山压顶,纹丝不动。我扭动着身子,强忍着腿脚酸麻,抬头向上看去,上车后,我几乎没抬过头,一直埋头在人堆里。顶在我背上的是个中年男子,站靠在车厢边,紧闭双眼,打着盹儿。我将背部拼命向后顶开,他这才睁开了眼,略带歉意地向我一笑,将膝盖挪开,他摇晃了两下,人群随即骚动起来,有人骂那男子踩脚了。男子一脸无辜,分辩说,大家都是老乡,担待点,这小妹都被你们挤得起不了身,我是给她挪块空隙。在我周围,蹲下的大都是女人,男人都站着,姿势各种各样,像一个个竹竿斜靠在一起,相互支撑着。即便这样了,有人嘴里还叼着烟卷,“潇洒”地喷出呛人的烟雾,真不知道抽完后,那烟头该丢向何处。
可能都是乡里乡亲的,站在两旁的男人们,见到我脸红脖子粗的痛苦表情,都自觉地向外挪了挪脚,给我腾出方寸地盘,我这才在缝隙里挣脱出来,起了身,再次贪婪地深吸了一口气,尽管浑浊,比起那车外的寒风,要舒畅得多。
我望了一眼近在咫尺的厕所,发现门口也站满了人,有几个抽烟的男人挤在门外,不耐烦地敲着门。一瓶矿泉水喝下后,我很想小便,可望着眼前风雨不透的人墙,也只得暂且忍着。忍受的办法就是转移注意力,我开始留意起旁边聊天的人们,听着家乡话,我感觉这飞驰的列车好像还停靠在巢湖的站台边,开得再快,也丢不开那熟悉的乡音,在单调的铁轨“喀哒”声中,乡音听来格外亲切。
我身旁的中年男子也点上了烟,搀和到聊天里。听他话里的意思,像是修车的,他埋怨道:在北京城里摆个摊子整日提心吊胆的,城管像猫捉老鼠一样盯着,打一枪换一炮,一年到头挣到的钱还不够来回车费钱。他说自己做梦都想在街面上租个小铺头,不再干打游击式的勾当,可惜,没那么多本钱。旁边一个戴着眼镜、学生模样的人,听口音是合肥人,他跟中年男子说,摆到学校大门口不光生意好,也没人管。中年男子忙问戴眼镜的在哪所学校上学,戴眼镜的说昌平石油大学。
我很奇怪,一个保姆专列上怎么也有大学生。中年男人也问他,怎么是在巢湖上的车,兴趣不在于什么保姆专列,而是对方满口合肥腔。学生说,这年头买张车票比买人头还要难,找人在巢湖买到的全票,学生半票是不指望了,能尽快到学校也不在乎那点钱,管他什么专列,大家都是保姆吗?这话一出口,引来周围一阵哄笑。蹲在下面的胖婶一听,冒出一句来:没我们保姆,你们这些男人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