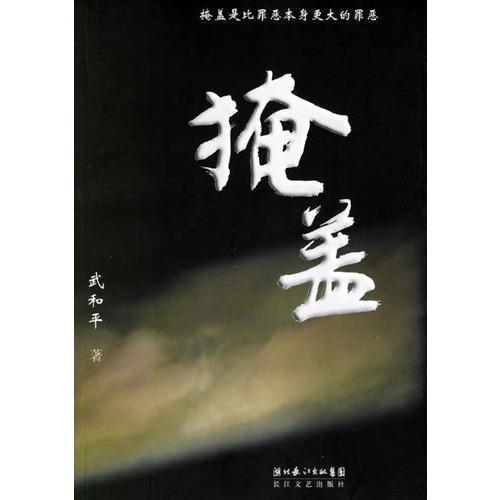掩盖-第6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头天上工,领班的矮个子绰号叫“蛤蟆”的欺生,把他分到了最底层的十五平巷掌子面装矿石,两个装矿石的民工一老一少,半天才把矿车装满,罗江自恃身大力不怯,一下子把两台矿车摞在一起在轨道上推,为的是多歇一会儿,遭了小矿工—顿挖苦。原来老矿工这几天发烧,矿车走得太快,就会把装车人累趴下,罗江细看这小矿工才十五六岁,胳膊腿儿瘦得像根筷子,说话连奶腔儿都没褪,听他说老家是贵州毕节的,便叫他“小贵州”。
罗江随后帮着装车,让老矿工歇息。到了中午吃饭的时候,井上顺着矿车送下来干粮,掌子面上一下子像从地缝里冒出了六七十号人,纷纷围拢上去抓筐里的包子。在昏黄的灯光下,罗江发现,这些人当中不少人赤身裸体,浑身上下沾满了矿灰,头发乱得像杂草,真像刚从洞穴里跑出来的灰皮大猴子,他们或站或蹲,用手托着包子,张口咬时才露出满口白牙。走动的时候,裆下晃动着卵子,谁也不觉得丑。罗江穿着衣服倒觉得不自在起来,细想这四周都是矿石,碰上了皮伤骨裂,一层布最多是遮遮羞,汗透了还得洗,所以也开始光腚干活。可干了不到半晌,肚子便饿得叽里咕噜叫,“小贵州”从石旮旯里拿出藏着的两个包子,他三下两下吞了。
就这样干到了第三天,罗江改到十二巷道装矿,遇上了一场大难。
那天上午,管卷扬机吊钩的“蛤蟆”,正在给矿车挂钩子,猛听得一声爆炸响,“蛤蟆”的手一抖,吊钩没能挂上,矿车轰隆隆就冲下来,罗江和掌子面上干活的七八个人登时傻了——因为狭窄的巷道无路可退,四周全是坚硬的矿石,跑和不跑都照样会砸成肉饼。眼见那庞然大物呼晡而下,矿井中没有一个人说话,罗江只把小贵州掩在身后,用手把他推到凸起的矿石后边。说时迟,那时快,失去平衡的矿车翻着跟头像倒扣的大锅砸下来,罗江本能地闭上了眼睛,脑子里想了一下怀孕的新婚妻子……
等他睁开了眼睛,以为到了阴曹地府,却见那些裂碎的矿石像雨点般落下,那节矿车就在离自己的脚趾半米多远地方停住了。原来,冲过来的矿车正被两边的石块卡住,七八个人算是捡了一条命。绝处逢生的人此时背靠着背挤在一起,谁也没有动,也没有人说话,在这可怕的寂静中,听得见每个人的心跳。这时候,上边传来了“蛤蟆”没了底气的叫喊声。
“有人在下边吗?”
“×你妈——”回过神儿的工人们几乎是异口同声地恶骂,骂声如雷声滚滚直冲巷口!就打从这歇斯底里的一声骂,七八个人真正成了生死兄弟。
事后,“蛤蟆”请他们七八个人吃饭,大伙喝得全部烂醉如泥,东倒西歪,罗江这才明白,这成了井下一条规矩,只要在事故中死里逃生,上井就得喝顿酒,这叫“还阳酒”,像这样的酒饭,矿井中隔三差五就要吃上一次。
矿难那天,罗江被领班派去打炮眼,开钻机的姓刘,因为一次塌方被埋在矿石里,胸部骨折,以后就穿了钢背心,那人手里拎着钻机只管打眼。可这掏眼儿的活把罗江难住了,因为巷道狭小,人只能弯腰半蹲着,要想歇一歇,只有坐下来直直腰,屁股一会儿磨出了血,可这一天监工像发了疯似的催着放炮,说是顶上见了狗头金,要把炸药装足,人炮不歇,一上午炮声连连,恨不能把整个矿山都掀上天。
已到了临近换班的时候,又是一炮爆炸,这次药量极大,震得山摇地动,罗江躲在安全洞中避烟尘。猛然间,有一股呜呜咽咽的声音自远而近,脚下顿时潮湿起来,随着地震似的剧烈抖动,一大股碎石和泥浆不知从什么地方像出膛的炮弹喷发而出,一下子把同班打钻的一个民工冲到对面的矿壁上。罗江看到,那人像被钉子钉在了墙上,脸变了形,身子成了个饼子似的平面。更大的泥浆和水流随后喷涌过来,罗江只觉得眼前被黄色糊状的东西迷住了眼睛,身体像陀螺一样失去了重心,被一股无法抗拒的力量冲进了浑浊黏稠的泥石流之中。
罗江自幼水性极好,可以一口气在水中憋上好几分钟,他此时只觉得周身刀剜似的疼痛,意识到自己已经被矿石包裹起来,并且身子像在搅拌机中被剧烈地碾压着。朦胧间,他感到被一股水流推着朝上走,一下子给掀得老高,又很快跌落在坚硬锐利的石头上。一种绝处求生的念头使他借着水势扒着矿石向上爬,一有机会就在石缝中张嘴呼吸。头顶上方,不断有石块向下落,幸亏自己裹在石堆里边没被砸伤。昏暗中他突然看到了一丝光亮,就拼着命向那里挪动着身子。随着身后又一股巨大水流的推动,他被堵在了一个什么地方,耳边听到了一阵施工机械的声响。他猛然意识到:这里可能是又一级平巷出矿的孔道。他想喊,但是徒劳的,因为嘴里全部堵满了沙石,他在拼命挣扎,已经耗尽了最后一点气力。就在这时,一件冰冷锐利的东西突然从自己腋下猛力戳了过来,求生的本能使他一下子抓住了这件东西,原来是根钢钎!他两手死死把它攥住,再也没有松开,生怕这根尖利的锐器再次戳进来。这时只听外边有人大声喊叫着,又是轰隆一声响,他就连石块带泥浆地一下子给拔出了洞口,在光亮的照射下,他觉得自己就像一个没眼睛、没耳朵、没头没脑的动物一样,但残存的意识使他知道有人把他拽了出来,帮他掏嘴里的东西,冲洗他眼里的泥沙。等他睁开眼,发现一个络腮胡子的老矿工正蹲在自己身边,便大声哭喊着,底下透水了,还有几十号人在里边,快去救他们!老矿工马上捂住了他的嘴,并且朝着他的屁股上蹬了一脚,低声骂着:你他妈的不想活了!他挣扎着倚在矿壁上,这才看明白,只见这里正在搞封堵施工,一个面带凶相的人指挥着矿工大袋大袋地搬运水泥,自己身后洞口处的泥石流和碎矿石还在向外涌流。那人见矿工们说话,便朝这儿大喊,谁在那磨洋工,想找死啊,刚才踹他的络腮胡子赶忙应付道,没有事儿,刚才这个兄弟摔倒了!
罗江一下子全明白了,这是黑心的矿主在堵口封洞,下边的人全没指望了,不知哪来的一股力量,他突然爬起来,拖着软绵绵的身子向巷口跑,并且向上一层采面攀爬。爬到掌子面,看到依然有民工在干活,就大声喊,快逃命吧,下边透水啦!十几个工人就扔了钻机和镐把,一齐跟他向上跑。这样跑一层他就喊一层,年轻力壮的民工都在他前面上了巷口,他却跌跌撞撞落在后边。
就在这时,一束强烈的手电灯光从下方斜照过来,他回头看时,只见一个壮汉手里攥着一把宽刃刀正朝自己追过来,他心中一惊,明白对方是要抓他灭口,求生之念驱使他疾步快走,为免遭壮汉的毒手,他仍然继续大声喊,意在让更多的人看到自己,使后边的人不便动手。眼看对方要抓到自己的时候,他已经逃到了矿井出口,外边一片光亮,几十个矿工正在急切询问井下的情况,罗江这才松了口气,只见身后拿砍刀的那个人已把刀围在了腰间,躲在人丛中观察他的动静……
片刻不敢停留,罗江沿着有人行走的山道一路小跑,一口气走了十几里地,觉得那人还是跟着。他跑到镇上,躲在女儿红霞上学的必经之路上等红霞。原来,罗江与矿工们相熟后,有人撮合他和当地的一个年轻寡妇成了亲,做了扫金老太的倒插门女婿。红霞是妻子和前夫生的女儿。罗江让红霞给妻子捎信,而后只身窜入了人迹罕至的自然保护区,以山林为家,与野兽为伍,寒暑春秋一下子过了六个年头。
袁庭燎一直屏息细听,目光也由审视变为了惊疑,神情中透着关切和怜悯。望着这个饱受磨难的生还者,他的心头一阵阵发紧。
“你是怎么从保护区脱险的呢?”袁庭燎给对方茶杯中加了些水,手微微地颤抖着。
“多亏有人在暗中保护着我和儿子小黑蛋儿,不然俺们早就没有命了。”罗江思维迟钝,语言缓慢。可袁庭燎还是听明白了事情的原委。
“从洞口逃到深山,拿砍刀的人一直在追杀我,我假装跳崖装死,让岳母搞了个假坟,骗过了他们。可没有想到过了这些年,这个拿砍刀的人又发现了我,这一回,他穿着警服,开了辆吓人的吉普车进了山里,我知道这下子完了。”
“就在大前天,我的儿子被他抓了去,吊在树上,我正要去救孩子,就看见一群野猪被群众轰过来,尘土过后,孩子没有了,我慌了神,追着野猪的方向进了深山,在一处很隐蔽的山坳里,我突然又看见了那台吓人的大吉普,我以为这下子完了。没有想到遇上了救星。借着那群野猪逃命的尘土,有人从树上救了孩子,又来救了我。我这才明白,在那人进山再次追杀我的同时,是他们一直在保护我。”
“你说他们?他们几个人?”袁庭燎不禁诧异起来。
“先后是两个人,一个高,一个瘦。高个子开了一辆和坏警察一模一样的车子,还特别有主意。他告诉我群众上了假警察的当,晚上要进山搜捕我,他就帮我设计了一个脱险的办法。”
“什么办法?”袁庭燎书记顿感兴趣,点着了香烟。
“他让我和搜山的群众兜圈子,乘这个机会,他把我那只大山猇用胶布贴住了嘴,套上我和黑蛋儿的衣服,在狗身上捆了两只手电筒,把狗绑在杜鹃树下的藤子上,朝裂隙涧这边荡过来,狗身上的手电筒一明一灭,引得假警察开枪,子弹打断了藤子,可怜的狗掉进了深涧……”
“看着人们都走了,我随着救我的这个高个子往回跑,半路上那台大吉普开过来接俺们,车是那个瘦个子开的,他白白的脸,很文静,可车开得很好,路上高个子和他商议,让他跟我一起回矿井找证据,自己留下来对付那个假警察。”
“这两个人是谁呢?”袁庭燎问。
“高个子姓曲,他让我看了他的工作证,另一个是记者,说他姓夏,一会儿我就要说夏记者的事……”
袁庭燎被搞蒙了,他转过脸诧异地望着严鸽,严鸽此时点了点头,眼睛红红的。袁庭燎的心头隐隐升腾起一阵不祥的预感,他催着罗江说下去,当他听完了这一段叙述,抑制不住老泪纵横,颓然跌坐在沙发上。
驾驶着悍马车的正是《沧海商报》记者夏中天,身后坐着的是罗江和他的孩子小黑蛋儿,他和曲江河取得联系,得知假警察邱社会连人带车中了圈套,已经陷在一处沼泽里,一时出不了山,曲江河要他把小黑蛋儿交给扫金老太,火速赶到鑫发金矿下井取证。
由于这台悍马车改喷了浅绿色,和邱社会那台车别无二致,进入鑫发金矿,一路上畅通无阻,直开到坑口附近的更衣室。因为天色已晚,加上夏中天改穿了保安服,身后的罗江提着工具袋,门卫也没细看证件,两人就下了井。按照曲江河复印的原始矿井图,他们绕开了八层平巷的封堵墙,从另外一条极窄的斜下方坑道钻到了下层平巷,突然听到了一阵响动声。
巷口处一个保安正在清点雷管炸药,他的身后已经堆满了从外边运来的废渣,看来是要待坑口充填后,用炸药永久性地封住这条斜道。夏中天走过去向保安点点头,让了一根烟,后边跟着罗江,被矿井帽遮住了半个脸。
“你干毬去了,这么晚才过来,不想混了?”保安说话的当儿,突然呆在了那里,因为面前的这个人分明是张陌生的脸孔,他抽出腰间的警棍就砸了过来。夏中天个子虽小,但动作快如迅雷,劈手攥住那只持棍子的手,猛力一拧,没等对方反应过来,棍已落地,他就势一拳正中那人面部,对方一仰脸把肚子挺了出来,夏中天用膝盖猛顶对方下腹部,正中睾丸,那个人一声惨叫坐在了地上。
“快说,这里是第几层?下边还有多少人?!”
“这是十一层——哎哟,”那人忍痛说,“十二层的两个人刚收工,下边没有人了。”
“胡说,那条通风管道呢?”夏中天记得图纸上标明在十一层和十二层中间,还有一条通向矿井深处输送空气的管道,并且连着上边的竖井,他恐怕对方隐瞒,就又用膝盖顶过去。
“下边几层不归我管,听说马上要从通风管道倒进水泥封填,别的事我真的不知道,饶命,别再用腿顶我……”
夏中天没有让他再说,迅速堵上对方的嘴巴,找到地上一段捆扎炸药的绳索把他捆了个结实,扔到了电闸间。
两人钻过了满是粉尘细渣的通风管道,在尽头发现一处被石块垒住的巷口,费了半天的功夫,他们终于移开了一处仅能爬过身子的小洞。罗江钻进去,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