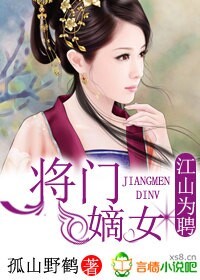一品江山-第39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正在寻思着,王珪从对面过来,远远便朝他抱拳施礼。
唐介也连忙还礼,笑道:“某非执政也要为某人说情?”
“既然他们都说过了,”王珪登时一脸尴尬道:“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了。”
“呵呵。”唐介笑着点点头道:“我要去拜见相公了。”
“子方兄请便。”王珪说着,还是咬牙轻声道:“仲方的人品我了解,胆大妄为或许是有的,但绝不会不顾百姓死活,更不会将这样攸关国运的工程,当成打击敌人的武器。”顿一下道:“他进献水泥,完全是出于公心的……”
“嗯。”唐介微笑着应下,才平静下来的一颗心,却再次起了惊涛骇浪。暗道这是第几个给陈恪当说客的相公了?包拯、欧阳修、还有平素里百言百当、不如一默的王珪,以及更早些时候的曾枢相……
前日曾公亮就专门找到他,言道自己曾经亲自测试过水泥,可以保证这种新材料没有任何问题……用水泥重修大顺城,就是他批的。曾公亮还拍胸脯保证,陈恪是个很靠谱的人,绝不会犯这种错误的。
算起来,两府八公,竟有一半力挺陈恪,真让人惊掉下巴。平素看不出,这厮竟如此得人心。有四位相公护着,谁也动不了他!
不知不觉来到首相的签押房外,唐介稳一稳情绪,迈步进去,便见富相公一脸憔悴的坐在大案后,似乎正在出神。
书吏唤了一声,富弼才回过神来,看是唐介,嘴角牵起一丝笑道:“老夫不知怎地,竟有些恍惚了。”
“相公是太累了。”唐介轻声道。
“快坐吧。”富弼笑笑,吩咐随从道:“把官家赏的小龙团拿出来……”
“不必了,”唐介忙道:“我已经在醉翁那里吃过了。”
“哈,那就不暴殄天物了。”富弼笑道:“醉翁之意不在酒,怕也不在茶吧。”
“是。”唐介点点头道:“他关心自己的学生,问了问我具体情况。”
“什么情况?”富弼缓缓问道。
唐介便简略汇报了和陈恪对话的内容,而后道:“从目前的情况看,决堤处的水泥出了问题,主要还是违期施工,且偷工减料造成的。”
“他既然这么明白,为何之前从不预警?”富弼沉声道:“陈仲方何时变成,只会靠奏章说话的哑巴了?”
唐介心说果然,富相公也对这点无法释怀。
“相公这就有些苛责了。”唐介简直不相信,这话能从自己嘴里说出来:“从头到尾,陈仲方都坚决反对二股河工程,何曾见相公听过来着。怎么能出了事,又怨人家没有死谏?”
第三五九章 说客(下)
…
富弼本来不想追究陈恪的责任,他对这个年轻人的印象向来极好。陈恪数年来不避毁谤、不辞辛劳,为朝廷立下了许多汗马功劳,却一直靠边站。虽然并非富弼的意思,但他身为首相,不能保护属下、维护公正,已经深感内疚了。如今怎会伙同他人,栽赃构陷于他呢?
就算那个说不清的问题,他也只是有些失望而已,远不止于欲加其罪。
富相公是日三省乎己的君子,扪心自问换了自己,也不会比陈恪做得更好……谁也不是圣人,也不能要求别人是圣人,既非责任所在,又已经尽到提醒义务,断不该再为此事苛责了。
相反,他一直担心唐介的态度,现在见对方先替陈恪说话,却又有些吃惊……难不成赵宗绩一党的实力,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强大若斯?连唐介这样的官场屠夫,都已经被收编了?
他却是想多了,殊不知人家唐中丞,只是抹不开两位老友的面子,又觉着陈恪确实没什么过错……放着真正的罪人不问,却纠缠陈恪尽没尽心,这是哪门子道理?
于是陈恪的问题被放到一边,两人商讨起如何给这个案子定性来。关口是让赵宗实承担多少责任?庆陵郡王作为河道总管,不但责任是不可能的,但主要责任还是次要责任,是无心之失,还是渎职无能。轻重虽在一笔之间,却极可能影响到朝局、国本,更不用提他们自身的荣辱了。
~~~~~~~~~~~~~~~~~~~~~~
就在两人为二股河一案伤透脑筋之际,数匹快马自西而来,从万胜门径入京城,直奔位于新门内大街的祁国公府。
祁国公正是富弼富相公的封爵,相府门口,就是亲王也要下轿,岂容等闲喧哗?门口的卫士刚要喝斥,却看为首之人有些眼熟。有资深的卫士定睛一看,大吃一惊道:“公子,你怎么……”
那一身穿青衣角带丧服的年轻人,正是富相公之孙富直柔,他翻身下马,带着哭腔问道:“我爷爷呢?”
“老公相在衙呢……”门卫答道。
“快带我去见他,”富直柔急声道。
政事堂中,富弼和唐介正在说话,突然听到门口有慌乱的脚步声,紧接着富相公的管家便推开门进来。
“你有何事?”富弼皱眉道。
管家面色苍白,还未答话,富直柔便跌跌撞撞进来,扑通跪在爷爷面前,放声大哭道:“爷爷,老奶奶没了……”
“什么,你说什么?”富弼失声道。
“老奶奶已于前日,在家中仙逝了!”富直柔大哭道。
富弼如遭五雷轰顶,只觉一阵天旋地转,跌坐在椅子上……
与富相公值房相对的,是韩相公的值房,看到富弼的孙子穿着孝服,冲进对门,韩琦淡淡对吴奎道:“还好来的不算太迟。”
“可见王爷乃天命所归,见着眼前这关要悬,连阎王爷都出手相助。”吴奎露出如释重负的表情,说着又心一揪道:“可是历来宰相遇丧皆起复,只怕不会有什么影响。”
韩琦冷冷瞥了他一眼,吴奎便唬得缩起脖子,不敢多言了。
~~~~~~~~~~~~~
第二天早上,是例朝的日子,卯时已过,却不见富相公的身影,领班大臣的位置上,立着面色肃穆的韩相公。
这是富相公任首相数年来,第一次没有按时上朝点卯。不过,大小官吏并不感到惊奇,因为头一天,消息灵通人士,便已得知富相公的母亲,在洛阳老家病逝的消息。今日一早在待漏院,更是传得人尽皆知了。
首相丧母,百官其哀,今日朝堂之上也显得特别沉闷。
排班问安后,官家问富相公为何缺班?
韩琦便出列禀报道:“启禀陛下:臣等于昨日得知,首辅富相公令堂,已于三日前病逝于洛阳家中。富相公闻讯哀恸不已,已穿孝服在家守制。”
其实官家昨日已经知道了,只是在朝堂上必须有此一问罢了, 闻言面露悲痛道:“悲乎富卿,与公同哀。”说着对王安石道:“你替寡人拟一道谕旨,以最高规格抚恤。胡总管,待会儿你替寡人到富相公府上宣旨抚恤。”
人一起应道。
“启奏陛下,”知通进银台司兼门中封驳事韩维又出列,双手捧着道札子:“昨日接到富相公《请即日返乡丁忧状》,进呈陛下。”
胡言兑看看赵祯,赵祯缓缓问道:“朝廷制度如何?”
翰林学士胡宿答道:“国朝有‘丁忧’制度,官员父母去世,应弃官居家守制,服满再行补职。”顿一下他轻声道:“但对于宰相,按例可带丧起复。”
“那就先接下吧。”赵祯点点头,胡言兑才收下了富弼的奏章。停了一会儿,皇帝又对王安石道:“谕旨中加上一句,愿公以国事为重,节哀顺变,朕翘首以盼早归。”
这就算是为夺情起复埋下伏笔了。群臣听了心里酸溜溜的,但那是宰相的特权,羡慕不来……
“今日骤闻噩耗,不胜悲痛,就此退朝吧。”赵祯说完叹口气,挥挥衣袖道:“尔等下朝后,可自去富相公府中致祭……”虽然不算辍朝,但对于大臣丧母来说,这也是极大的礼遇了。
“遵旨……”
群臣出了宫,便各自回家去换素服,写挽幛。也有那消息灵通之辈,早在车中备下了青衣角带、白布竹竿,换上后便往祁国公府而去。
此时的国公府中,已是缟素一片,客堂被临时布置成灵堂。尽管接到准许丁忧的旨意后,富弼便要返乡奔丧了,但国公府中的丧仪依然不能马虎。
富相公平素持重厚道,待人公正,百官都十分尊敬他。加之宰相丁忧,不过是走个过场,过上一两个月,又会被夺情起复,故而汴京城的大小官员,一个不落全都前来致祭。
按照京城吊仪,每位前来的官员都会送一道挽幛,以及白包一个。灵堂里很快便放不下了,就摆在院子里,院子里摆不下,就摆到大门外,到后来,整个一条大街上,都摆满了灵旗挽幛。前来吊丧的人仍络绎不绝……
富弼本就悲伤不已,看到满堂满院的挽幛挽联,更是难以自禁、哀毁骨立,几乎哭得要晕死过去。
家人见他摇摇欲坠,连忙将富弼扶到后堂书房歇息,前面由他的儿孙打点。接到报丧之后,富弼就没合过眼,丧母之痛加上大半天的应酬,老相公已是乏极了,一歪到书房的卧榻上,就呼呼睡着了。
也就是刚打了个盹,富弼又被家人唤醒了。要是一般吊客,倒也不会来骚扰他,但前来吊孝的是韩琦韩相公……
富弼忙强撑着爬起来,戴上孝帽子,在儿子的搀扶下,来到灵堂。
灵堂中,韩琦一身素服,正在哭祭,富弼向他行了礼,便请他到后堂就坐。
~~~~~~~~~~~~~~~~~~~~~~~~~~~~
书房中,一身孝服的富弼,与一身素服的韩琦东西昭穆而坐。
两人二十多年的交情了,又在相位上共事经年,虽然不融洽,但还算能维持,此刻富弼神情憔悴,韩琦的眼里也含着泪。
韩琦轻声安慰富弼道:“老夫人享寿八十有三,是喜丧了,彦国兄节哀……”
“唉,先妣春里便传病重,我却一直没有回家探视,更没有床前侍疾哪怕一天,实在是不孝啊。”富相公叹息道。
“彦国兄身肩国务,大宋一日都离不开你,是以一人之遗憾,为千万人谋福祉,老夫人在天之灵,一定会欣慰的。”
“多谢稚圭安慰。”富弼挤出一丝笑道:“我明日便要回乡奔丧,国政繁冗,劳烦老弟多多担待了。”
“彦国兄多虑了,”韩琦难以捉摸的笑道:“不出月余,官家就会夺情起复,这副重担,还是兄长来肩!”
上午时胡言兑来传旨抚慰,官家的话里,已经暗示了他会起复,这也是惯例了,富弼也觉着理所当然。但不可能大喇喇的承认,否则他富弼岂不成了贪恋权位、罔顾孝道的小人?于是富弼摇摇头,拽了句文道:“此乃金革变礼,不可用于平世。”
意思是,夺情起复是战争时期的权宜之计,现在天下太平,再这样就不合适了。
傻子都知道富相公是在假客气。就好比请客吃饭时,不小心点的菜不太够,主人要起身再加几个菜,客人们一般都会说‘饱了饱了,不用加了!加了我们也吃不了!’
这就叫假客气,只是一种客套而已,你要是信以为真,以为人家都吃饱了而不去加菜,肯定就把客人得罪了。
一般稍微懂点人情世故的,就不会犯这种错误。然而我们独一无二的韩相公,却好像不懂什么叫‘人情世事’,竟漫不经心地回了一句:“彦国兄所言极是,此非朝廷盛典也……”
第三六零章 绯闻(上)
…
‘此非朝廷盛典也。’换成白话就是,这不是什么值得提倡的事儿……
富弼难以置信的望着韩琦,韩琦摸了摸鼻子,笑道:“彦国兄不要当真,我是开玩笑的。夺不夺情自然有朝廷旨意,岂是我们自己能说了算。”
“是啊……”富弼艰难的点点头,后面韩琦再说了些什么,他一句都没听进去。脑海中光萦绕着那句‘此非朝廷盛典也’!
富相公自问一生清廉自守,问心无愧,不会在青史上留下任何污点。但韩琦的话,就像一根刺一样,深深扎进他的心窝,想一想都觉着刺心——如果他接受了夺情,岂不就成了官迷心窍,还怎么为百官之师,名垂青史?
翌日一早,带着这样沉重的心理负担,富相公返回洛阳丁忧了。
汴京城中,自然由次相韩琦主持政务。不过因为从上到下,都认为富弼回去悲痛一阵子,就会回来继续当他的首相,所以韩琦依然任昭文馆大学士,至于集贤馆大学士的位子,则暂时虚悬。
虽然韩琦依然在原先的值房中,但大宋朝的权柄却已渐渐向他倾斜。
“恭喜相公,贺喜相公,”吴奎虽然是枢密副使,却整天往政事堂窜,实指望着巴结上韩琦,能从西府调到东府来。这不,由韩琦‘暂署中书门下事’的旨意一下来,他便跑过来道贺了:“终于得掌我大宋相印!”
集贤相之所以是首相,就是因为‘中书省印’在他手里,而昭文相两手空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