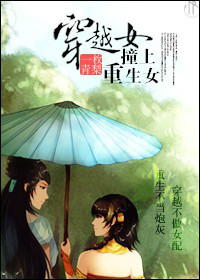穿越1879-第1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李经述进了家门,妹妹李菊藕高兴地迎了出来。脸色绯红的李菊藕,穿了一件李经述从美国给她带回来的西洋白裙子,显得更加漂亮。她挽着李经述的手,一个劲问李经述:“二哥,你看我今天穿的裙子漂亮么?”
李经述笑道:“漂亮极了!你都长成大姑娘了,到出嫁的年龄了哦!要是谁能娶上你,可真是好福气呀!”
李菊藕害羞地点了点头,道:“二哥,你还没娶媳妇呢,就惦记着我的婚姻大事了。我不着急,一定要找一个自己喜欢的!快说,你和容雪姐姐准备什么时候订婚?我都听父亲跟母亲提起过这事了,说等容大人一回国,就给你提亲去。”
“是吗?”李经述微微一笑,现在自己都十九岁了,在古代确实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这时婚姻确实讲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李经述自己也懒得考虑这问题,便走过去摸了摸弟弟李经迈的头,捏了捏他胖乎乎的娃娃脸,笑道:“经迈也长这么高了!”
李经迈这时才六岁,一双眼睛又黑又亮,很讨人喜欢的面相,像他的母亲莫氏,但他是庶出,在家里没地位,只有李经述待他如亲弟弟。李经迈平时就胆子小,话很少,于是朝李经述傻傻一笑,露出两颗小虎牙。
李经述便弯下腰去逗李经迈玩,心里备感轻松。肩头的历史使命,使李经述提前成熟,但那并不是他真正的面目,更多的,是一种速成的缺乏根基的应付假象,李经述在亲近的家人面前,还是会表现出孩子般的顽皮和青涩。
就在这时,李经方走过来,看李经述和李经迈玩得火热,嘲笑他说:“经述,你都多大了,还跟偏房的小孩子玩呢?你今年的乡试也没参加呀!这次回来准备呆多久?”
李经述直起腰,做了一个伸展运动,冷冷回答李经方道:“我是在跟弟弟玩呢,你最好搞清楚,经迈再怎么庶出,他也是父亲的亲生儿子。”
李经述这句话暗示李经方不是李鸿章的亲生儿子,李经方自讨没趣,气得脸都黑了。
李经述见李经方还站在他的面前,一语双关,道:“大哥,我再跟你说一遍,我们是一家人,如果不能相亲相爱,那就各走各的路,别挡我的道!”
李鸿章回家后,一家人吃过晚饭,当时一轮明月挂在高空。李经述在院子里跟李鸿章谈起想回国训练海军人才的事,为以后成立水师做准备。
李鸿章捋了捋花白的胡子,点点头道:“现在士大夫和淮军将领中有一些人,思想迂腐,只想着自己升官发财,耻于练兵。你有这样的想法,难能可贵,为父一定大力支持!正好,北洋水师学堂开办一年,去年学额未满,成效不明显,招来的学生中也少出色之才,为父也正想去学堂看看是怎么回事!你回来了,就去协助总办吴仲翔和严复进行改革吧,希望北洋水师学堂能开北方风气之先,立中国兵舰之本!”
原来,经过极力争取,1881年8月,李鸿章就已经在天津成立了北洋水师学堂。严复还应李鸿章之招,从福建船政局调津任天津水师学堂的总教习。
李经述知道,这位历史上翻译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的著名启蒙思想家严复,此时才二十八岁,不过严复确实是一位难得的海军人才——福州船政学堂第一届毕业生,先后在“建威”、“扬武”两舰实习5年,1879年毕业于英国皇家海军学院,回国后担任福州船政学堂教员。所以对见严复,李经述的内心还是颇为期待,他会不会让自己失望呢?
李经述回国休息了两日,便去了北洋水师学堂。学堂在天津城东八里、大直沽东北的东机器局旁。那天秋高气爽,蓝天白云,阳光洒在北洋水师学堂的草地上。李经述走进学堂一看,这学堂的环境很优美,堂室宏敞整齐,不下一百余椽。楼台掩映,花木参差,晨读、休息之所无一不备。另外还有观星台一座,以备学习天文者登高测望,学堂的硬件设备很不错,但是学堂里冷冷清清,见不到几个人。
一身长袍的总办吴仲翔,到门口来迎接李经述,介绍水师学堂现在设有驾驶、管轮两个专业,今年原本计划各招收300人,但到现在快开学了,也就100来个人报名。
李经述在朝鲜时,到淮军大营中和士兵们聊过天,在1882年,不仅士大夫和淮军将领耻于练兵,多数年轻人也是耻于当兵的,因为当兵的没社会地位。当兵的人,多是为了军饷,要养家糊口!李经述看了一眼从身边走过的两学生,穿得破破烂烂,面如菜色,像营养不良,他似乎明白了北洋水师学堂办不好的原因,问吴仲翔:“北洋水师学堂的学员每个月学堂给多少生活费?”
“生活费?”吴仲翔道:“李公子说的是赡银吧?每个月学校发给每一位学生赡银一两!”
“才一两?”李经述说:“吴总办,你马上重新发布招生布告吧,每个学生每月给白银八两,不,十两!中国海军现在最缺的是什么?人才!这钱一文也不能少!少买一艘炮舰,就可以培养一大批海军技术人才了!”
十两银子在当时的天津也是一大笔钱,这意味着一旦谁家有学生入选学堂,即便是八口之家,其生活也就有了保障,每个月还能吃上顿肉。李经述有钱,当然可以这么任性,问题是,北洋水师学堂也没这么多办学经费,吴仲翔吞吞吐吐道:“这事下官得请示中堂大人,学堂办学经费紧张…”
吴仲翔的话还没说完,就被李经述打断了:“能用钱解决的问题,就不是问题!不就是一年三万六千两白银吗?这钱我出了!你在布告里还要写上——在学习期间,学生若卓有成就,学堂从优重奖,每年还给发五十两白银的奖学金!另外,朝廷的水师破格录用!”
第27章慈禧的权欲
北京的春天,来得比较迟。故宫护城河边的柳树,一点绿意都没有。阳光也透着几丝冰冷,在紫禁城血红色的城墙上投下斑驳的暗影。这座四四方方的老皇城,将宫内宫外分隔成两个世界。中国这时有四万万人,终其一生,有机会走进这座权力牢笼的人,不会超过四百。没有人走动时,这里显得异常安静,安静得让人感受到难以忍受的孤独。
四十八岁的慈禧,立在紫禁城西边的储秀宫外,雍容华贵的衮凤长袍拖到地上,脚上是一双绣花鞋,鞋底中央是四到六寸的木底,使她的身材显得更加修长。她一头秀发,用一根别致的玉簪盘在头上,脖子上挂了一串色泽很好的珍珠项链,左手腕上带着两只雕有兰花图案的金手镯,她望着储秀宫内的雕花门窗,铜镜妆台,檀香木椅,一切都还是她初进宫的模样!
此时的慈禧,已贵为圣母皇太后,慈安也死了,她搬入了长春宫,但她还是很喜欢储秀宫,这是她1852年初入宫时居住的地方,在这里有她的青春,有她的欢笑,她还这里生下了同治皇帝载淳。每当慈禧心情不好时,她总喜欢回到这个梦开始的地方看看。
慈禧今天的心情很不好,是因为军机大臣李鸿藻在策动“清流派”弹劾李鸿章,这件事情恭亲王也知道,即便不支持,也是默许的。支持弹劾李鸿章的人很多,都是重量级的大臣,翁同龢、张之洞、张佩纶,甚至拿枪杆子的左宗棠,他们想借中法之战扳倒李鸿章。这在慈禧看来,不仅是要打她的脸,更是要把她赶回西宫的信号。
这一年,光绪皇帝已经快十三岁了,古代皇帝一般到十四五岁就该成婚亲政了。如果任由恭亲王、李鸿藻、左宗棠、翁同龢把李鸿章搞掉,光绪皇帝亲政,她铁定要靠边站了,这朝堂之上,她最信任的人,以前是恭亲王,现在是李鸿章。
恭亲王曾经是慈禧最亲密的战友!咸丰帝死后,慈禧的儿子同治继位,肃顺等八大顾命大臣企图专权,权力欲极强的慈禧非常不满,联合在京主持和谈的恭亲王奕訢,发动辛酉政变,逮捕了八大臣,杀了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肃顺斩立决,其他人革职,终于垂帘听政。那一年,慈禧才二十六岁。
但现在,恭亲王对慈禧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威胁。虽然被革除了议政王头衔,但恭亲王仍任领班军机大臣与领班总理衙门大臣,掌管军机处和总理衙门——军机处在清朝地位特殊,从雍正年间开始,军机处虽然都是兼职,但总揽军政大权,凌驾于六部之上,军机处加上皇帝,就是大清的最高决策机关。而总理衙门,会跟洋人打交道。他最近和李鸿藻、翁同龢走得太近了,以至于慈禧怀疑他们要勾结起来让光绪皇帝很快亲政,这是视权欲为性命的慈禧太后绝对不接受的!
而李鸿章,慈禧是绝对信任的。当年慈禧太后拉拢慈安太后,在光绪皇帝即位的问题上独断专行,绕过了军机处,对固守正统的清流大臣也是极大的刺激,他们认为慈禧违背了清朝祖制。对光绪的继位,宗人府是反对的,因为这坏了嫡长子继承这个大统,当时很多清流大臣也不满。慈禧就在宫里她说她生病了,李鸿章就推荐了薛福辰去给慈禧看病。薛福辰实际上是李鸿章派的一个密探,告诉她李鸿章全力地支持她。有了李鸿章这一支淮军驻扎京师,慈禧才肆无忌惮立了光绪皇帝。从那时候开始,慈禧对李鸿章的信任无以复加,很多时候,只有李鸿章懂得她的心思。
一想到这么多人要弹劾李鸿章,慈禧的心情就有几分焦虑。
慈禧走进储秀宫里,坐到梳妆台前,李莲英上前帮她梳头,望着铜镜里一头乌黑发亮的长发,慈禧心里很得意,嘴角露出微笑,但看到额头日渐增多的皱纹,慈禧又不禁叹了一口气。是呀,她已经四十八岁,光绪皇帝一天天长大,她一天天变老,这是多么残酷又不得不接受的事实,快到更年期的慈禧太后,内心的烦躁感和孤独感越来越强烈,感觉到前所未有的危机!
这时,储秀宫外的小太监来报,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到了,慈禧宣见。
李鸿章很奇怪,储秀宫根本就不是议事的地方,慈禧太后为什么在这里召见自己呢?他心中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慈禧见了李鸿章,让李莲英将一叠抄有朝廷官员奏折的《邸报》交给李鸿章,上面全是各大臣要求撤回留美幼童和弹劾李鸿章的奏章。
李鸿章道:“老臣刚派儿子去上海稳定了股市,就又有这么多大臣旧事重提,迫不及待跳出来要求撤回留美幼童,还集体弹劾老臣,这背后肯定有大人物在谋划和支持!”
慈禧冷笑一声,道:“他们这些人,表面上是弹劾你,实际上是在打哀家的脸呀!”
慈禧的身后,站着的人,除了李莲英,还有荣寿公主,她是恭亲王之女,十二岁时慈禧赐名,做主指婚于额驸景寿之子志端,结果她十七岁时,额附志端就因病去世,她没生儿育女,没有精神寄托,所以性格有一点古怪,一直跟在慈禧身边,和慈禧很亲近,参与一些政事的讨论,她从来不为娘家人说话,一心向着慈禧,所以很讨慈禧太后喜欢。
但这一次,慈禧和李鸿章有要事相商,却让荣寿公主退下了,连李莲英也被支走了。储秀宫里,只剩下慈禧太后和李鸿章两人。
慈禧开口对李鸿章说:“李中堂,你和哀家,相识已经二十年了吧,你老实说,哀家现在处理朝政,是贪恋权力吗?”
李鸿章摇摇头,说:“太后垂帘听政,日夜为国事操劳,不了解你的人才会说你贪权,实际上,您是迫于形势,不得不主持大局。”
慈禧叹了一口气说:“你说得好,但有些人不这么想呀!没有哀家,长毛和洋人,还不知道亡我大清国多少回了呢。世人却只看得到我凤冠上的宝石,看不到我也是一个守寡了二十多年的女人。就像他们只看到咸丰是至高无上的皇帝,却看不到他是一个纵欲过度、体柔多病的男人。对于一个女人来说,丈夫就是她的天,我的天早塌了,亲生儿子也死了,除了权力,这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能让哀家安心踏实睡觉呢?”
李鸿章问道:“那么,太后打算怎么处理‘有些人’?”
慈禧说:“这次中法之战,不管结果怎么样,哀家打算让恭亲王回家养病去!还有那帮清流大臣,哀家早就想收拾了。这话,哀家只和你一个人说。”
李鸿章说:“啊?恭亲王有病?老臣没听说呀!听太后的意思,现在您也支持中法开战?”
慈禧点点头,说:“现在恭亲王、左宗棠、翁同龢、张佩纶、张之洞等人都主张开战,连醇亲王也说,与其赔款给洋人,不如拿赔款当军饷,去和洋人一战!人人喊打,哀家不同意都不行了。”
这帮人中,时任山西巡抚的张之洞特别积极,张之洞陈抗法事,多有谋划。张之洞也是个人才,打小聪慧异常,他爹是贵州的一个知府,26岁名列殿试一甲第三名,当即被分配到翰林院工作。翰林院是个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