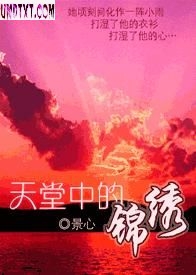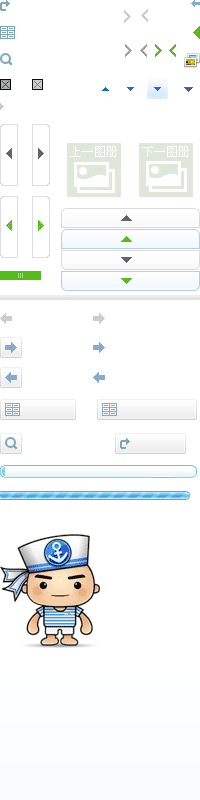天堂也有一双媚眼-第2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谁闹别扭了?我们本来挺好的。”说完,我偷偷瞟了对面的铁木儿一眼。我是笑的,但是笑得挺尴尬。
我以为铁木儿会像贝多芬那样皱个眉头,或是哼上一声表示轻蔑,然而,没有。她跟我眨了眨眼睛,冲圣虹姐说道“我们俩很谈得来,没什么可吵的。”从她的声音,我能感觉到一股子热带的气息,这是否预示着我们之间的坚冰已经打破,可以正常通航了,我还说不准。
“那就再好不过了。”圣虹姐一边说一边将茶杯在托碟里转来转去,看也不看铁木儿,在她心里的那杆秤上,那个准备要派在我头上的芭蕾舞演员显然比铁木儿份量重得多。
大家围着篝火跳舞的时候,我犹犹豫豫地向铁木儿伸出了手,铁木儿却毫不犹豫地把手递给了我,让我握着。伴奏的音乐是彭哥从古董店挖掘出的老唱机,原产日本,总坏也总修估计换配件换得已经没多少原器件了,但是,彭哥还是很珍惜,是不是拿出来炫耀一番。不过,多欢快的音乐,在老唱机上一放,都得慢半拍。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挺尽兴的,不用说,是因为铁木儿的缘故。我们两只手攥得紧紧的,我仿佛终于抓住了野马的缰绳。心里一下子就踏实了。
至于,这匹野马还会不会脱缰而去,我却一点把握也没有。
“你还在生气吗?”铁木儿跳舞跳得气喘吁吁的。
“我什么时候生气来着,哪敢呢!”我说。
“不生气才怪呢。”
“我真不生气,我只是好奇——你的那些个男友怎么样了?”我酸溜溜地问道。
“吃醋了吧,我哪有什么男友,是气你呢。”她嘿嘿笑着。
虽然天寒地冻,大家还是跳出了一身的汗,每个人的额头都散发着热气,像黄昏时的一缕缕的炊烟,篝火熄灭的时候,已经是午夜时分了,大家才散去。这是个无比快乐的夜晚。
我们俩就这样莫名其妙地反目,又莫名其妙地和好,已然成了一种恶性循环。我不知道以后会怎样,我也懒得去想这个,只要跟她在一起,我就满足了,谁叫我们是一对欢喜冤家呢。
()免费电子书下载
那天晚上,我们没有Zuo爱,也许是因为我有了某种心理障碍吧,不知为什么陆清的面影总是在不合时宜地时候突然出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令我特别沮丧。结果,整整一个晚上,我惟一能做的事情就是竭力来掩饰自己的沮丧情绪,尽可能地不让她看出来。还好,她坐在我的腿上,让我轻轻摇晃着她。听她说这说那。
她说累了,就跟我一起拼图,那是一幅复杂的泰坦尼克号巨轮的平面图,一个拼图高手,恐怕也得用上半天时间才能完成,像我们俩这样的学徒水平,起码得用仨月时间,还是少说。铁木儿留了个爱米莉 ?狄金森式的发型,松松地挽在脑后中间还留着一道中缝她还曾拿出爱米莉?狄金森的肖像画,让我比较,谁更好看些。我当然说她好看,她就愉快地笑了,然后又继续拼图。
拼累了,我们就躺在地板上睡了。
睡半截,我被冻醒了,就爬起来,把她抱进被卧里,搂在一起再次入梦。
我醒来的时候,第一眼就看见铁木儿的笑脸,双颊呈紫罗兰色,她俯视着我。“早安。”我说。我跟她在一起,尽量少说话,最好用海明威电报式的简洁语言,以避免又无意间重复了那个新西兰小子的哪句话,挑起新的争端。
“你也早安。”她用手撩拨着我的下唇,像拨弄着琴弦,她变得更像一个女人了,同时还流露出一个女人所具有的柔情蜜意,这种柔情蜜意很容易使我联想起蓝色鸢尾花或别的什么花。“以后我们再也不吵嘴了,好吗?”她说。
我从来就没想过要跟她吵架,吵架的都是她。当然,我不能这么说,我只是举起她的手,吻了吻她的手指尖,制造一种此时无声胜有声的艺术效果。
果然,铁木儿像是受了感动似的,把脸颊搁在我的胸前,仿佛那里是一个码头,远航的船只可以再那里停一停,靠一靠。
天堂也有一双媚眼 48
好几次,我都拿起电话来,想给陆清打个电话,向她解释一下,毕竟,错不在她。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念头就像浮标一样在我汹涌的脑海里沉浮。
可是,跟陆清说什么呢?说我们之间一切都是一场梦,醒过来之后,最好就赶紧把它忘掉……能这样说吗?显然不能,既便是此时此刻,只要一想起她来,我仿佛就感到她嘴里的热气暖融融地呼在我的脖子领里边。
我知道,陆清是无辜的,她是三人游戏的牺牲品,我也知道,她的眼睛像荆棘一样,什么都逃不过它的锋芒,她也许早就把这些看透了,却仍然投身进来,成为刺激性游戏的一员。也许,她只是试探一下,然后便退出去,去做一个旁观者。
不然,这么久,她也不曾主动跟我联络,现在,我的电话铃声一响,心里就怦然一动,以为是她,接听以后,发现不是她的时候,就很失落。
天堂也有一双媚眼 49
花枝放寒假了,回到了村里。大家都要为她接风洗尘,末了还是彭哥和圣虹姐先拔了头筹,那天,不但叫上了我们几个,彭哥还特意邀请了房三爷和秀大妈两口子。花枝经圣虹姐的一番乔装打扮,简直让人认不出来了,太摩登了,太像巴黎街头的白领姑娘了,幸好花枝的脸颊上还有乡下姑娘特有的两朵红晕在燃烧。
花枝无疑是今天的焦点人物,在柔和的灯光下,在鲜花的簇拥中,她站在房间中央接受着众星捧月似的祝福,她有点忸怩,不断地把重心从一只脚移到另一只脚。
“我们的小公主,今天的致酒词应该由你来!”圣虹姐热情洋溢地说。
“我会说啥呀。”花枝笑嘻嘻地推却道。
“要我说呀,还是房三爷先开个头吧,他是这里最年长的。”我提议。
房三爷倒显得落落大方,举了举杯说:“你们都是好人。那就为好人一生平安干上一杯。”我注意到,房三爷喝的是朗姆酒,一饮而尽,眉头都没皱一皱。我原本以为他会喝不惯的。后来才知道,当兵那时侯,他在战壕里常有洋酒喝,那是美国飞机空投的。
推杯换盏,房间里弥漫着一股热气腾腾的节日气氛。可惜,没有我的份,秀大妈剥夺了我和马大叔饮酒的权利,我只好喝茶,嘴角上再叼上一支烟,看看这个,瞅瞅那个,仿佛置身事外。
“你真的戒酒了?这倒是一件天大的好事。”紧挨着我身边的铁木儿小声说,我不知道她是夸我还是骂我。
“既然我答应过秀大妈不再喝酒……”
“就必须一诺千金是吧?”铁木儿挤了挤眼。
“够了,你就别趁火打劫了,你明明知道戒酒的滋味并不好受。”我可怜巴巴地说。
她咯咯笑了起来,“好了,好了,放你一马吧。”后来他们一干人拥着花枝卡拉OK去了,只留下我和房三爷及秀大妈夫妇,我们喝着热茶,一派休闲。这时候,我记起了房三爷那天讲了一半的故事,便央求他接着往下江,我想听。秀大妈也在一边替我说情,说是对年轻人进行传统教育很有必要。房三爷穿着一件翻毛的羊皮坎肩,因为热,就敞着怀,露出里面一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中山装的扣子有好几种式样,一定是原先的掉了,又随便找几个缝上的。
“讲讲就讲讲。”房三爷咳嗽了一声,爽快地说。
圣虹姐出来给大家续了一回茶,就又回到音乐间去了。今天她表现得很不错,对特别邀请来的当地客人,几乎可以说是关怀倍至,彬彬有礼。
()好看的txt电子书
“这个小媳妇挺周到的。”房三爷冲着圣虹姐的背影说。
我等着听他老人家的故事呢,所以就敷衍似的哼了两声,唯恐我一搭茬,他又把话题扯到别的地方去——上年纪的人都有这毛病。
“上一回讲到哪儿来着?我都忘了,人老,记性就差。”房三爷拍拍自己的后脑勺。
“讲到您当兵去了。”我提醒了一句。
“是啊,我是当了兵,不过当的不是八路军,是国民党兵,那时侯,也不懂个啥,只要是打鬼子就成。随着队伍到了黄河边上,干了几场大仗,负了一点皮肉伤,就算立了功,提拔成了连长。”房三爷说的太简单,简单得不太过瘾。
“危险不?”我问。
“那还能不危险,有一回,半夜三更偷袭一个坦克师,匍匐着过垄沟时,正巧赶上一个鬼子撒尿,尿了我一身,我抬手就是一枪,把他送上了西天,这下子,可惹了祸了。”
“咋的啦?”
“暴露目标了呗。”
“挨整了吧?”
“可不,团长说,要么你把鬼子的火力给端了,要么就让我把你给崩了。”
“那么说,您一个人把火力点端了?”
“那是,军中无戏言,谁违反军令谁挨枪子,不去能行。我驮着炸药包,连滚带爬,也算我命大,那么密集的炮火,愣是没伤了我。”房三爷嘿嘿笑了说,“末了,还是让我把火力点炸掉了。爆炸声响起来能把人震个跟头,后来,我的耳朵聋了半年,总是嗡嗡叫唤。”
“您那会儿多大了?”
“不到二十岁。”
“难道不害怕吗?”
“怕有屁用,硬着头皮上呗。两年下来,我原来那个连的兄弟,只活了仨人,其余全他娘的毁了。”
“您是怎么当上团长的?”
“嗨,就那么一回事。”房三爷摸出来烟荷包,我赶紧递给他一支烟。
“详细地说说吧。”
“反扫荡时,团长中了飞机投下来的炸弹,我背着他突出了重围,团长非有我扔下他不可,我不肯,他没辙,只好说,‘你非得背,那好,就直接把我背到师部去。’到了师部,他跟师长说,‘就让这小子来替我吧,这小子仗义。’说完,就死了。”
“当团长时您多大?”
“虚岁二十一。”
“这么年轻,就当上团长了?”
房三爷一摆手说:“别提了,才当团长没几天,小鬼子就投降了,抗战也结束了。”
“您为什么非得解甲归田呢?”
“当兵就是为了打鬼子,鬼子投降了,不回家干啥?再说了……这些年,离开家,也不知家里老老少少咋样了,惦记呀。”
秀大妈插了一句:“怕是最惦记的还是没过门的媳妇吧?”
“我是没跟你们说这一段,我那没过门的媳妇早死了。”房三爷抖了抖手。
“咋死的?”秀大妈问道。
()好看的txt电子书
“你们都以为是病死的,其实不是,是我跑走了投军的那天,她上吊自杀了。”房三爷苦笑了一下,“我还傻乎乎地盼着回家团圆呢,谁想会是这样的结局。”
“那么后来呢?”我问道。
“以后还能怎么着?一个人过呗,不光给爹娘养老送终,还得管丈人、丈母娘。”我发现,房三爷的眉毛特别的粗。深陷在马鬃般粗眉毛下面的则是一双闪着刚毅光泽的眼睛。
“你不知道,三爷这辈子可是遭老罪了。”秀大妈说。
这时候,彭哥他们唱卡拉OK唱罢了,都出来喝茶,润润嗓子。
房三爷讲的故事也让他们打断了。
“柯本,你没听到我们花枝唱歌,那是一种遗憾,她模仿孙燕姿模仿得太像了,我敢说,稍微包装一下,她就能在娱乐圈里红起来,而且红得发紫。”铃子的脸因为兴奋而膨胀起来,不住地抚摸着花枝的脑袋。
“我们班同学比我唱得还好呢。”花枝腼腆地说。
我拍了拍花枝的肩膀,为没能听到她的演唱表示遗憾。铁木儿啜着热茶,问我:“你不去给我们一起唱歌,在这里卖什么呆呀?”
“我在听房三爷讲故事,讲他亲身经历的故事。”我告诉她。他嗔怪我为什么没叫上她,她也很想听,“还没讲完,就让你们给搅了,只好改天再说了,到时候,我们一起去找老人家。”我安慰了她几句。她显然对我的回答比较满意,点点头,给了我一个很有穿透力的眼神。
大家喝下最后一杯茶,从衣架上取下各自的外套和帽子,意味着要散伙了。花枝今晚就住在彭哥家,明天轮到苏怀那,轮到我那得三天以后了,到时候秀大妈陪着她,用不着我太操心。我把钥匙给了铁木儿,让她先去我家,我得开车送房三爷和秀大妈他们,虽然只有几步路,可是天凉,我怕他们感冒了。电视上说,现在正流传感冒。感冒甚至比刀郎还流行。
一出门。寒冷的空气一下子灌进了喉咙里,像掉进了冰窟里一样,树枝的梢头上都结满了白霜。
我回来时,铁木儿已经煮好了咖啡,咖啡是特浓特浓的那种,点起了蜡烛,托着腮帮子在等,这样一来,她给这个夜晚赋予了缠绵悱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