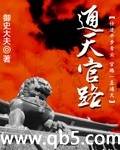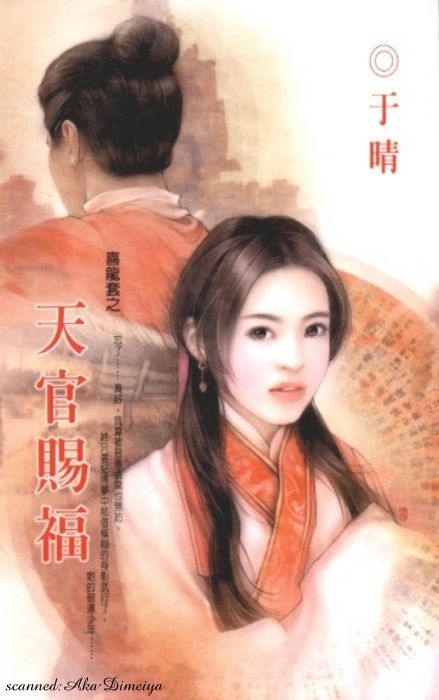天官-第1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道痴生而丧母,十一岁才见到生父,要是张真人说他父母缘厚才稀奇。
现下听了张真人的话,老和尚道:“真人勿怪老和尚啰嗦,除了三岁时那死劫外,不知道痴是否还有其他死劫需避?”
张真人没有再掐算,而是直言道:“从八字看,道痴小友平生有三生劫、三死劫,如今已破了一死劫,还需有五劫可过。生劫向来变化无踪,不可捉『摸』,幸而难以伤及『性』命,顺其自然便好。死劫则要小心七九之年,需避阴地,防小人。”
说到这里,见老和尚面『露』忧『色』,他又劝道:“道痴小友生气正旺,短夭之相渐散,多半是无碍,大师切莫过于挂怀。”
老和尚叹了一口气道:“这孩子是老僧俗世血脉后人,老僧关心则『乱』,着相了……”
张真人沉思片刻,道:“道痴小友的八字之厄,并非无法化解。天地生阴阳,互有补足,若是能以纯阴女子为婚配,即便不能全然为道痴小友免灾,亦能带来几分福祉……”
*
吼吼,求推荐票,求收藏!收藏就是书页放入书架那里,不习惯收藏的朋友请帮忙收藏下吧,这个关系到榜单数值。冲榜艰难,恳求诸君援手。
ps:《天官》有群了,感谢血皇兄,群号:21011140。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进群。;
第第十五章章 论反王,传大考
听了张道人的话,老和尚并未有多少欢喜之『色』。
因世人多重八字,亦听过纯阳纯阴八字的不好。家中但凡有孩子犯了这纯阳纯阴八字的,多会请道士改八字。除了至亲之外,鲜少能有人知晓内情。
不过,张真人既能将这个当成一个化厄的法子说出来,想来也是没有其他化解之道。
天道推演,哪里是那么容易的。
老和尚因同张真人的曾祖父有旧,早年曾帮过张道人父亲小忙,与天师道渊源颇深,才厚颜请张真人推演这一回。
要是再啰嗦下去,反而是不知趣。
老和尚谢过张真人,两人的话题从道痴身上岔开,说起张真人西行青城山之事。
等到中午用了素斋后,张真人便携弟子随从下山去了。道痴则是被老和尚叫到禅室,说了“三生劫、三死劫”。
“七九之年”,不用说就是逢七逢九之年。“阴地”,这个范围就笼统了些,草木为阴,水位阴,墓地为阴。“小人”的定义更是不好捉『摸』。
不知为何,听到张真人留下的这几句话,道痴心里想起“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这几句话。否则的话,真要想着张真人这几句话,自己也要将自己吓死了。
至于以纯阴女子化厄之说,道痴很是不以为然。难道找不到这样的女子,自己就要做和尚?女子本身就是阴,要是真说起阴阳调和方能化厄,那自己就要去做『色』狼?
只是他心里腹诽虽腹诽,却不能不接受老和尚这番关怀:“大师父,我都记下了……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没有这样磨难,说不定我就要碌碌无为。这样想来,即便有劫难,又有何惧?”
老和尚闻言,笑着颔首,道:“痴儿心『性』豁达,今日终成人矣。”
对于十一岁的少年,这可谓是盛赞;可道痴低下头,眼里却有几分恍然。
少年人,哪个不是神采飞扬,他也曾张狂过,只是……
想到这里,道痴心里一痛,眼泪几乎要汹涌而出……
老和尚招待一上午外客,精神有些不足,道痴便没有再问功课上的事情,而是与老和尚说起家常。
包括自己进王宅后发生的事情,还有对王容娘与王三郎姐弟两个的观感。
老和尚看似不在意,可道痴还是发现,当自己称赞王三郎时,老和尚的嘴角还是挑了挑。
道痴见状,不由心下一动,道:“听说三郎有过目成诵之才,观其行事亦带古君子风。不晓得其他王家子弟如何,只是凭宗房七郎能主动相交,想来也是看好三郎。”
老和尚望向道痴,似是看透他的小心思,含笑着:“痴儿并不是热心肠之人,看来是王三郎的赤子之心打动痴儿了!”
道痴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
有些感觉是说不出来的,他并非被所谓“手足之情”感动,只是瞧着王三郎品『性』纯良,有些担心而已。
现下小时还罢,这样纯良品『性』,只会得人称赞与喜欢;长大以后,还是如此,就要撞得头破血流,不知被人坑成什么样。
王三郎越是出『色』,道痴这个做兄弟的身上的担子越轻。想要与家庭的牵系越轻,就要有人能真正支起撑门户。
老和尚沉默了一会儿,终是摇了摇头,道:“老和尚已经老了……有你一个,已经累了老和尚十载,老和尚哪里还会自讨苦吃……你若不放心,随意指点一二便是……”
这是无意相见了。
道痴不过是随口一句,既老和尚没这个意思,便也撂下此事不提,反而开口提及宁藩之事。
“我父亲借‘养亲’还乡,张真人携弟子西行,这其中会不会是因宁藩不稳?”老和尚是他在这世上最近亲的人之一,他便没有遮遮掩掩,直言道。
老和尚面上依旧镇定,可捻着佛珠的手却颤了一下,道:“此话怎讲?”
实际上,此时宁王确实早有反迹,例如暗杀钦差与『逼』迫地方臣子之类。道痴哪里晓得这些,他之所以笃定宁王必反,不过是因为晓得历史上有这么一段。
老和尚既相问,道痴只能做沉思状,将想好的说辞说了:“宁藩与朝廷不睦,天下皆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改变这局面,无非两种法子,一种是朝廷寻故除藩,一种是宁藩奋起反击。今上『性』子随了先皇,御下以宽仁为主,难以做出除藩之举。听闻宁藩当代王爷是庶长子袭爵,出身卑贱,不说旁人,宁藩内部诸王、将军,袭爵初始,想来未能全部臣服。十数年间,整合宁藩之势,宁王在封地已经势成。”
朝廷将宗室王爷拘在封地上,像养猪似的养着,哪里会允许他们做大?
宁王既然在地方势力大,朝廷定要想法子削减,宁王舍不得放弃手中权力的话,就只有造反一条。
至于王青洪在前途正好的时候致仕,而张真人率众弟子西行,则是佐证。
老和尚望向道重的目光,已经不单单是欣慰,还有震惊。
一个十一岁的孩子,能从蛛丝马迹中,就能分析出天下大势,如此聪慧异与常人。
“南昌府是行省衙门所在,驻军数目不菲。若是所料不差,怕是领兵之人早被宁王策反。宁王若是敢动,反军数量绝对不对少。大明承平许久,地方将士那里能承受真正战火,说不得叛『乱』会成席卷之势。”说到这里,道痴不无担心:“若是宁王有心入住蜀中割据天下,那湖广亦不能幸免。”
他担心这点,也是经过深思熟虑。
依照他看,造反是需要“天时地利人和”。
固然朱棣当年以藩王身份造反,抢了侄儿建文帝的江山,也不代表有人可以跟着效仿。
建文帝登上皇位后,先是重用儒生,施行改革,废除太祖旧例,御下宽仁,出发点是好的,可是成效却不尽人意。
没有人会感激建文帝御下宽仁,反而会觉得他行事有悖祖宗家法。
建文帝减免江南重税,后果是国库空糜。
他下令限制僧道私田,分了他们多占的土地,损害了他们的既得利益。
天下承平没多久,在藩王封土边疆,手握重兵时,建文帝开始削藩。
明明是名正言顺地继承皇位,却闹得“天怒人怨”,而后燕王造反,多少有些顺势而为的意思。
现下天下承平已久,正德皇帝又不是昏君暴君,没有什么天怒人怨之举,宁王也不是边藩,手握数十万大军,想要推翻朝廷,可谓是痴人说梦。
“天和”既占不上,剩下的只能靠“地利”。
毕竟蒙古在关外虎视眈眈,朝廷有能力平『乱』,却未必能受得了持久战。
偏生南昌府无险可守,要是想要跳出生天,蜀中就是最好的选择。
老和尚闻言,思量片刻,摇了摇头道:“不会取道蜀中,蜀藩开府百五十年,经营蜀中以久,且又是出了名的亲善朝廷。宁王若是想要去蜀中,不等朝廷出兵,蜀王振臂一会,说不得就与之展开对峙之势。当是东进南直隶,欲取南京。名不正则言不顺,只有占了南京,宁王才能抬出宁献王与成祖皇帝旧约,与朝廷划江而治。”
道痴闻言,这才放下心。
虽说兵祸起,定会殃及地方百姓,可他又不是救世主。
王道洪与张真人的退避,无一不说明宁王反迹已『露』,朝廷却无动静。这只能说明,宁王势大,还有就是朝中有人阻塞视听。
道痴只是千里之外的小童,哪里轮得着他『操』心此事?
辞过老和尚,又吩咐虎头好生看寺外,道痴从山上下来。
王家的马车,早已在山下候着……
*
京中王宅,王三郎回来,直接去了书房寻王青洪。
“宗学七日后要进行大考……”王青洪闻言,不由皱眉。
他原打算明日带道痴去拜会族长与宗学先生,后日开始便让道痴跟着三郎去宗学读书。
在他看来,四郎已经耽搁数年,能早些就学当然是好的。
另外就是让他早出晚归,避开王崔氏与王杨氏。
当年的事情,不管是这两位谁做主,谁推波助澜,都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已经愧对道痴数年。
王青洪不愿意让母亲与妻子再有什么不当之举,那样的话不仅冷了道痴的心,他也没法面对族中长辈。
可突然出来个宗学大考,要是道痴这个时候入学,成绩不堪,岂不是丢了十二房的脸……
*
甩汗,这一更,还是昨天的。晕倒,前天欠下一更后,想要补足,可每天码完两更后,脑子就木了。从奢入俭易,从俭入奢难。有点这个意思。不过握拳,坚持住,脑子会越用越活,人也会越来越勤快的。吼吼。
第十六章 访族亲,珉与瑾
王三郎虽才进宗学小半月,可是也瞧着宗学里竞争不少。同窗们,不是比出身,就是比课业,年纪不大,可也都顶着势利眼。
偏生自己的弟弟不管是出身,还是课业,都难以出彩,难免受人挑剔。
他倒不会想着庶弟会不会给自家丢脸,而是想着是弟弟在家中,同自己一样三岁开蒙,未必就不如自己。说到底,还是长辈耽误了弟弟。
他原盼着早日带弟弟去学堂,可没想到赶上大考,心下便有些踌躇,不过是担心成绩不好损了弟弟的自尊心。
王青洪的心里有些奇怪,他就是从宗学出来的,当然晓得宗学的规矩,是一季一考,现下不是大考的时候。
怎地突然要在这个时候大考,到底是为何缘故?
他一时想不出是什么,想着明日要带四郎去拜会族长与执掌宗学的亲长,便将此事先撂下,反而问起三郎课业。
王三郎道:“先生说孩儿时文尚可,并且吩咐孩儿多与六郎共勉。”说到这里,有些讪讪道:“六郎似乎并不喜孩儿,孩儿也不好过于强求。”
王六郎是王珍之弟,王琪堂兄。在王三郎回乡之前,王六郎是王家小一辈子弟最出挑的。只是十二房回乡后,王三郎入了宗学,即便不是爱出风头的,可他课业出彩,先生喜欢,赞了好几次,就引得王六郎恼恨。
王青洪本身自己少年才子出身,当初也是在宗族兄弟的嫉妒下过来,自是晓得儿子困然,道:“不必理会,四书五经与时文,该学的你都学了,让你入宗学,不过是多认识几个投契的族兄弟。等到明年下场,你就要去州学,与他们有什么好计较的?”
王三郎点点头,显然父子二人都没有将明年的童子试放在心上。
等到道痴回来,王青洪并未没有刻意问西山之事,王三郎却专程道耦院,正经八百地拉着道痴到书房,考校他的功课。
可以说,除了大字还过眼外,其他的在王三郎眼中都不过关。
他望向道痴的目光,添了几分担忧,道:“四郎,这几日我来给你讲四书如何?”
因宗学大考之事,他专程告诉父亲,本是想要让弟弟延后入学。可等见了道痴,又觉得自己思量的不对。
道痴既已经回家,这个年岁就当进学堂读书,自己真要延迟入学的话,落在旁人眼中则太刻意。按照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