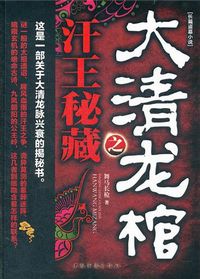大清颠覆者 公子魔-第4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一只明黄的荷包在眀赫赫、亮闪闪的珍宝中格外突兀。若说是有名的湘绣、苏绣也就罢了,偏偏针脚扭曲、断线横生,白乎乎的一团,也看不出所绣何物。众人离了席面,凑成一团,皆围着它转悠半天,心中暗叹:这可是溶儿亲手所绣啊,万金不敌,价值连城,无价之宝啊……众人将烫手山芋抛给我,“溶儿,你说给谁便给谁。我们皆无异议!”说罢,双双狼眼,恨不能将我盯穿,威胁、胁迫、恐吓招数一一使将,这还叫“无异议”?
我岂不知他们的心思?唯有一块肉,狼者甚众,不好分配呢!便只笑道:“若想要它,也容易的很,只说出我绣的什么图案即可,机会只有一次,各人写在纸团上。”说罢,轻松一扭身,坐回席面。
十三凑在荷包前瞧了半天,心中暗道:“这个古怪东西到底是什么?”肘轻轻一碰身旁的四哥,低声道:“四哥,咱俩好好合计合计,肥水不流外人田不是?”
四爷轻轻颔首,摸着下颌又一番思索。狗?还是猫?
那厢,十四对十爷挤眉弄眼,“十哥,咱俩搭帮结伙,一块儿商量,两个臭皮匠,准顶个诸葛亮!”
十爷奇道:“为何不加上八哥、九哥?四人一起,岂不更容易猜出?”
“笨!”十四一敲他脑门,“再加上他俩,即便猜出了,一人能分几天?算来算去,无非是那几种动物,溶儿胆小,肯定是绣些可爱的,咱们列出来,再一排除,找两个最有把握的,这荷包岂不手到擒来?到时我一月,你一月,轮着戴。”十四闪过算计的光芒,笑嘻嘻的望着十爷。
“十四弟,还是你聪明啊!”十爷感慨着,拉着他往一边合计去了。
众人千姿百态,各显神通,我和牡丹抿着小酒儿,嘻嘻哈哈。“你这不诚心为难他们么!若没有‘那两句’提示,谁能猜得出?”牡丹端起酒盅,喂到我嘴里,笑谑道。
“管他们呢!”我仰口含着,任酒香在唇舌中弥漫,美滋滋的往椅背上一仰、一躺,正对上一双黑漆漆、眀亮亮、闪着狡诈的狐狸眼。
他俯下身,微微的麝香气息拢在我面上,灵活的撬开贝齿,在我嘴里吮吸甘甜的酒液。上颌下齿被他吮了四五遍,小小樱舌也酥麻麻的痛,他这才满意的放开我,自顾自的坐下,将我抱入怀中,大手抚上我的腰来回摩挲。
“我又不是酒盅!”我在他怀里微微挣扎,若是被四爷瞧见了,又是一场泼天大醋!
()
“唔~~~”他闷哼一声,脸上露出“痛苦难忍”的神色,不知是真是假,可手仍是紧紧箍着我,将我埋在他胸口处,无限眷恋的深叹一声。
我安稳的蜷缩在九阿哥怀里,想着他方才的血染前襟,这会子我一折腾,别是伤口又裂开了吧?即便是他使的苦肉计,我也认了,“给我瞧瞧,有没有裂开?你这人也真是,什么都闷在心底,让人费劲心思的猜……”
他轻笑:“若你肯费心思猜,我伤上十次八次,又有何妨?即便是我死了……”我捂上他的嘴,轻啐道:“什么死啊活的,大年下,偏你这般口舌无忌……”
他伸出温热的舌,轻舔着我手心,含含糊糊一声接一声的低叹:“溶儿……你若肯放一分心思在我身上,哪怕是登时去死,我也……”
我撤开手,横他一眼,“你若死了,我怎么放心思?下次再敢乱说,别怪我手不容情!”说罢,在他腰侧轻轻一拧,柔媚俊美的九爷顿时龇牙咧嘴,装作痛不敢当的拙样。
三团大战
他轻轻拥着我,看不远处众阿哥们为了一只荷包争执不休,辩来辩去,揪头揪发,冥思苦想,他只状似无意的问道,“溶儿,你绣此荷包时,心里想的是什么?”
知道他来意所为,只是笑他非得先使个苦肉计让我怜惜,也罢,本就怜他伤重难愈,此刻也不过顺手推舟,挑眉一笑,别有深意:“衣不如新,人不如故。你不知道么?我最爱穿新衣衫……”
他露出不敢置信的惊讶,不料我竟直言不讳,想必他还有许多招数未使,只狂喜着问我:“真的?真的?”
我笑嗤一声,“骗你作甚?又没什么好玩儿的……”
是呵,胤禟,你还不知道吧?我在心底,留了一个小小的角落,专门候你住进。好吃好喝伺候着,挡风遮雨的关心着,你且安心住进去吧……看他为我着急狂喜、心情大起大落,我掩住唇角笑意,赖进他怀里。想要居住权,可得付出些代价呢……
最终,众人心中皆有了答案。坐回时,不成想见我与胤禟暧昧姿势,没人敢使脸色给我,只是各自朝他哼了又哼。四爷将我抢过,复又箍在怀中。胤禟不以为意,挑挑眉,着小厮拿了纸笔,潇潇洒洒写了几个字,投在一盒纸团中。
牡丹一一展开,为我念着,果然,除了胤禟猜中白兔,无一人中的。白狗,白鼠,白猫,白狼……更有甚者,写了白象二字。我将今日的胜者之名报出,果然听见阵阵咬牙切齿,一片嘘声。我且不管,仔细的将荷包系在胤禟腰间,他欺在我耳边,嘻笑道:“烦劳娘子……”
我白他一眼,还不是靠我放水?十三早轰一声站起,大叫:“九哥作弊!”
胤禟挑挑眉,“十三弟哪知眼睛瞧见我作弊?”十三指指他,又指指我,悻悻然道:“若不是溶儿事先告知你,你能猜对?”
“呵呵……十三弟啊……”说着,胤禟解下荷包,递给十三,“你看看里面的衬里。”
十三狐疑的接过,往外一番,几行秀丽的小字,飘逸的映在他眸中:“雌兔脚迷离……安能辨我是雌雄……”
胤祥满脸黑线,我慢悠悠的开口,“我只是绣了两只兔屁股罢了……”旁边十爷暗自嘀咕,“怪不得没瞧见眼睛……”十三无言,闷闷坐下,时间紧迫,他只顾着研究白乎乎的图案,谁料到玄机正在衬里?
胤禟占了天时地利人和,如何不胜出?天时地利——这荷包并众多珍宝,早早的送到他府里,几日时间,够他翻来覆去研究个清楚。人和——他唯恐自己猜得不准,又来找我求证,我只说“衣不如新,人不如故”,前面两句“茕茕白兔,东奔西顾”已是不言而喻。
夺宝大战结束,众人悻悻。余下的东西各自拿回,也不评什么三六九等了。本来嘛,不过是想个由头让我挑选,难不成真将奇珍异宝送给其他女人?
又闹了一会,时辰已近丑时,宫中方向传来响彻天的爆竹声,众人皆知这是皇帝起床盥洗,在养心殿神牌前、天地前,拈香行礼。众人皆一整衣裳,纷纷告辞,各归各府。寅时众阿哥并各府福晋尚要身着朝服、齐聚奉先殿祭天祭祖,乃是一刻也耽搁不得的。
各府的马车、暖轿早已预备下,四爷弃了暖轿,抱着直打瞌睡的我上了马车。来时坐轿,费时颇多,他可趁机调戏挑逗,吃尽豆腐,去时乘车,他可早些回府,挤出片刻时间再做些“爱做”的事儿。
九阿哥立于门前,含笑与众人辞别,左手似是无意,时刻抚过腰间明黄荷包。众人皆看不过他这副小人得志的轻狂样,气鼓鼓的去了。我只勾住帘子,笑问胤祥:“怎么?不陪我回府?”
他脚步一顿,他身旁花红柳绿的身影也一顿,他略略迟疑,四爷在背后一揽我,语声无奈:“昨夜、今夜、明夜,他必须在嫡福晋房里过,这是规矩,你又不是不知,偏来逗他!”
“哦?”我佯作不知,只抬眸问他,清脆入“有心人”耳中,“这么说……你也要在姐姐房里过了?”
本方阵营亦有几名竖起耳朵,微颤的绢帕在手里攥来攥去。四爷宠溺一笑,意有所指:“你那拉氏姐姐身子不舒服,怕过了病气给我,撵我去你那儿呢!”帘外右侧,原本“健壮”的那拉氏,配合的作出“摇摇欲坠”的虚弱,勉强一笑:“可不是?大年下的,过了病气可不是玩儿的……烦劳……妹妹了……”
“嗯,我明白了,姐姐请放心。只是……我有一舞,乃是专为闺房之乐而跳……看来,今儿偏了四郎。”猛猛一叹,勾起媚惑樱唇,在四爷颊上一香。
胤祥跺跺脚,又气又恼,高声一喝:“小桂子!回府将爷的朝服取来,送到四阿哥府!”说罢,一屁股坐上来,猛的一放车帘,把我扑倒,马车启动的杂音掩不过清晰的裂帛声。
我在喘息中绽出肆意低笑,在马车的起伏中攀上高潮,在四爷的唇舌间释放花蜜。我的男人,谁又配跟我抢?
甜头么,只给胤祥尝了一点,待他迫不及待、熟门熟路的抱我入簪梅苑后,我收敛淫媚,肃声将太子之事禀明他二人。唉,瞧我多好,生怕太子于寅时祭天之时发难,四爷、胤祥等毫无准备,我索性作了那狐媚子恶人,将胤祥“劫持”入府,告知一切。原本么,我占了各福晋们的男人大半年,此时回给她们点红利也“不算什么”,也不会“太计较”胤祥在谁房里过夜,可太子的心思,谁也猜不透,他说可等片月,谁又敢将此语奉为圭臬?还是早作准备为好。奸笑一声,留人、告警一举两得。
四爷、胤祥面色古怪,像是咬牙切齿,又像是欢喜无限,嗯……男人在这种时刻被打断,估计都没什么好声气吧?他们感激于我的信任坦诚关心爱护,气急于我偏挑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之时煞风景,两人嘀咕半天,终究还是先屈从身体本能,来个三团大战。
气咻咻、声媚媚、吼声声、叫淫淫,门外下人们捧着朝服、朝冠躬身而待,门内热火朝天、攻城略地,秦顺儿的咳嗽声第十遍响起,四爷貌似天聋,胤祥貌似地哑,俩人不知在跟谁呕气,一声不吭,默默耕田。
最后,时间真是来不及了。我一脚一个,踹下床去,“想害老娘没丈夫?不知道你们的皇帝老爹脾气大的很么?若是一气之下将你们扣在宫中,老娘这块田谁来耕?”
俩受虐狂,就爱听这些粗俗不堪的,尤其是越到紧要关头,越有味道。四爷只叫牡丹进来伺候穿衣,然后趁着穿衣的当空让我坐于他腰上动了半晌,非泄的一塌糊涂不可。牡丹见怪不怪,胤祥有样学样,最终,两人“精神爽利”的打马而去。
牡丹又伺候我沐浴更衣,按摩复苏,这才将辛劳半天的我拽到床上,然后并肩躺下,哄我入睡。虽身上疲惫不堪,偏脑子里灵光的很,这才想起心中隐约之事,华者,烨之去火也。那代表,他永远不会对我发火吗?
嘴里嘟哝着:“牡丹,等我睡醒了,咱们去看看府里的冰床。”真是好奇呢……我虽会溜冰,可从未试过玩冰床,想必是个极有趣的游戏。牡丹笑骂一声:“知道了!就没见你这样儿的,睡个觉也记挂着。”手下轻柔无比,如哄着婴儿一般。
冰嬉大典
这一睡,直至巳时一刻。四爷、胤祥、福晋们皆滞留乾清宫,吃不甚可口的“赐宴”,众妾们皆小心翼翼的躲着我,想找人斗嘴也没个搭理的,怏怏逛了半晌,方想起还有紧要大事,忙着人唤来秦顺儿,带我至库房一游。
要说这秦顺儿这总管实在不是盖的,当我这八百年难出簪梅苑一次的主,破天荒的要去库房时,他已知道我是为那托冰床而去,便带着我七拐八绕,在一座院落停下,铁锁一开,没有意料中的尘土满面,屋里温暖干燥,十几台大冰床簇新簇新,排列整齐,静立当中,周围还散着无数小冰凳、冰锥,秦顺儿微笑着打了个千,“溶主子,入冬前爷便吩咐过,故奴才早采买了几台备着,您若看中哪样,奴才着人替您收起来。”
我踱着步,背着手,检阅华丽的冰床部队,座位宽敞,可容三四个人,华美精致,雕着花鸟鱼虫、岁寒三友之类的,果然是福晋气度。唉,实在是因这冰床乃是女人家坐的,故而装扮得精致漂亮,可是——不合我的口味!
我想象中的冰床,该是像秦始皇乘坐的战车,人可立可坐,站立时挥斥方遒、英挺无比,坐时指点江山、姿势优美。而不是只能坐或躺,还拿粉红、紫红、鹅黄的纱幔拢起来,似船非船,似艇非艇,不伦不类。我心里好一通臭骂,这些女人,还号称什么满族儿女,一个个弱化的像是江南碧玉,这不敢碰、那不敢使,好端端的冰床,硬弄成密不透风的车轿样,还备有火盆、铁箸、暖手炉,嫌冷别玩啊……登时豪情万丈,恨不能化作巾帼红颜,坐上战车似的冰床,征战沙场。哎……实在是在四爷府里憋屈坏了,刚入冬时四爷便应承过我,陪我游冰湖、踏冰川、玩冰床,谁知又出了某人差点当街被掳的危险情况,从此被禁足府中,甚少能到街市上游逛,更遑论赏玩天然景致。我对这次的冰嬉大典可是存了莫大的期望呢!
我的眉渐渐耷拉下来,秦顺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