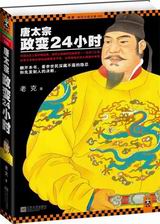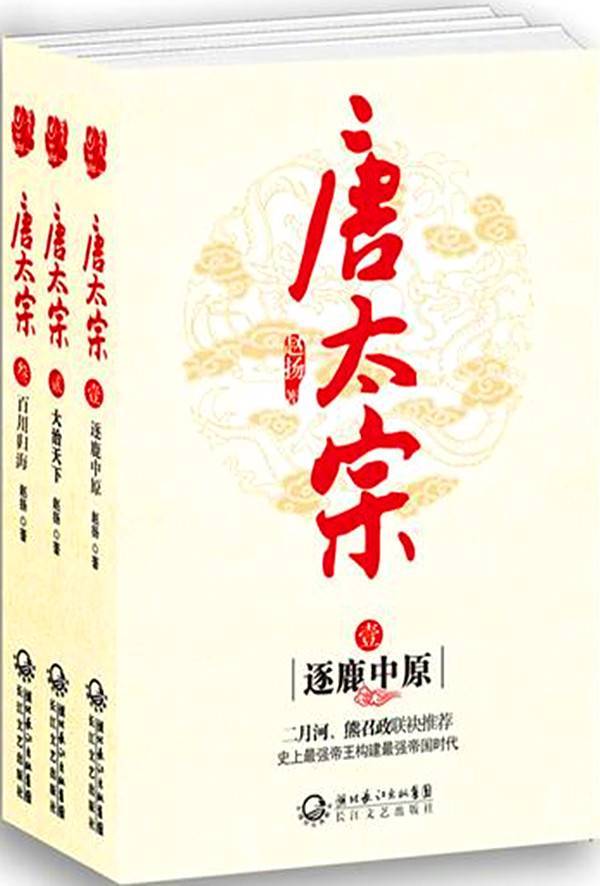唐太宗政变24小时-第7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文帝杨坚要来得少。所不同的是,杨坚是采取压制相权甚至完全废黜相权(相位阙置)的方式来杜绝宰相染指最高权力,而李世民则完全不同,他是采取分化相权的方式来避免相权对皇权的潜在威胁。
李世民时期的三省六部制,是运行机制相对健全分工合作相对明晰的一种政治体制。这位旷古绝今的封建统治者采取降低宰相资格门槛的模式来分化相权。前面我们已经叙述过,按照定制,国家拥有六名名副其实的宰相,而李世民又通过“参知政事”等等诸如此类的名义使得宰相的群体更加广泛,在贞观年间的朝堂上,十几位宰相共议国家大政的局面并不罕见。在众多宰相当中,地位最高的左右仆射也仅仅是从二品的官秩,至于中书令和侍中,衔仅正三品,更不必说那些非正式的宰相了。这种群相制的好处在于,决策权由多人掌控,而最终的拟旨、封驳、执行大权分属三省,他们相互制约相互牵扯,不仅仅在决策流程上更加科学更不容易出纰漏,也同时杜绝了宰相独秉朝政成为权臣威胁君权的可能。
虽然在防止相权威胁君权的问题上李世民与杨坚的思路大体一致,但在治理天下的理念上,两个人却是大相径庭。杨坚从骨子里不信任自己的大臣,他唯一相信的只有自己,对臣属的猜忌丝毫不亚于后世一些著名的独裁君主。而李世民却认为,皇帝本人的能力再强,对于治理偌大一个国家而言也是远远不够的。他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绝不是一个无所不能的超人,天下可以为李姓一家所有,却绝不可为李姓一家所治。实际上,在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几十位君主将近八百年的统治期内,这种认识在皇权内部是普遍存在的。统治者们也并非全都是自大狂,绝大多数人还是有自知之明的,因此这期间虽然不断地有政权更迭,不断地有权臣篡位,统治者们却还是要依靠宰相所领导的政府来统治天下。并非是统治者们不想自己一个人来操控大权,就像后世的一些著名独裁君主一样,而是以他们的能力实际上做不到这一点。
也正因为此,门阀世家和士人的力量才会渐渐崛起,并逐渐在两晋时期成为一股可以主宰天下兴亡的政治力量。其实这个道理不难理解,君主需要通过大大小小各级官吏来治理国家,而这些官吏必须具备相应的受教育程度和文化水平,在那个没有学校,读书成本相对高昂的年代,只有这些门阀世家的子弟读得起书,具备比较高的文化素养,在科举制度兴起之前,统治者们实际上是别无选择的。
李世民身处的时代与魏徵相同,他们同样经历了隋朝由强盛迅速转向衰落乃至王国的动荡时期,缺乏相权制衡的君权给天下带来的危害姑且不论,隋炀帝横死扬州的凄惨结局无疑更令李唐的统治者们悚然心惊。李世民本人就出身关陇世阀之家,世族士人的政治理念也曾经是他自己家族的政治理念,而他又清楚地看到了与这种政治理念背道而驰的可怕后果,那么他在登基之后采取皇帝垂拱君臣共治的政治理念就不足为奇了。
也正是在这种政治理念的作用下,魏徵的那种近乎无礼的平等观念才能为李世民所认同和接受。这并不是说唐太宗是一个具备古代民主思想和平等观念的皇帝,只不过在李世民看来,以魏徵为代表的士人阶层身上这种令人不快的特征对于李唐王朝的统治是有利的。当然,如果这种平等意识有一天真正威胁到了唐室的统治地位,李世民也一样会反过手来用强硬手段予以镇压。然而幸运的是,在李世民作为皇帝统治中国的二十三年当中,这种危机似乎从未出现过。
其实说起来,唐太宗这个皇帝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被后世人敬仰尊崇的一代明君,并不是李世民本人的能力比之其他的封建帝王要强出多少倍(起码在勤政这一点上,他就明显比不上隋文帝杨坚),而是因为他比别人多了那么几分作为君主的自知之明。
在贞观年初,初秉国政的李世民雄心勃勃,既要使国家富强,又要消除严重的外来威胁。而在此之前一直作为军事统帅在外领兵打仗的李世民很难说这时候已经具备了治理国家和处置琐碎的民政事务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新的贞观政府采取什么样的决策机制和政治理念,就变得举足轻重了。
大概因为“隋炀帝情节”的存在,使得年轻的新皇帝变得异常谦虚谨慎,他不仅允许鼓励大臣在朝堂上指出他的错误,还制定了一套以“五花判事”为核心的决策流程,不惜以降低决策效率来保证国家大政方针的谨慎出台。隋文帝分三省六部,虽然名义上也赋予了门下省相应的制约职权,但却从未让这一职权真正变为现实过。李世民却实实在在强化了这一省权,因为他意识到,这是能够避免国家出现“乱政”的最后一道拦截索,一旦这道拦截索失效,国家就失去了安定和发展的保障。
然而这道拦截索毕竟是死的,需要一个能够尽职尽责的人来掌握。
贞观朝名臣辈出,李世民的左膀右臂房玄龄、杜如晦,两朝重臣、《唐律疏议》的执笔人长孙无忌,才兼文武、出将入相的李靖,白身入京布衣拜相的马周,无一不是一时之人杰。然而李世民却都没有用他们来执掌这条拦截索,至于原因,我们不得而知,如果非要列举一个原因的话,我们只能说,大概李世民觉得他们都不合适。
最终掌握这条拦截索的人是魏徵。
如果把贞观政府比作一辆汽车,李世民就是这辆汽车的油门,而魏徵就是那紧急关头能够救命的刹车。
大业年间的隋朝,就是一辆刹车失灵的汽车,将一个庞大的帝国彻底拖入了万丈深渊。
也难怪后世的君王们很难理解唐太宗与魏徵之间的关系,这种古怪的君臣关系在中国历史上极为罕见。皇帝人为地在朝堂之上树立起一个对立面,而且赋予重权,为的就是要这个人时时刻刻警醒刻板地指出自己的过失,且不给自己留半分颜面。无怪乎史家言三代之下最贤不过唐太宗,能够具备这种远见卓识的君主,在中国历史上确实是凤毛麟角的。
读史者往往爱争论李世民是否真正信任魏徵的问题。有人认为终唐太宗一生,对魏徵都尊崇备至信任有加,依据是根据史书记载对于魏徵的谏言李世民几乎无有不纳;有人认为李世民对魏徵的信任从不曾超过秦府心腹出身的房杜长孙,理由是直至魏徵病故李世民都未曾让他染指尚书省的行政系统,他这个“宰相”十几年间一直是在门下省内打转转。
其实二者说的都不无道理,从人情世理而言,李世民对魏徵的信任不应该超过对长孙无忌和房玄龄杜如晦的信任,但是李世民如果真的猜忌魏徵,又怎么会将制约自己的大权赋予这个东宫旧人?
在笔者看来,李世民是否信任魏徵这个命题根本就是一个伪命题,没有任何探讨的价值。
两者争论的信任与否,实际上本无所谓什么意义。对于唐太宗而言,魏徵存在的意义即不是“亲朋故旧”也不是“能臣干吏”。这两个人除了在“求天下大治万民乐道”这一点上是共同的以外,在其他方面差异都相当大。
这一点,历事四主的魏徵不可能不明白,在隋末唐初十八路反王间辗转杀戮通过血腥的军事政变登上皇帝宝座的李世民更不可能不明白。
所以唐太宗与魏徵之间的关系,并非寻常的“君臣从属关系”,也不是略显平等的“亦师亦友”关系。这两个人之间,实际上是一种默契的“同志关系”。
李世民知道魏徵想要什么,魏徵也了解李世民为什么要用自己。
这是一种超越了尊卑礼仪的关系,是两个杰出人物之间惺惺相惜的战友情谊。如果说在大业武德年间的李世民与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人之间的关系是战场上的战友关系,那么贞观年间李世民与魏徵之间的关系就是一种治国上的战友关系。两个志同道合的人共同为了一个目标以不同的方式进行努力,不是“同志关系”又是什么?如果说李世民是大唐这支军队的总司令,那么魏徵,就是这支军队的总政委。
后世对魏徵的评价很多,而且绝大多数都是褒扬赞美之词,很少有人去揭他“三姓家奴”的短,即使是思想相对保守秉性方正志虑忠纯的司马光,在写《资治通鉴》的时候似乎也下意识地忘却了这一点。大概是在古代士大夫眼里,抓住一个贞观名臣的历史问题小辫子大做文章是一种很不厚道的行为吧!
其实魏徵这个“三姓家奴”,和吕布这种人还是有着本质区别的。魏徵所追随的第一位主公就是李密,李密投唐后很快就被不那么厚道的李氏父子设局砍掉了脑袋,写史书的人写到这里只记得那位领兵在外一面向唐室效忠一面为故主李密发丧的李世勣,却往往忽视了那个亲自动笔为李密撰写碑文并且在碑文当中满含悲愤含沙射影地指斥李唐朝廷屈杀忠臣的古板文人,而此人,不巧正是未来的帝国宰相魏徵。
魏徵在后来的李唐皇室储位之争当中选择了太子李建成,将战功赫赫声望勋业如日中天的天策上将军弃如敝履,李建成在李密问题上手上不曾染血大概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参考因素。
在魏徵所追随过的四位主人当中,其中三位都是很不幸的短命鬼,只有李世民与他君臣始终。然而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在史书的记录中实际上看不到魏徵“背主”投靠别人的恶劣形迹,在他投靠别人的时候,他的旧主人往往已经死掉了。
所以如果我们因为“四易其主”问题而否定魏徵是个“忠臣”,论据实际上并不充分。有人说忠臣的定义是方孝孺那种在斧钺之下梗着脖子高叫“成王死,其子尚在”的偏执型学究,对这种说法,起码我不能认同。
那么魏徵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这个人,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知识分子。
他是胸怀天下的乱世豪杰,是腹藏经纬的治世名臣,是明慧若愚的智者,是权重一时的宰相。
他是贞观之治的护法真神。
贞观朝有着众臣议政畅所欲言的开放式政治氛围,也涌现出了如戴胄、张玄素,王珪等等一大批敢于指着皇帝的鼻子尖放胆痛骂的诤臣谏臣。在这个独特的历史现象背后,有着更深层次的时代背景和思想内涵。在那个时代,隋炀帝因为独断专行拒绝臣属的谏言劝告而导致国亡身死的残酷现实无情地揭示了君权独治体制的弊端,这一点最终成为了大唐贞观君臣整体的共识,也最终奠定了二十三年贞观之治的政治基础。
历代名相甚至权相,无一不是手握决策行政大权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凌迫于君权之上令皇帝都有所畏惧有所猜忌的宰相。然而贞观一朝二十几位宰相当中,在历史上留下最显赫声名的却是那个整天在皇帝耳边絮絮叨叨这也不许那也不行的魏老头。如果有人说汉武帝一朝最著名的宰相是汲黯,所有人都会当笑话来听;然而若说贞观朝最著名的宰相是魏徵,恐怕异议者的声音就会低八度——毕竟史书上就是这么记载的。魏徵成为贞观名相群体的表率,是那个时代所独有的一种政治现象,也是两千多年君权专制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健康表征之一。
唐太宗也畏惧魏徵,有那只被活生生憋死在袖筒里的可怜鸟儿的冤魂作证。然而这种畏惧并非是对一种更加强大的权力和势力的畏惧,而是一种对道德的畏惧,对因犯下错误而即将遭受到的批评的畏惧。贞观朝的政治特色之一,便是天下人都知道,皇帝做事也分对错,皇帝做错了事情,也要像小学生一样接受老师严厉的批评和教育。贞观朝的大臣们,对于质疑皇帝所作所为的正确性报以极高的热忱,因为这是公认的对天下有利的大义之举。
如果说魏徵是唐太宗李世民的一面镜子,那么这面镜子当中所映射出的,恰恰是唐太宗自己。在魏徵这面“镜子”里面站立着的,是一个与李世民本人绝对平等的存在。唐太宗将魏徵比喻为一面可以使自己“明得失”的镜子,实际上就是默认了魏徵所代表的那种最原始的平等观念,那种中国古代士大夫身上所独有的人格精神。
贞观十七年正月,司空特进知门下省事太子太师郑国公魏徵病逝,贞观二十三年五月,贞观天子李世民病逝,贞观之治,便这样随着两个即将相伴千秋的历史名人的离去落下了帷幕。
如果有人问究竟什么是贞观,贞者正也,观者鉴也。贞观,就是一双持正不阿的眼睛,默默地注视着后世:她是清明政治的化身,默默地映照出后世帝王将相们的倾轧纷争;她是和谐社会的灯塔,静静地俯瞰着未来社会的凄惨动荡。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在众生面前,统治者们必须谦卑,必须敬畏。他们只有将自己置于始终受到监督受到制约的政治理念和文化氛围之下,才能确保自己的地位,才能换来社会的稳定,才能迎取天下的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