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园-第44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这一手足以主宰中原日后的走向!谢宁心里非常清楚。自己、族叔谢映登、还有追随自己执行此任务的人,将来定会在史册上留下重重的一笔。但能主宰历史的事情,为什么自己做起来心里没有半分喜悦?
目送着心腹离开,谢映登再度跨上了战马。长城上依旧没有喊杀声,突厥狼骑的角声依旧吹得惶急。既然安不下心来在营帐中休息,不如到城墙上找些事情做,借以驱逐内心的忐忑。
尽管李旭和李建成一再强调大伙可以先调整一下,第一仗由河东军与博陵军来打,大部分援军将领却和谢映登一样没心思躲在营帐里边养精蓄锐,。走在半路上,他先后遇到了刘季真、时德睿和韩建紘等人。彼此打了个招呼,并络赶向了第一线。
河东与博陵将领早已爬上了城墙,站在距离黄花豁子最近的一个烽火台上,正热烈地讨论着敌情。见到谢映登等人到来,众将赶紧让出了一排空档,一边寒暄,一边七嘴八舌地说道:“诸位来得正好,快看看骨托鲁在卖什么迷魂药。从一大早到现在了,居然来半根箭都没法放!”
“他那花花肠子里边,还能拉出什么好屎来!”刘季真不顾有女将在场,出口成脏。“待老子仔细看看,那厮的屁股朝哪个方向撅!”
“管他,先赏他几箭再说!”韩建纮也是个急性子,跟在刘季真身后附和。手打凉棚向下一望,二人却又不约而同地闭上的嘴巴。乖乖,但见满山遍野的突厥人,手里提着斧头和锯子,正在砍伐距离长城三百多步左右的大小树木。还有数不清的各族牧人、奴隶,在号角声的指挥下,沿着黄花豁子山谷两侧的斜坡,不停地堆放草袋。才半日多不见,昨天的战场已经完全变了模样。原来的山谷不能再被称为山谷,左右两侧,各有一道狭长的平台被草袋裹着泥土堆积了起来。
“他们要做什么,难道要修鱼梁大道么?”河间郡守王琮看得稀罕,皱着眉头问道。他曾经听说过,昔日大隋官军攻打辽东城,为了尽可能多地投放士卒,修了一条可从城下直通城头的鱼梁大道。但辽东城坐落于平原之上,一条鱼梁大道数日可就。万里长城却位于燕山之颠,突厥奴隶干活的速度虽然快,从山下修条鱼梁大道致城头,恐怕也得修上年余。
“不是修鱼梁道。那战术根本就是异想天开。大隋伐辽东,李密打黎阳,都未曾成功过!”不忍听老郡守继续露怯,上官碧接过对方话头,低声分析。“这一段城墙虽然绵延百里,但适合进攻的点,只有几个曾经被山洪冲开的豁口。眼前的黄花豁子算一个,三里之外的麒麟谷算一个。西边”她用力向远方尘土飞扬处指了指,“葫芦涧那算另一个。如果不能拿下这三个豁口,即便从别处上了城墙,大军依旧需要爬山。人过山头容易,战马和粮草却未必爬得动!”
“上官将军说得对!突厥人大兴土木的,刚好是这三处!”负责招呼众豪杰的博陵军将领时德方走过来,低声肯定上官碧的判断。目光与谢映登的目光相接,他微微点了点头,然后快速将脸转向了其他几位,“我们也认为,突厥人的主攻方向基本放在这三处。但保不准还会在其他地点寻找咱们的疏漏。这些人工搭建起来的土台距离都在强弩射程之外。所以一时半会儿很难判断他们要做什么?”
“那大将军呢?他怎么说?”上官碧冲着时德方微微一笑,然后低声探询。虽然与李旭只有一面之缘,也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她却在第一时间把李旭当成了这里的主心骨儿。
“将军在麒麟谷附近的烽火台上。骨托鲁的大纛也竖在那附近!”时德睿笑着回应,“那边情况与这里一样,大将军正在与人商讨如何应对!”
“嗯!”上官碧轻轻皱眉,凝神远眺。完全没考虑自己一颦一笑之间,吸引了多少目光过来。按照鲜卑人的风俗,那些目光无论带着什么心思,都算不上不敬。少女是一朵带刺的花,在原野中肆意开放,你可以远远地欣赏,但只有她喜欢的人才有资格靠近。
“昨天晚上,不知道她去英雄楼,得到什么结论?!”望着少女的如花笑颜,谢映登的心猛然跳了一下,然后不由自主地想。他记得上官碧等人去拜会了李建成,并且记得当晚上官碧所说的每一个字。如果她心目中的英雄是李建成?想到日后这个女子可能会因为自己而死,他的心不觉有些乱乱的,隐约带着一点点刺痛。
第七卷 逍遥游 第七章 盛世 (四 下)
正懊恼间,长城外的角声又响了起来。凄厉而悠长,就像雪天后从北方吹来的风,让人从鼻尖冷到骨髓深处。谢映登手扶城垛向远处望去,看到大队大队的突厥人潮水般让开一条通道,一大串骷髅,具体的说是一大串身体上挂着各种骷髅做饰物,长得如野猪般矮胖的男人在狼骑的膜拜下走到了刚刚搭建好的平台上。
这些人都赤裸着上身,胸口和肩膀上乱七八糟地画着或纹着各种图案,腰间用皮索系着各式各样的骨头。也许是牛羊的,也许是野兽的,随着人的脚步上下颤抖。每前进一步,骨头的主人便转过身来,向周围的人群嚷嚷几句。而人群瞬间就像进了水的沸油,爆发出一阵又一阵热烈的欢呼。
“啊—嗷嗷—嗷嗷嗷!”为首的赤身男人扯开嗓子,发出一声古怪的长号。霎那间,整个山谷开始沸腾。“啊—嗷嗷—嗷嗷嗷!”刚才还忙碌着的人,无论战士还是奴隶,全部停止了手头的工作,仰头,举臂,跟着骷髅们的节奏长嚎不止。
啊—嗷嗷—嗷嗷嗷!”带头嚎叫的男人年龄已经不小了,但中气却非常地足。一边晃动着手中由一块大骨头和两只铜铃铛组成的乐器吟唱,一边中了邪般前窜后跳。跟着他身边的其余几个手握各色骷髅乐器的男人也跳了起来,一边跳动,一边将油乎乎脏兮兮的长发摇摆不止,每个人身上所挂的骷髅饰物也跟着扬动,发出苍白碰撞声。随着碰撞的节律,他们自动形成了一个圈子,以某种独特的舞步在高台上往来循环。一时间,号角声,鼓声、铜铃声还有骨头与骨头的撞击摩擦声组合在一起,汇成股怪异而恐怖的音乐。听得人头皮发紧,毛孔发涩,浑身上下每一寸肌肤都好像沾上了血,湿淋淋粘得难受。
谢映登知道敌人是在举起某种神秘的仪式,但这种仪式在他眼里看不出任何美感,只令人觉得恐慌。他回头四望,发现身边大多数豪杰的脸色都不太好看,只有刘季真等少数来自塞上马贼,两眼呆呆的望着敌人的表演,目光居然带着几分羡慕。
“他们在祈求上苍保佑自己胜利!”刘季真性子虽然平素行事大大咧咧,却粗中有细。发觉谢映登在审视自己,赶紧回过头来,低声向对方解释。“塞上各部落的习俗都差不多,我小时候,族人在出战前,也由萨满带着向长生天祈福。后来我们的部落被突厥人吞了,老萨满也战死了。长生天,长生天那些日子肯定喝酒喝过了头……。”
说到这儿,他自觉心里凄凉,张开双臂,冲着长城下大声嚷嚷,“啊…………啊—啊———”
“啊………啊啊—啊啊——”刘季真的亲信拔出腰刀,与自家首领一道向突厥人嚎叫示威。长城外的喧闹声太大,几个人的干扰根本无法影响对方的节奏。萨满们毫不介意外来噪杂,继续跳动,白花花的骷髅饰物在阳光下发出一团团诡秘的光芒。围在平台两侧,突厥人、奚人、室韦人,伯克、土屯、战士、奴隶,全部跟着举腿,顿足,呐喊,高歌,如醉如痴。
突然间,所有喧闹声噶然而止?“啊——!”刘季真嘶哑的喊声传了出去,在群山之间孤独地回荡。他用手擦了把脸,停止了无谓的抗议,喘了口气,讪讪向谢映登解释道:“出口恶气。奶奶的,要不是我们匈奴人自己不争气,草原上哪里轮到他们嚣张。贼老天,贼老天要是保佑他们,老天就是糊涂蛋!”
仿佛要与他作对。萨满们大声吩咐了几句。狼骑当中又发出一阵欢呼,几个光着膀子的彪形大汉,将数十头羊,九头白色的小牛,陆续牵了上来。
牛和羊不理解什么是神圣,一边抗争被屠杀的命运,一边发发出凄凉的哀鸣。围观的突厥人则发出哄堂大笑,七手八脚地给萨满们帮忙。很快,羊和牛都被固定了到预先竖好的木桩上。几个少年捧来尖刀,双手举到祭祀们的面前。领队的祭祀大声吟唱了几句,随即抓起把尖刀,快速在自己额头上画了一下。
其余几个祭祀见样学样,举刀自残。血,立刻淌满了他们的脸。好像为了让长城上的守军看到自己的勇敢般,祭祀们转过身来,对着长城呐喊示威。然后用自己的血将刀身涂红,缓步走到九头白色的小牛身侧。
“哞————”受惊的小牛发出绝望的哀嚎。“呜呜…………呜呜呜————呜呜”早就等着这一刻的突厥人立刻吹响了号角。“嗷嗷————嗷嗷————嗷嗷!”祭台旁的将士们又开始大声吟唱,一边唱,一边用兵器割破自己的皮肤。
人血、牛血、羊血,殷红的血光晃得人头晕目眩。下一刻,杀戮成了主旋律,牛、羊全部倒在了祭祀们的刀下。早有手脚利落的战士用铜盆接下了牛血和羊血,一盆盆地摆在了祭坛中央。带队的祭祀们将铜盆举起来,口中念念有词,一边低吟,一边用血染红了整座平台。
风,立刻将血腥气传到了长城上。纵使见惯了生死,谢映登等人依然被熏得隐隐作呕。中原军队在大战前偶尔也会向神明献牲,却从没弄得如此血腥过。偏偏对方以血腥残暴为荣耀,刚刚将祭台泼成红色,紧跟着又在血泊中引吭高歌。
“刘兄,他们唱得是什么?”谢映登憋得难受,喘息着向刘季真询问。
这回,马贼头刘季真没强调他自己的高贵血统,侧着耳朵听了听,然后小声解释道:“这是一首突厥人的战歌,好像已经存在了上百年。第一段强调的是自己的出身,兜舆山下,天狼与人类的孩子。吃狼奶长大,传承着祖先的勇敢……。”
“我们是苍狼的子孙,长生天赐予我们强壮的筋骨。”停顿了一下,刘季真继续翻译,“弯刀是我们的牙齿,
战马是我们的翅膀,
阳光下所有土地都是我们的牧场,
苍狼的子孙
伸出手去拿
将男人的头砍下来
将女人拖进你的帐篷
别理睬他们的哭泣与哀告
这都是长生天赐予我的
我是天生的狩猎者
我是天生的狩猎者
身体里流淌着苍狼的血脉
长生天的宠儿
伸手去拿
将男人的头砍下来
将女人拖进帐篷
用他们的血来见证我的荣耀
这都是长生天赐予的恩典
我是天生的强者
我是天生的强者
无人能阻挡我的脚步
催动战马
踏过高山和原野
在白骨和尸体上竖起我们的战旗
别听弱者的祈求与哭声
烈火焚烧过的地方很快就会长满青草
………。。”
歌声漫长而恢宏,经刘季真翻译后再传到长城上众人的耳朵里,却令人毛骨悚然。那不是简单的祭祀,那是苍狼子孙隐藏于内心深处的宏愿。谢映登发现自己的身体在不知不觉间颤抖了起来,不是因为恐惧,也不是因为寒冷。
他从士卒手中抢过一把战弓,搭箭上弦,试图给狂热祭祀们一点教训。却发现距离太远了,四百步,即便床子弩射过去,也会失去准头。“来人,给我擂鼓,将狼骑的声音压下去!”尽管不是自家军中,他依然不顾身份地大声喝令。正为自家士气担忧的时德方向亲卫们使了个眼色,鼓声立刻从城头上爆豆般响起。
“我们是苍狼的子孙……。”仿佛挑衅一般,突厥人歌声根本不被鼓声所打断。山谷内外,几十万人一同唱着,如醉如痴。
“奶奶的,给我把床校准了!”时德方也有些急了,跺着脚怒喝。守城的将士闻令,立刻将床弩推到垛口处,弩尖微微下压,与远处的祭坛对成一条直线。
早已搭在弦上的弩箭却没有射出去。就在大伙忙碌的时候,突厥人又将几对少年男女推到了祭台上。隔得太远,长城上的守军分不清那些少年男人是中原人还是塞外人,诧异地张大嘴巴,眼睁睁看着意想不到的惨剧在面前发生。
“不是,我们匈奴人可没这个习惯。”刘季真心里发怵,迫不及待地向大伙解释。他一直以匈奴王的后裔自居,自认为血脉高贵。但这一刻,他却非常怕被同伴们当成城下那些家伙的同类。“我们匈奴人没这个习惯,我们……。”
没人听他的解释,所有守卫者的目光都盯着长城下的祭台。在众人的眼里,刘季真清晰地看到了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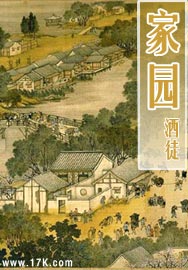



![[网游]家园封面](http://www.cijige2.com/cover/53/53257.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