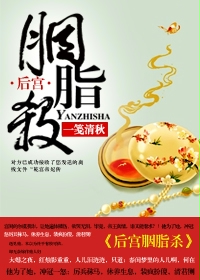胭脂与杀将-第6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你的胃好些了吗?”上颢一边喝着鱼汤,一边问道。
云檀点了点头,“接连喝了好几日粥,什么都不敢吃,今日炖着鱼汤,胃口倒是大开,可惜只能饱饱眼福。”
上颢微微皱了皱眉,他放下碗,隔着桌子握住她的手,“近来我事务繁忙,没有时间照顾你,委屈你一个人留在行馆里了。”
“不委屈,”云檀摇了摇头,她的脸上总是挂着几分笑意,上颢时常被她的笑容感染,毕竟跟爱笑的姑娘在一起,谁的心情都不会糟,“翠吟回来了,我闲来无事可以跟她聊天,对了,前些日子,我还画了一幅画呢。”
云檀说着站起来,轻盈地走到书案边,拿起一卷画,走到他跟前展开。
这是一幅《飞鸟逐蝶图》,画里的景象似乎是遥玦山庄中的一角,又有几分像很多年前西容城外的那处小院落,上颢细细地打量了一番,开口问道,“这是什么地方?”
“我也不知道,”云檀嫣然笑,“这是我胡思乱想的地方,大概是世外桃源吧。”
“画得很好,以后拿回去装裱齐正,可以挂在屋子里赏玩。”上颢说道,他并非文人,对于画作没有高超的鉴赏能力,在他看来,这幅画生动有趣,色彩鲜妍,便是佳作了。
“你取笑我呢,我这等陋质,哪里敢把画挂到墙上显摆?也就欺负欺负你这样的外行人!”女子笑得眉弯目秀,她学过不少才艺,但都算不得高妙,或许在外行人眼中如珠似玉,可对精于此道的人而言便只能算中庸了。
云檀将画卷好,重新放回陶瓷画桶内,然后坐回桌边陪上颢喝汤,待到用餐完毕,她收拾起碗筷,唤来仆妇拿去灶房洗了。
夜阑人静,窗外飘进来一阵野蔷薇的花香,云檀循着香气扑到窗边深深吸了一口气,院子里种着两棵高大的紫葳树,树冠上开满了淡紫色的花朵,风一吹便飘下一股类似茉莉花的清香。
月朗风清,天水城的夜晚比白天寒凉许多,上颢走到她身后,将一条羊毛毡子当作披肩裹在她身上,云檀转过身来,对他欣然一笑。
她细细端详着他的眉眼,忽然关切地问道,“你今天看上去不太高兴,出了什么事吗?”
上颢略微意外,他以为自己掩饰得很好,想来这张缺乏表情的脸,就算不掩饰也没什么破绽,有时他很好奇,她是如何分辨他心情好坏的。
“今日的确出了一桩麻烦事,我原本不打算告诉你,但多少与你有些干系。”上颢开口道,夜里风冷,他关上窗,让她坐回房里。
“什么事?”云檀将上颢拉到软榻边坐下,自己则像个小孩似的坐在他膝头,伸手抱住他的脖子。
上颢将世子苏虔意外死亡和镇洋王参他一本的事简单地叙述了一番,“事以至此,我不得不告诉镇洋王真相,如此一来,你的姐姐恐怕有麻烦了,镇洋王会如何处置她,我一无所知。”
云檀听罢,微微苦笑,“其实这事你不必告诉我的。”
“但我不想让你误会,等你知道了姐姐的遭遇后,我再来解释,你恐怕会记恨我的。”上颢伸手抚弄着她的乌发,像在跟一个乖巧的孩子讲道理,“你姐姐既然有胆量挑唆小世子弑父,那就应该料想到后果,我原本并不想声张此事,但如今境况危急,我必须实话实说。”
“我明白,但你也知道,我一向感情用事,姐姐若是出事,我难免要伤心,却也不会记恨你。”话虽如此,云檀还是露出了忧悒的神色,“不过,现下我最担心的是你,镇洋王的奏章既已发出,皇上若是信了他的话,会不会降罪于你?”
“会,但降罪不过一时,待到真相大白,我一定会平安无事。”上颢回答,他沉着的语气让云檀心头的惶惑消失大半,她倚靠在他怀里,只觉得世事纷繁复杂,想不出一个万全之策来。
***********
☆、美人陨落
入夜时分,海风依然带着湿润的气息,洁白的浪花泛出了淡淡的血沫,浮云飘过澄黄的明月,浩朗的夜空中繁星乍现,群山巍巍然竖立,宛如一把把巨大的尖刀,刀锋迎着海浪,越磨越锋利。
空广森冷的宫室里一盏灯都没有点,四面雕窗大开,夜风穿室而过,偌大的殿堂内纱幔乱舞。
宫中的陈设很凌乱,仿佛刚刚被人洗劫过一番,檀木书架被人推倒了,卷轴文书落得满地都是,风大的时候,惨白的宣纸满室飘飞,黑暗的宫殿中弥漫着一股阴森森的诗意。
云裳喜欢这样的诗意,当冷风吹过她的指尖,她整个人都沉浸在微凉的夜色里,耳边隐隐绰绰地可以听见遥远地方,浪打岸礁的轻响,潮水声一波接着一波,她感觉到一种欣然而起的喜悦,每当这种喜悦冉冉而生的时候,她的灵感也会随之蓬勃漫涨。
她沉浸在这样神妙幽诡的感觉里,世间所有纷扰在这一刻统统都轻若无物,生与死,爱与恨,都像是一场戏,而她不仅不在戏中,甚至连看戏的人都不是,她懒得观摩,懒得思索,她懒得为那些瞬息万变的东西浪费眼泪和感情。
世人明知唯有变化才是永恒,却还要为改变的心意,轮转的名利而郁郁寡欢,她觉得这不安分的世界能给人的只有失望,而黑暗中流光溢彩的灵感则超越了一切世俗的快乐,那是真正属于她的,不需要任何人给予或施舍。
红衣佳人坐起身,漆黑的长发铺满了绯丽的宫裙,她的眉目即使素面朝天也浓艳如画,女子匆匆忙忙地走到烛台边,点燃了一支蜡烛。
淡淡的烛光照亮了一处阴暗的角落,空寂的宫室中只有女子衣裙窸窣的声音在忙碌地回响。
云裳借着微弱的烛光在地面上摸索着,她欣喜地拾起一张空白卷轴,急切地走到花梨木的桌案边,执起一支光亮的紫毫笔,饱蘸墨汁,在卷轴上飞快地谱写起来。
她希望自己书写的速度可以快些,再快些,那样就能跟上脑海中一闪而过的旋律。
夜风穿窗而入,吹得烛火一阵乱晃,满地的书卷散了开来,裱金的卷轴滚得到处都是,陈旧的书页哗啦啦地翻过了一页又一页。
云裳对此浑然不觉,她潜心于编写曲谱,直到一阵杀气腾腾的脚步声由远及近,她檀口中轻哼的旋律才戛然而止,女子如梦初醒般抬起头,孱弱的烛火在夜风中最后闪烁了几下便彻底熄灭了。
明月的微光里,她只觉得一阵旋风在急速靠近,有人一把抓住了她的头发,将她从木案后拖了出来,云裳惊呼一声,完全跟不上那人的步伐,她踉踉跄跄地往前走,时不时被脚下的红裙绊倒,然后又被人粗暴的提起来。
“放开我!放开我!”红衣女子尖叫起来,她扑向那人,伸出尖利的指甲往他脸上一通乱抓,苏烈将她拖到宫门外扔在地上,云裳头晕目眩,她披头散发地挣扎了半天才站起来,身体左摇右晃。
“你想干什么?”她眯起眼睛,在浓郁的夜色中寻到了苏烈的身影,“你这条疯狗想要干什么!”
回廊上的侍从们吓得纷纷跪倒在地,战战兢兢。
“不要脸地东西!”苏烈一个耳光将女子打得背过身去,重重撞在门框上。
云裳不以为然地笑了起来,她的半张脸当场肿了起来,人却转了个身,背靠在门边笑个不停,“不要脸又怎样?就算我是个婊/子,王爷不也照样离不开我吗?”
“毒妇!”镇洋王忍无可忍,一声狂吼,他噙着泪的眼睛里布满了血丝,头发从束发冠里纷纷散落下来,苏烈扑上去,双手紧紧抓住女子的头发,疯狂大喊,“你害死了虔儿!他的年纪那么小,跟你有什么仇?你这条毒蛇!”
云裳一愣,紧接大笑了起来,她恶狠狠地瞪着苏烈,毒辣的话跟连珠炮一样从她艳丽的红唇中蹦了出来,“你怪我有什么用?谁让他是你的儿子呢?跟你一样像条狗,看见漂亮女人就走不动路,让他干什么,他就去干什么!他满心满眼都只有我,连他自己都没有,更何况是你这个爹!”
苏烈听完后吃惊地看着她,仿佛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人一般。
他一直以为云裳的个性高傲倔强,超凡脱俗,除了逆来顺受之外,只会用沉默来进行反抗,可他没有料到今夜,这双诱人的嘴唇里竟会吐出那么恶毒的话,更没有想到她那颗孤冷骄傲的心会酝酿出那么恶毒的计划。
或许她厌世已久,又始终得不到解脱,于是满腔的烦闷之情在潜移默化间变成了怨毒和愤恨。
“好,好……”苏烈死死瞪着她,目光凶恶,“我记得你说过,你的心里只有音律,对吗?你的歌声才是你的生命,是不是?”
云裳冷冷地瞅着他,她在不顾一切地发泄后,突然感到一阵恐惧从脚底蔓延上来,“你想怎样?”她顶着一头蓬乱的长发,咬着牙发起抖来,“你到底想怎样?”
“来人!”苏烈冷笑一声,他的目光像匕首一样牢牢扎在云裳的脸上,只听他切齿道,“把这个女人给我拖下去,让她吞炭,吞烧红的炭!本王倒要看看,没了这副百灵鸟般的歌喉,她还能自以为是些什么?”
********
镇洋王府内的乱子刚告一段落,敌军便再次大肆进攻,艨艟战舰纷纷如蚁,乘风而来,军中有高人吹笛,控制海中异兽,闹得天水城哀鸿遍野。
好几次,眼看着敌军就要攻破岸堤,璇玑海一带的百姓纷纷弃屋而逃,城中乱成一片,各个城门都挤满了逃亡的人,水军各营都遭到了严重的侵袭。
上颢每天接到的战报数不胜数,敌军本就擅长水战,深谙声东击西的策略,让人分不清究竟哪里才是主战场,放眼海上,入目尽是硝烟,没有一处安宁。
他已经连续三天三夜没有回行馆了,军营里忙得不可开交,上颢已经料到回去以后,一定会看见一个满怀闺怨的少妇,云檀最擅长玩这种把戏了。
记得有一次,他外出征战,走了两个月才回来,云檀一看见他便腰肢款摆着迎上去道,“哟,这位军爷好生俊俏,我家夫君已经很久没有回来了,不如你来陪陪我吧!”
每次念及女子的音容笑貌,军人的脸上总会不自禁地露出笑容。
营帐外的战鼓声接连不断,他正寻思着要不要出海,刘都尉挺着圆滚的肚子没精打采地走了进来。
刘都督自从腿摔折后,手下的人为他打造了一副木头拐杖,可即使如此,他也没法乘船打仗。
“将军,让我上船吧。”他恳切地对上颢说道,“我这样留在后方怪难受的,不如上阵杀敌来的痛快。”
上颢抬起一双因为熬夜而布满血丝的眼睛,“你可以去,不过去之前最好想清楚,要是一浪打来,你一个人掉到海里去也就罢了,如果有下属为了救你而白白搭上一条命,那可划不来。”
刘都督听后相当气闷,他将双杖往地上一扔,单脚立着,昂首道,“将军看不起我呢!”
“刘都尉胆子真不小,敢冲上将军发火!”
这时,姜少安风风火火地冲了过来,他的形容十分狼狈,身上的戎装被撕烂了一大片,左臂上有一道三寸长的伤口,鲜血流得整条胳膊都是。
“姜校尉这是怎么了?露着血口子给谁看呢?”刘都尉立刻将满腔憋闷的怒火转移了过去,大吼道,“这里没有美人儿为你掉眼泪!”
姜少安满头大汗,他一边扯下衣上的布条包扎胳膊上的伤口,一边急切地禀报道,“将军,不好了,防线被冲破了!”
上颢皱了皱眉,“步兵可有阻拦?”
“闻将军正率人死战。”
“我也去一趟。”上颢说着起身,匆匆随姜少安离开了大帐。
这处战火四起,将士们抛头颅,洒热血;那处的王府却是悲悲戚戚,白幔低垂。
云裳被关进了大牢,这所牢狱是天水城最肮脏的地方,里面关押的罪犯,几乎人人都背负着好几条人命。
连日来,云裳受足了刑罚,她躺在干草垛上,皮肤是冰冷的,身体里却像在被人焚烧。
烧红的炭被人用铁钳强行塞入她的口中,滚烫的温度像把火,从咽喉开始烧,一直烧入了五脏六腑。
她张开嘴,想听听自己的声音,可入耳的只有一种嘶哑恐怖的怪音,她不相信这是她的声音,于是试了一遍又一遍,试到最后她发疯一样哑声乱叫,将身下的干草拨得乱七八糟,热泪从女子的眼睛里滚落出来,染满了整张脸。
胃部的剧痛让她弯起了身子,她感到自己的内脏在滚烫的温度中逐渐融化,血变得越来越粘稠,越来越干,云裳痛苦地抬起头,她看见了石墙上的高窗,稀薄的光芒从那里透进来,她可以望见灰白的天空正渐渐被黑暗吞噬。
那片浩大沉寂的天空下有什么?
会不会是大海呢?
她拼命扬起脖子,想要透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