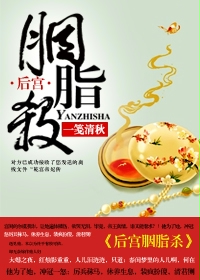胭脂与杀将-第5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苏烈一声不响地看着她,她觉得时间像是过了一个世纪,镇洋王突然挥手一拳打在她脸上,他的拳头很硬,毕竟是个好弄枪舞刀的男人,力气一点也不比当兵的人差。
云裳被打得整个人都翻倒在地,她的嘴里吐出一口血,刹那间头晕目眩,整个脑袋嗡嗡作响,脸上火辣辣得仿佛烧起来了一样,苏烈慢慢走到她跟前,俯身抓住她的一条胳膊,将她提起来粗暴地扔在了床上。
云裳只觉得浑身骨头都在那一刻散了架,之后的事情犹如一场酷刑,到处都是破碎的衣衫,床上是毫无温情的肢体纠缠,粘腻的汗水从交叠的身躯上流淌下来沾湿了衾被,她咬住嘴唇扭过脸去,觉得趴在自己身上的男人就像一头发情的野兽,原始,肮脏,下流,愚蠢,所有低劣的词汇都很适合这一刻的男人。
当晚,苏烈并没有在她的寝宫中过夜,等到一场欢情结束,镇洋王便披了衣裳,拂袖而去,云裳听见宫门砰地一声合上,终于长长地吁出一口气。
她没有立刻穿上衣服,而是赤身裸体地躺在锦绣堆叠的卧榻上,目光迷离地望着流苏帐顶,云裳的胴体是一片无瑕的雪色,她的容颜和身体都将女人的美丽发挥到了极致,可她自己却毫不在意。
云裳为人所爱,却从不爱人,她不相信人世间存在真正的爱情,她认为那是欲|望的代称,或者更美好一些,它是长久不变的感激之情。
她曾经细细地想过,如果有一个男人愿意长久地善待她,一心一意,体贴周到,她也许会出于感激而表现出善意,并且对他永远忠诚。
所以,在云裳眼里,世上至高境界的爱情也不过是感激之情,她对此毫无兴趣,与其让她爱一个男人,倒不如让她爱自己的小妹妹,云檀显然要比那些污浊的男人可爱多了。
不过,那些人,那些事都不足以让她上心,这世间唯一能激发出她热情的东西便是音律。
云檀不久前曾好奇地问过她,“姐姐,既然你只爱唱歌,那又何必渴望自由?留在这座宫殿中并不妨碍你谱曲弹唱。”
“不,这妨碍到我了。”云裳那时摇了摇头,烦躁地将手伸入长发里,将发髻胡乱地打散。
没有自由的日子确实削弱了她在音律上的造诣,只是这样的感觉该如何与云檀解释?她又如何能明白?
云裳爱的不仅仅是唱歌那么简单,她热爱阴天,热爱暴雨,还热爱电闪雷鸣,狂风巨浪,她热爱一种怪异的,介于虚妄与真实之间的意象,那种意象来源于大海,以及海中那个神秘寂静的世界,它看不见也摸不着,却能激发她那潜在的热情。
这股热情是异于常人的,而她曲艺上的天赋也确是举世罕见。
从小,云裳的世界便充满了袅袅余音,树木的婆娑摇摆,花儿的盛放凋零,那都是一首首完整的乐曲,它歌颂着枯荣流转的生命,从初章至终章都磅礴又绚烂,她似乎能听见花言柳音,鸟声兽语,她的脑海中永远都飘浮着各色各样的旋律,一闪即逝,新陈交迭。
秉异的天赋让她尝到了一种超脱凡俗的乐趣,同时也削弱了女子作为常人的情感,她渐渐对凡夫俗子,红尘琐事都丧失了兴趣,并时常被一种深深的,无法排遣的寂寞笼罩,因为世间没有一颗心灵能与之相通,她的天分有多高,寂寞就有多深。
如今,苏烈囚禁了她,她无法回到海边,无法置身于浪涛,更无法自由自在地追逐探索那些神秘的意象,所以她恨他们,恨他们妨碍她拥有活着的唯一乐趣。
深夜,云裳裹了一条丝绸床单缓缓从卧榻上走了下来,宫室里一片漆黑,朦胧的月光隔着纸窗透了进来,女子没有点蜡烛,她的眼睛向来只望向高高的云天,不需要将这真实的人间看得太清切。
今夜,在遇上苏烈之前,她偷偷见了小世子苏虔。
云裳几乎是看着这个少年长大的,她刚来的时候,苏虔才十三岁,镇洋王当他是个孩子,等到他十六岁的时候,苏烈依然将他视为孩童,只是一个孩童怎么会用那样的眼光去注视父亲的姬妾?
云裳时常在心里默默地嘲笑这对见色起义的父子。
苏虔从十六岁起就开始迷恋她,他敢涉险来这片禁地看她,愿意为她出生入死,干杀人越货的勾当,甚至敢于背叛自己的父亲,她从小世子的身上看到了一丝希望——或许她可以利用这个情绪极端又热烈的少年来摆脱镇洋王。
于是,云裳引诱他,给他尝到了甜头,让他陷得更深,反正她向来不在乎自己的贞洁,这具皮囊与身外之物无异,必要时完全可以贡献出来用作交易,而且她不用担心会怀上孩子,因为苏烈一直都让人给她喝凉药。
镇洋王虽然对她爱不释手,却也十分地倨傲。
他瞧不起她,因为她是个卑贱的,出身于商贾之家的亡国人,是他的战/俘,他的女/奴,他怎么会让一个奴/隶怀上皇族子嗣?
云裳垂下一头及膝的乌发,裹着丝绸床单缓缓走到窗边,夜风带着海水的腥味迎面吹拂进来,黑夜浓得化不开,她听见了海浪声,却什么也看不见。
今晚,苏虔见她的时候十分反常,他处心积虑的谋划似乎被外人发现了,那个人的身份很高,高得让他不知该如何抗衡,她看着这惊慌的少年扑倒在她的腿边,将脸埋进她宽大的裙幅里哭着忏悔,说他再也不愿做伤害父王的事了。
云裳当时既没有反驳也没有责备,恰恰相反,她像个温柔长姐一样,轻轻抚摸着少年的头顶,柔声道,“傻孩子,别再为我做那些事了,我又没有拿刀逼着你,从今以后,你若是想我,偷偷来看我便是,只要你的父王不知道,我们仍然能在一起。”
当她说完这番话的时候,小世子的眼泪已经消失了,她温柔的声音简直比天籁还要动听,等到苏虔抬起头,对上女郎充满关怀与怜悯的眼波时,他心中的恐惧与悔恨统统都不见了,眼睛里只剩下在黑夜中闪闪发亮的倾国之色。
“不,我一定会让你离开这里。”少年握紧了两只汗涔涔的拳头,指关节发出了咯哒响声。
云裳没有再多说一句话,只是对他绽开了笑容,笑容中充满了母性的关怀与恋人的柔情,这样的笑她从未对镇洋王展露过,小世子激动得浑身发抖,他腾地站了起来,热切地望着她。
可惜苏烈就在那时候带着随从来了,苏虔一惊,矫健地跃入了黑压压的草丛里,而云裳则施施然顺着回廊走向宫室。
此时,云裳立在窗前静静地等待着黎明的曙光。
她闭上眼睛,依稀听见远方传来规律的浪涛声,她想起了小时候凫水嬉戏,肆意玩耍的日子,那些盘桓在脑海中的旋律,由狂风暴雨猛烈地伴奏着,让她的心灵跟着激荡起来。
每当这时,傻得可怜的小世子和暴戾阴冷的镇洋王就会化作了天边的浮云,风一吹就在她的脑袋中消失不见了。
*********
作者有话要说: 姐姐表示天才总是寂寞的~
☆、生命如雨
海边的腥风吹动着海浪,呼啸的风声像是野鬼们阴戾的嚎叫。
傍晚时分,璇玑海岛国再次来袭,他们趁着月阴云密布,太阳无光的时刻乘风而来,依然是火攻为上,快船开浪,战舰你来我往,不是接舷跳帮,便是撞杆相拼。
天水城施行了严格的海禁,坚壁清野,将士们擐甲执兵,水上各营排兵列阵,牢牢守住各大行道海峡,上颢分发各营督军一支令箭,倘遇紧急军情,允许他们一面飞报上级,一面调度各汛口的兵力。
出海作战以气象为先,可惜这些日子老天爷似乎想好了要跟雩之国对着干,潮水与风向一个劲儿地往天水城扑,敌军顺水顺风,十几艘点燃了膏腴油脂的小型火船轰轰烈烈地窜入了雩之国的军阵,那速度快如离弦之箭,一路点燃了好几艘楼船,焰光随着他们的行进明晃晃地亮了一路,烈火四处迸射。
舰队里的水手们齐心协力,吆喝着从船上伸出长木,左勾右挑,费了好大的劲儿才将突入阵列的火船一一打翻,与此同时,东西两营横向杀出,直攻敌军两翼,试图截断璇玑岛国的船队,使他们应接不暇,双方迅速陷入了僵持,刀剑相接,互不相让。
谁料祸不单行,天上忽然下起暴雨,宛如银河倒泻,海上浊浪滔天,狂风大作,由于水面上战乱频繁,船只相撞的巨响惊动了海中异兽,这些体格庞大的动物咆哮着从波浪中冒了出来,四处攻击战船,狂性大发。
沿岸的后营中,一艘又一艘战舰出发前去支援,船上的战士各居其位,船上的气氛紧张而肃穆。
这些经过了严苛训练的水兵虽然个个劲捷过人,但还是初次经历如此可怕的战役,战舰上悄无声息,暴雨冲刷着战士们刚毅的面庞,不安和恐惧在每个人心中无声无息地蔓延。
上颢最后一个走上船,水手立刻收起了连接海岸的跳板,战舰缓缓离开了安全的港口。
远处,金铁交鸣,火光冲天,行驶的船上却死寂一片。
这一战几乎与赴死无异,战士们的目光都有些迷离,因为此时的平静极有可能是他们平生最后一次能想想家,想想心事的机会。
上颢从一排排罗列的战士中间缓缓走过,他的身上有一一股独特的冷漠气质,这让他看上去虽然跟大家一样处于险境,却又好像完全不在场似的,只是冷眼旁观着正在发生的一切。
船上的气氛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军人淡漠的神情,沉着超脱的气度让战士们没来由地感到一阵轻松。
“呦,将军又亲自来了啊。”在上一次的战役里不幸断了一条腿的刘都尉,撑着拐杖慢悠悠地向站在船头的军人走去,他笑吟吟道,“像将军这般人物,何必亲自出战?坐在帐幕里头比划比划就行了。”
“不需要亲自出战的人是你,”船只大幅度地转了个弯,避开了水中的暗礁,上颢伸手扶住栏杆,“你这条断腿还能跟人打吗?”
刘都尉发出了一声沙哑的笑,“要死也得跟战士们死一块儿,我最讨厌那种高高在上的将官,只会躲在帐子里指手画脚,却让将士们去替他送死。”
他说着用双拐将身子支得更直了一些,“刚开始,我以为将军跟那种人一样,只把自己的命当命,对手下的人根本就不顾惜,不过现在看来,是我弄错了,人总有些例外的,对吗?”
上颢微微一笑,他的眼睛一直注视着前方的战况,并没有仔细听他说话。
随着战圈越来越近,风雨加剧,长空与水浪融为一体,明月躲在乌云后,连一丝光芒都不肯泄露,远处,有庞然大物从从水中跃了出来,它仰天咆哮一声,那力度简直能摇撼整个天地。
战船虽隔得很远,却也发起了剧烈地摇晃,战士们竭力稳住身形,上颢抓住了摇摇欲坠的刘都尉,没让他跌下海去。
“往左,补进前方阵线。”上颢低声吩咐掌舵者,又对身边的传令官道,“通知后方船队,拨两艘战舰支援左营。”
“是,将军。”
船舱内立刻升起了红蓝两面旗帜,挥动了三下,后方的船队望见便立刻行动起来,两艘战舰迅速从队伍中分离出来,箭一样窜向了远处火光最大最盛的地方。
接下去发生的又是一场残酷的恶战,生命如大雨中的水滴,密密麻麻地陨落在狂暴的大海中。
战舰一入战圈开始便像飘萍一般脆弱,四处乱窜的火船,随时从海中跃出的奇兽,突如其来的咆哮声,无不惊心动魄,震天撼地。
战士们疯了一样地杀敌,带火的乱箭在空中飞窜,随着船尾发出的一声巨响,几十丈高的水浪扑打下来,战船登时开裂,慢慢地往下沉,战士们手持利器,身子却左摇右晃,随后东倒西歪地跌成一团。
“弃船——!”上颢大吼道。
一支强硬的劲弩不知从哪儿飞射而出,精准地射中了一头骊龙的要害,巨兽浓稠腥气的血液狂喷出来,像雨水一样泼洒在船只上,淋得将士们满身满脸。
庞大的战船正在以缓慢的速度倾斜,狂风呼啸,大雨滂沱,高高的桅杆轰隆一声倒了下来,上颢正往船头奔去,忽然听见了一个非常微弱的声音在呼唤他。
“将军,将军……”
他回头一望,只见一个小战士的腿被折倒的桅杆压住,他摔在地上,一张染着血迹的脸朝上,正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将军,”他瞪着惊恐的眼睛望向不远处的军人,“救救我,救救我,我不想死!”
“弃船!统统弃船——!”上颢见状,向四周狂吼了几声,然后快速奔向那个被桅杆压住的小兵。
他本以为将他从桅杆下面拉出来即可,可等他走近了才发现,这年轻战士胸口被一种钝重的兵器砍伤,整个腹部都豁了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