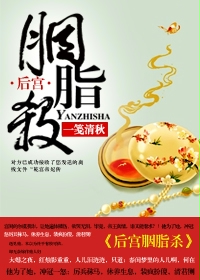胭脂与杀将-第3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于是红霞夫人开始傅粉施朱,盛装打扮,一看见上颢便目挑心招,可惜无论她怎么挑引,怎么搔首弄姿,都没得到一星半点的进展。
有一回,她差点以为自己就要成功了,因为上颢破天荒地没有抗拒□□,让她顺利地坐到了他的腿上。
女子心中大喜,立刻施展伎俩,露出妖娆情态,千般娇艳,万般勾魂,可他一点反应都没有,她不甘心地宽衣解带,罗衫半褪,又抓住他的手,放在自己雪白的胸脯上,可他依旧冷若冰霜。
对红霞夫人而言,人生最大的耻辱不是为人玷污,而是赤身裸/体地出现在一个男人面前,那个男人却无动于衷。
上颢看了她半天,最后只是笑了笑,“像你这么不知自重的女人,倒也是罕见。”
说完,他突然抓住她的头发,将她拖出了书房,回廊上的仆侍顿时全看见了她衣不蔽体的模样。
红霞夫人乱喊乱叫,拼命挣扎,可这点力气对上颢根本起不了作用,他抓着她就像抓着一只兔子,毫不客气地把她拖进上老将军的屋子,扔到他床边。
“爹真是大方,把自己的女人送给儿子当通房。”上颢冷笑着对上铭说道。
上铭气得瞪大眼睛,几乎没法呼吸,等到上颢离去,他勃然大怒,抽出腰上的鞭子,关上门狠狠抽了红霞夫人一顿,可惜戎马半生的老将军最终还是屈服于女人的媚术之下,竟是下不了狠心将她逐出府去。
红霞夫人从此看清楚了上颢的面目,他是个铁石心肠的人,没人能从他身上挤出半点好处,更不用说将他勾引过来为己所用了。
就此,她对上颢的感情从春心荡漾变成了痛恨,这痛恨的来源不仅是希望的落空,更是自尊心的损害,于是她调转矛头跟上隽厮混起来。
上隽对父亲的继室早就觊觎已久,两人一拍即合。
他对弟弟的仇恨与红霞夫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两人在个性上的契合程度更是□□合缝,他们都唯利是从,阴险狡诈,只要有足够多的利益就能六亲不认,并且以此为荣,不知羞耻。
红霞夫人知道了上隽的难处后,便借机向上老将军施媚,待他睡熟,偷偷溜进了他的书房。
上铭时常与小儿子在书房议事,她在桌案上发现了一张地图,上面画有上颢行军的线路,她记下后立刻赶去告知了上隽。
上颢虽然知道上隽的图谋,却并不晓得他埋伏的地点,如果临时改变路线则更容易节外生枝,所以他除了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之外,没有别的法子。
果不其然,行军途中,上隽的伏兵如约而至。
为了保险起见,上隽左思右想,最后还是决定将伏兵设在了一条归城必经的道路上。
那是一处荒凉的滩地,白裕长河横穿过方圆四百里的土地,周围杂草丛生,花木凋零,四面群山环合,高耸入云,将战火死死围困在中心。
这支凶猛的伏兵人马很杂,上隽接受了叛军残兵,又令自己麾下的劲旅扮作南漠勇士,让人以为这是三王爷的部下卷土重来,跟自己一点关系都没有。左将军虽然料定这支归来的大军已经人困马乏,战意全无,可事先还是做了严密的部署。
在他的计划下,白裕河一战打得极其惨烈。
千里迢迢从南漠赶回来,已经累得面黄肌瘦的将士们几乎憋足了劲,轮番攻击,疯狂突围。他们确实已人困马乏,只求归城安歇,未料眼看着就要到达目的地了,中途却又横出一支彪军,硬生生拦在近在咫尺的安逸之前,叫他们恼怒异常。
上隽派人用战车围成一道道屏障,横栏在前方,又让□□手趁机放箭,将冲上来的人统统当成活靶子,上颢率领千余骑兵左冲右突,他们越过对方用战车围成的屏障,撕开阵脚往前猛冲。
将士们皆心知肚明,若是冲不破这堵黑墙,便只能命丧于此了,归家团聚的希望将会像泡影一样消失,于是求生的欲望令他们野性迸发,将士们凭借着‘闯过这关就能安富尊荣’的信念拍马冲杀。
面对如林的戈矛,他们宛如飞蛾扑火一般迎了上去,谁料两方战得正酣,战局后方忽然又有鼓声擂动,一股长长的烟尘向这里蔓延过来,堵死了他们的退路!
看来上隽这次是没少动脑子,上颢不禁有些意外,他没料到他竟派遣另一支军队人衔枚,马裹足潜伏在暗中,用前军吸引对手注意,继而再由后军突出,将他们杀个措手不及,果真是高明又毒辣。
此时,两堵黑墙一前一后夹了过来,上颢当即指挥全军分成三路,一路正面突围,另两路抵挡后阵,前军只能冲突,决不能后退,只要形成突破口,他们便有逃脱的机会。
千声号角响起,万面战鼓擂动,广阔的滩地上人声鼎沸,万马嘶鸣,旌旗横斜倒地,喊杀声震得地动山摇,一方冲突,一方截杀,很快便血流成河,尸体堆积如山。
上颢率军拼死扑杀,他们无论在体力上还是人数上都已全然不及对方,即使凭着爆发的兽性狂冲也无法持久。
很快,五万人马便折损了大半,而敌军黑墙般的阵仗也被冲出了一条宽约三四百步的缝隙。
三万余人马争相涌向这条突围口子,后面的军士围追堵截,战车步卒如潮水一般掩杀而来。
上颢引军断后,周边金铁交鸣,短兵相接,他们勉强引出了一万余骑,敌军便从两侧挤压上来,重新堵上了这个细小的裂缝。
年轻的主将不得不舍弃剩余的人马,且战且退,这场大战持续了约莫两个时辰之久,三万多的将士只冲出了不到两万,还人人带伤。
随主将断后的陪戎副尉常岄,臂上,腿上多处被砍伤;庞凌副将背上中了一箭,腰上被砍了一刀,血流不止;上颢自己被迎面而来的战刀在脸上留下了一道三寸长的伤口,俊秀的面目染满了鲜血,十分可怖。
***********
作者有话要说: 男主就是在这里被毁容的,不过没有关系,男人的帅不在于脸,气质好就行,哈哈
☆、往事:逼亲
好在虽然全军主力伤亡不少,他们总算杀出了重围,直奔皇城而去。
白华帝大喜过望,他立刻犒劳三军,论功行赏,当日便传命大设宴席,以慰军士长日奔劳苦战,大小三军尽皆受封,人人手拿御赐美酒,放怀举杯,欢欣雀跃。
这支胜利之师连月来在鲜血与阴谋中挣扎,一路淌血归来,劫后余生的战士们刚刚失去了成千上万的战友,浑身负伤,有些甚至再也不能骑马握剑,从鬼门关走过一回的人对于身外之物往往会展现出超然的淡漠,他们面对荣华富贵时,心里竟不似平常那般激动,唯一的执念便是与家人团聚。
上颢如今已经官拜正三品,只比上铭差两级,他又年纪尚轻,不好擢升,于是苏昂赐给他紫服玉带,黄金千斤,又有绫罗彩缎,美酒馔玉,成箱成匹地抬入府中,王侯大臣纷纷前来道贺,整座府邸又一次呈现出张灯结彩,门庭若市的景象。
军人脸上的伤口几乎深可见骨,因为没有得到及时治疗而发炎,起初整张脸都惨不忍睹,过了三四天才有好转的迹象。
上颢自从回府后一直都闭门谢客,倒不是因为脸上的伤,而是他每次打完仗,总有那么一段时间会变得非常自闭,连上老将军也拿他没有办法。
不过,上颢回府当晚,曾无视仆从们接二连三的阻拦,径直冲进了上隽的书房。
进门前,他便听见了里头的争吵声,上隽正勃然大怒,破口大骂着什么,文素音则微弱地辩驳着,细柔的声音宛如黄莺在狂风暴雨中啼鸣。
上颢冲进去的时候,文素音正满脸泪痕,衣衫不整地立在桌案边,她的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看见上颢突然闯进来也顾不得礼节,捂住脸飞快地跑了出去。
年轻人的戎装上散发着血腥味,他刚下战场,满面血污,脸上豁开一长条口子,在夜色里显得十分狰狞,他盯着上隽,怒火在一双黑眼睛里燃烧。
“如果你要杀我,拿上刀,穿上盔甲,直接与我决一死战,我乐意奉陪!可你为了一己私欲,殃及无辜,让一万多人命丧黄泉!堂堂左将军既然视人命如草芥,为何自己却敛身匿迹,在战场上连个头面都不敢露?”
他的声音宛如戛玉敲金,字字都铿锵有力,上隽察觉出弟弟的眼神中有一股想要将他大卸八块的狠劲,心里先是一慌,可紧接着便平静下来——他的父亲还没死,上颢是不敢轻举妄动的。
于是,上隽坐在椅子上从容不迫地一笑,他今天难得没有喝酒,神志非常清醒,所以他接下去说出来的话再也不能归结于酒后胡言了。
“打仗嘛,死个万把人是常事,弟弟打了那么多年仗,怎么还是看不透这一点呢?”他懒洋洋地开口,这副好逸恶劳的模样在喜欢他的女人眼中是意态疏懒,轻狂不羁。
上隽说着,眼里泛起一丝讥讽,“上颢,你跟你娘很像,不管吃了多少苦头,心里总抱着一些清新隽永的念头不放。她对那百无一用的书生忠贞不渝,不肯接受我爹的恩惠,连个笑容都不愿给,可结果呢?不还是死得那么早吗?至于你,你大可以派遣手下的兵将来暗算我,可你从来不,因为你把人命看得太重,从不肯伺机利用,但是你要知道,在兵连祸结的年岁里,最廉价的东西就是人命。”
他说着,从椅子上起身,慢慢绕过桌案,“你可以说我是奸佞小人,但如今世风日下,唯有顺应世道,才能步步高升,英雄都是应运而生的,至于诚实正派,赤胆忠心,其实并无用处。你看,我高居庙堂,只要挥挥手,便能让你浴血奋战,而你呢?你的军职比我高,打仗比我厉害,却也不得不受制于我。”
“如此说来,你成了一个识时务的俊杰了?”一行鲜血从军人眉角的伤口处淌了下来,他的脸上血迹斑斑,目光却又冷又亮,“既然你自以为是个顺应世道的人才,那我问你,这么多年来,你做成了什么事?你上过几回战场?立过多少功勋?除了那班酒肉朋友,军中又有多少人敬重你?”
上隽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征战非我所长!”
“好!既然征战非你所长,那你可会写诗?可会作画?”戎装青年咄咄逼人,“你可曾有过箴言高论?除了损人利己,滥施职权,你还知道什么?”
上隽气得浑身发抖,一时竟无以辩驳,他面红耳赤,又羞又恼,上颢冲上去一把抓住他的衣襟,将他狠狠撞在墙上,咬牙切齿道,“从小你就想置我于死地,可时至今日,你成功了吗?”
说罢,他突然抽出腰间的短刀,划破了上隽的脖子,殷红的鲜血流了出来,左将军只觉脖子上一凉,紧接着又温热起来,吓得浑身直打哆嗦,再也顾不得面子,战战兢兢地开始求饶。
“这种时候,你还觉得人命轻贱吗?”
说罢,上颢收起刀,将对方狠狠地掼倒在地,再也没看一眼。
**********
却说云檀,她照旧在皇城内招摇撞骗,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身体一天比一天差。
上颢率军回城的时候,她就站在人群里远远看着他,跟出征时一样,此次归城也是在华灯初上,人声鼎沸的夜色里。
他的脸受了伤,流满了鲜血,她几乎认不出他来了,看着他策马徐徐行进,表情仍旧是肃肃穆穆的,既看不出得意也看不出骄傲。
云檀不知怎么地,忽然觉得全身发热,泪水不自禁地涌了上来,一行接一行地从眼睛里流下来。她无可奈何地发现自己还是很想念他,虽然这已经是离开他的第二个年头了,可她的感情从来没有变过,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迹象。
日子缓缓过了下去,差不多又过了三四个月,这三四个月里发生了两桩大事,让云檀措手不及。
第一桩是通缉令,这伙贼人在皇城里骗倒了不少富商权贵,渐渐引起了官府注意,官吏们画影图形地试图捉拿,可惜缉捕文书上的头像画得实在是太糟糕了,就算云檀站在这画像旁边,都不会有人相信那就是她。
第二桩事情比第一桩要棘手多了。
有天,云檀上街的时候觉得有些异样。
一辆马车在暗里跟踪她,这情况已经持续好几天了,她本来以为只是错觉,直到有一天,她居然在黑鼠的院子里看见了那辆马车,才真正惊慌起来。
他们迎来了一位贵客,是个年过七旬的老人,他的头顶上几乎没有头发,一对眼珠枯黄浑浊,脸上的肉松松垮垮地垂着,身上瘦得皮包骨头,却穿着非常昂贵的华服,坐着豪华的双毂马车,由两匹的卢宝马拉着,很是气派。
但见他走进主屋,坐在正中央的位子上,前后左右分立着四个彪形大汉。
等云檀走进去的时候,那老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