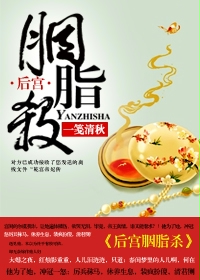胭脂与杀将-第3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枪,斗得火光迸发,双方转眼便斗出了十余合,却是平分秋色,胜负难定。
上颢从不畏惧体格庞大的对手,他的副将庞凌与张正德同样身高体长,平日里经常与他比武较量,他对于如何规避千斤之力,以巧取胜,有着十足的经验。
今日,上颢之所以制止了弓箭手,又亲自出战是对张正德留有余情,毕竟他在西容城时,张将军曾对他照顾有加,因此在决斗之初,上颢只采取守势,并未痛下杀手。
可惜张正德并不是这么想的,他悲愤填膺,志在杀敌,越打越来气,每一次攻击都是致命杀招,上颢只守不攻显然不是长久之计,对手的斩马大刀接二连三地落了下来,有一回竟划穿了他的铠甲,砍进血肉里,一缕鲜血从他的肩头飙了出来!
士卒们见主将受伤顿时紧张起来,远方的弓箭队立刻拉弓瞄准了张正德,随时准备将他射成刺猬。
对阵的二人交马而过,上颢长/枪执手,飞马便回。
这一次,他再也不留情面,回马冲杀,举/枪就刺,张正德拍马舞刀,两人又战在一处,难分难解。
上颢发现这威名远播的张将军虽然膂力惊人,打起仗来如猛虎出山,却远不及庞凌灵活,他使的武器是□□,流星锤一类的重物,收势极其缓慢,时常露出空门,上颢有过好几次将他一举击毙的机会,却并没有付诸行动。
双方又战了三十余合,张正德彻底失去了耐心,他狂吼一声,扔出流星锤,锤子连着铁索飞出,上颢恰恰纵马而来,他快速闪身一避,同时一枪搠去!
流星锤力道刚猛,张正德一击不中来不及撤回,顿时左胸空门大露,而上颢正一枪击出,势不可挡,只听见一声铁甲崩裂的脆响,铁枪当胸刺入,上颢收不回凶猛的余力,竟是当场将他刺了个穿!
胜负已定,两马交驰而过,鲜血从张正德口中涌了出来,他巨大的身体软绵绵地往后一仰,从马上跌了下去。
兵士们见主将不仅赢了战役,还将叛军将领当场格杀,惊喜地敲击盾牌,狂呼起来。
上颢迅速勒停了奔马,他跃下马背,大步走向倒在地上的对手,张正德浑身是血,他不甘心地扭动着庞大的身躯,喉咙里咕噜咕噜地冒出鲜血来。
军人走到他跟前,低头看着他,脸上没有丝毫喜悦和得意的神色,只是伸出手,将长/枪从对手身上/拔/了下来,濒死的人猛地痉挛起来,鲜血从胸前的窟窿里喷出来,溅在上颢的军靴上。
“张正德——!”
远处忽然闪现出一个红影,风尘仆仆的女郎策马飞奔,那竟是朵雅公主,她居然不管不顾地冲到战场上来了!
朵雅在几丈开外的地方跳下马背,向战圈狂奔,好几个将士试图阻拦她,可她爆发出一股惊人的蛮力,硬是冲过了拦截,扑到重伤的将军跟前。
“你怎么了?怎么了?”她跪在他身边,发现他全身几乎被鲜血给浸没了,女郎颤抖着伸出手,却不敢碰他,一阵剧烈的悲痛从心底冒了出来,她的眼泪失控般落下来,洒在那大个子的脸上。
“你……和他……他……”他睁大了眼睛,努力想要抬起头。
“我和他半点都不相干啊!你这个蠢货!”异族女郎发疯一样哭喊起来,“我早就连他什么模样都不记得了!只是说一些气话罢了!没脑子的东西!你跑来打这场仗完全没道理啊!”
上颢站在一边,他听见这样的话,顿时明白了这场决战的来龙去脉,看着地上即将死去的猛将,他的眼睛里盛满了阴忧,隐约还有几分痛心。
张正德吃力地对妻子露出一个微笑来,他的笑容展到一半,忽然吐出一大口血,庞大的身体开始不住地在地上扭来扭去,他的嘴巴张开又合起,仿佛想说什么,但又抑制不住口中涌出的鲜血。
红衣女郎哭得撕心裂肺,这强烈的悲伤几乎与一年前得知部族被灭时相当,虽然它未必会持续很久,但至少这一刻,她是真的痛不欲生,“你这个傻瓜!快点站起来啊!我跟你回家!再也不求富贵了!咱们归隐乡间!从此以后你去哪儿我都跟着!”
上颢的脸色十分阴晦,他冷漠地瞥了她一眼,转身走向自己的战马,朵雅公主见他离开,忽然站了起来,她提起裙子疯了一样追上去,好像凭一己之力就能报仇雪恨似的。
军人听见身后的脚步声,霍然回过头去,他的脸上呈现出罕见的暴怒之色,嘴角边的肌肉因为愤怒而微微往一边抽搐,他压低了嗓音问道,“你跟着我做什么?”
异族女郎吓了一跳,还未来得及回答,便听他大声喝斥起来,“张将军已经为你送命了!给我回到他身边去!”
朵雅蓦地打了个激灵,军人脸上毫不掩饰的轻蔑和厌恶让她又羞又恼,女郎狠狠一跺脚,只觉愤恨的情绪跟浓烈的悲伤搅在了一起,让她几近崩溃。亏她自诩聪明那么多年,这一次却实实在在地当了回傻子,如今这场祸事除了怪她自己之外,谁都怪不了。
女郎越想越恨,她冲着上颢离去的背影胡乱地尖叫了一声,然后奔回张正德身边,跪了下来,他似乎有什么话要对她说,脸上的神态异常柔和,朵雅竭力想听清楚他口中的低语,却怎么也办不到。
这大个子看了她一会儿,嘴巴张了张,然后抬起手,她不知道他是不是想抚摸她的脸颊,只是犹豫着将脸凑了过去,可他的手已经落了下去,紧跟着身子往左边一歪,嘴里又淌出一行血,便再也不动了。
*********
作者有话要说: 让我们欢送女配一号,朵雅公主!鼓掌~~撒花~~
☆、往事:污辱
自从第一次行骗成功后,云檀就接二连三做起了当诱饵的行当。
她知道,在整个行窃的计划里,她这个诱饵是最重要的,一旦她出了岔子,他们后面统统都没戏。
大半个月后,这一行人得到了不少钱财,云檀之前听蓝缎阿姐说过要共享富贵的话,便旁敲侧击向他们打听起分成的事来。她寻思着等攒够了钱就偷偷溜走,待找到地方安定下来就偷偷回来将老妇人也一并带走。
可惜她还是太天真了,蓝缎阿姐听到分成的话哈哈笑了起来,她亲切地握着少女的手,露出那种让人难以设防的诚挚笑容,“傻孩子!说什么傻话呢!咱们给你吃给你住的,你还要分什么成呀!”
云檀这才意识到自己是落入了什么样的圈套,从此以后,她怕是要一辈子给他们当诱饵,根本没有出逃的机会,要是哪天运气不佳被逮住,说不定还要在雩之国吃牢饭呢!
云檀心里虽气急,却也无可奈何,她当晚彻夜未眠,冥思苦想,把自己弄得精疲力竭,却什么主意也没想出来,最终还是打算随遇而安。
接下去的几个月里,她继续给他们当诱饵,凭着几分小聪明一次又一次地圆满完成任务。她一会儿上酒楼,一会儿是茶铺,有时逢上节日,她便打扮地花枝招展地去赏灯会或去寺庙上香。
大多数时候,她都能得手,不过偶尔也会遇上一些品格高尚的正人君子,对她的明示暗示都无动于衷,这些人算是给了她一点安慰——原来男人并不是个个都那么无可救药的。
有时她会忍不住想,要是上颢遇到这种事会怎么样?他能做到不为所动吗?
每到此时,她便像个怀/春少女一样猜来猜去,然后又强迫自己不去想他,结果却往往适得其反,一个细小的声音总会不合时宜地从心里冒出来:“只是想一想罢了,算不得罪过,怕什么呢?”
不过最有趣的是,有一回,她都已经把一个年轻公子引上了马车,可却突然发现不对劲。那人对她说着话,手却悄悄抚上了她的耳垂,他看中了她那对贵重的耳挂,而她正瞄着他腰间的玉佩。
“你是个偷儿!”她一把抓住了他的手。
那人打量了她片刻,恍然大悟道,“你是个饵!“
两人瞪视了对方半晌,继而笑了起来,然后他跳下了马车,大家各找目标,扬长而去。
蓝缎阿姐见她给他们带来那么多收益,自然非常高兴,平常对云檀的态度是亲热的不行,除了分成这事她不答应,其他衣食起居,她都有求必应,好像云檀是她的亲女儿似的。
可另一个少女柳丝儿却不待见她,她看她的眼光总是很冷漠,带着七分骄傲和三分敌意。
原来柳丝儿从前也是假扮富家小姐给他们当诱饵的,但自从云檀来后,她就成了一个可有可无的角色。
云檀从小在大户人家长大,千金小姐应有什么样的举止她早就烂熟于心,怎么提裙子,怎么摇扇子,看男人的时候眼睛怎么瞟,她根本不需要刻意去学。
柳丝儿却是在花街柳巷中长大的,她最熟悉的是风尘女子的一举一动,即使穿上名贵的裙袍,佩上精良的簪珥,也毫无大家闺秀的风范,反倒像极了都市驰名的红/妓,好几回,她被人看出了端倪,要不是有一双矫健的双腿让她跑得比羚羊还快,她恐怕当场被抓去吃牢饭。
有一回,云檀路过灶房的时候,听见柳丝儿在里头愤愤不平地跟蓝缎阿姐说道,“她长得一点都不好看,一张清汤寡水的脸,跟得了痨病似的,哪里讨人喜欢了?”
“可她有本事让人上钩,你呢?”蓝缎阿姐洗着池子里的碗筷,漫不经心地回答,她跟柳丝儿的应该很熟,因为她对她说话的时候从不会露出那种假装亲热的笑容。
“我怎么了?”柳丝儿将抹布往灶台上一甩,尖声尖气地说道,“从前你们靠我挣了多少钱财,现在翻脸不认人了?”
蓝缎阿姐无可奈何地回过头来,想跟她说些什么,眼角的余光却瞥见了云檀,于是立刻向柳丝儿抛去一个眼色。
柳丝儿一愣,转身看向门边,只见云檀手里拎着一个茶壶走了进来,浅浅笑道,“天气冷,我下来倒些热水,打搅你们了。”
“哪里话!”蓝缎阿姐立刻笑着迎了上去,她接过她手里的茶壶,往里头灌满了刚烧开的水,一边亲热的叮嘱道,“这水烫得很,你拿上去慢慢喝,小心一点。”
“好,谢谢阿姐。”云檀又笑了笑,她拎着茶壶走回自己的房间,然后关上门,走到铜镜前坐下,细细端详起镜子里的容颜来。
她未施粉黛的脸非常苍白,十分柔和的五官跟她的人一样没精打采,她想到柳丝儿那句‘跟得了痨病似的’,竟觉得有几分形象,不禁又好气又好笑。
这些年她消瘦了许多,不仅褪去了少女时的娇憨和可爱,举止也变得越来越老练,随着心头的热情日益减弱,她对粗言暴行也不再震惊,有时甚至不得不费些心思,装作天真可欺的样子才能引人上钩。
她的橱柜里挂满了鲜艳的衣裳,梳妆台上堆着簪珥钗镮,□□精巧,件件生辉,这些东西就像是她的武器,每当她精装盛饰完毕,就好像铸就了铜墙铁壁,她变得不再是自己,走出去便能无所畏惧。
日子一天天地过,仿佛看不到尽头,有一天夜里,云檀睡不着觉,披了一件外衫去楼下的院子里散步,等她吹够了凉风,提着灯笼回房时,突然在回廊上撞见了黑鼠。
黑鼠喝醉了酒,醉醺醺地拦住她的去路,她进一步,他退一步,而她退一步,他则进一步,好像她不让他满意,他就不会放她走似的。云檀看出了他的企图,跟他面对面僵持起来,黑鼠冲她呵呵地笑,嘴里传出一股难闻的酒气。
云檀心想这么耗下去不是办法,于是伸手一把撕了纸糊的灯笼,掏出里头的蜡烛往黑鼠身上扔去,烛火碰上他的衣服立刻烧了起来,她趁机夺路狂奔,穿过回廊,转了个弯,闪入自己的屋子里,将门牢牢关上,又拴上了门闩。
“你这个贱/人!”那黑鼠在回廊上乱骂乱嚎,他使劲拍打着身上的火焰,蓝缎阿姐听见声响从屋里冲出来,“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过道上传来一阵夹杂着尖叫的骚动,火光亮一会儿,很快便被扑灭了。
云檀贴在门上听着外面的动静,心怦怦直跳,她觉得自己得想一点自保的法子,于是开始在屋子里踱来踱去,最后目光落在一个陶瓷花瓶上,少女走过去将它砸碎了,从中挑出几片又长又尖的,用布条裹住一端当匕首用。
她在枕头地下塞了一把,常穿的衣服上也系了几把,又再梳妆台的抽屉里藏了一些尖利的碎片。
果不其然,那个长着八字胡的男人并没有那么轻易放过她。
过了约莫三五日,蓝缎阿姐跟柳丝儿上街去了,而那老妇人则一个人在西面的厢房里休息。
黑鼠很少去看她,从前他去看自己的母亲也只是为了要钱,现下更是不上心,给老母亲地方住,便觉得自己仁至义尽了。
老妇人受了打击,身体每况愈下,如今已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