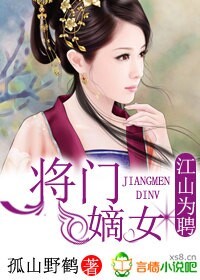江山别夜-第7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你与他犯下不伦的罪行,你为他杀害了太子又杀害了君王,你帮着他将这天下搅得一团混乱——
可是他竟然就这样让你去死?!
这样的死,难道还值得么?
梅慈没有回答,也再不会回答了。
薄暖挥了挥手,内官们上前抬走了她的尸体。
“在思陵旁边另起一陵,让她能与孝怀皇帝相依相望吧。”
她的声音里,终于有了叹息的痕迹。
顾泽即位后,薄暖终于在宣室殿中休息了下来。
这一休息,便是整整七日七夜,顾渊的丧礼,全数缺席。
治礼的官僚找不到顾渊的尸身,只能以衣冠入殓。薄暖留下了那一把鎏金弓,挂在床头,每日呆呆地凝望。寒儿唤她吃饭,她便吃饭;唤她沐浴,她便沐浴;一切事务都抛给了孙小言和一群外朝官僚,自己成日价只是发呆和睡觉。
当顾泽惊闻阿母“暴病而卒”,曾赤着脚跑来宣室殿大哭大闹,孙小言直接甩去了一个耳刮子。
“皇太后还在休息,岂容你大吵大闹!”孙小言厉声叱骂,“既是要做皇帝的人,便该有个九五之尊的样子!”
顾泽呆了一呆,这才明白过来,自己的眼泪已经不顶用了,他从此成了皇帝,再不会有人在意他的眼泪,也再不会有人在意他内心里是如何想的了。
他摇摇晃晃、恍恍惚惚地往回走,感受着身上格外庄重的丧服带来的从未体验过的威压。天色苍茫如铁,映照未央宫千门万户冷笑般的飞檐。他收了泪,抽着鼻子,宫婢宦侍们都跟在他身后几步远,不敢上前相陪。
“阿泽。”
忽而,角落处传来一个平静的声音。
顾泽怔忡地转过身,双眸忽然大睁,嘴边咧开了一个真正欢喜的笑容。
“夫子!”
***
不论经历了怎样的严冬,春日也总是会来的。即算它来得迟,即算它来得浅,它也总是会来的。
烛火摇漾的宣室殿寝殿中,一切都仿佛还是昨日的样子。书案上凌乱的简牍,床边的玄表金綦履,帘后缓缓消磨的龙涎香……都是他的,又都不是他的了。
床头的那把鎏金弓已经被拉坏,不能再用。薄暖盯着它,想象着顾渊在山崖上为人所迫,只能靠着一把弓支撑自己——
她闭上了眼。
她决不能再想了。
睹物怀人,是一种痛苦,又何尝不是一种慈悲?如果没有这些物事,她甚至会怀疑那些缠绵入骨的爱恋与相思,都不过是她自己的黄粱一梦。现在梦醒了,她看见荒凉的炊烟袅袅上升,回头,江山已换了主人。
“无耻……”她低声喃喃,“便想这样将担子都卸给我么?无耻,无耻之尤!”
帘后人影微动,是寒儿在添香。薄暖现在已离不开龙涎香了,仿佛那是一种令她镇静的麻药。她深深吸了一口气,感受到那曾经流转在顾渊身体里的浓郁香气又在她的血液里凉了一遭,才慢慢地发话:“寒儿。”
“奴婢在。”空阒之中骤然被传唤,寒儿受了一惊。
“聂丞相和安成君还没有找到么?”薄暖疲倦地问。
寒儿轻声道:“没有。太后不必忧心了,聂丞相和安成君都是有福之人……”
一声冷笑,打断了寒儿好心的安慰。薄暖稍稍挑起了年轻得苍冷的眉,那神态竟酷似她刚刚死去的丈夫:“有福之人?那你看,大行皇帝和本宫,算不算有福之人?”
寒儿被这句话堵得哑口无言。想宽解她,又不知从何说起,难道要硬着头皮承认这天人两隔的夫妻是有福的?薄暖感受到她的无奈,自己的心也如香灰一寸寸萎顿下去,终而,声音也衰竭了:“将奏疏拿来我看看。”
“是!”寒儿大喜过望,太后终于肯起身了!她连忙去书阁里搬来了一些奏简,不敢搬太多,怕累着太后。
薄暖披起衣衫走到书案前坐下。那是顾渊惯常坐的位置,他坐在这里,手握着刀笔,凝眸批阅奏疏,一批便是一整晚。灯火微明,她躺在床上看着他如削的侧脸,她常常想,这就是她的丈夫,她即将共度一生的男人,他会是个了不起的好皇帝,大靖朝堪与孝钦皇帝比肩的中兴圣主……
现在再想过去,那种种悠远的幻想,竟都成了讽刺。
寒儿正打理着床榻,忽然听见一声刀笔落地的轻响。她回过头去,却见御案之前,年轻的太后容色惨白,手中的笔杆掉在了地上,双眼死死地盯着案上的奏疏。
寒儿心头一咯噔,莫不是那奏疏上有什么忌讳的东西?薄暖却突然转过头来了,朝她厉喝一声:“叫孙小言过来!”
“喏!”寒儿连忙提着衣裾奔了出去,片刻之后拉着孙小言气喘吁吁地跑回前殿,薄暖突然抬手,将一卷奏简重重砸在了地上!
“这都是什么东西?”她的眉目间仿佛凝了冰霜,寒气微微,令人心胆皆战。孙小言连忙抢上,将那竹简一抖,只是掠了一眼,脸色便刷地青了。
“这……这都是些什么人?”他将竹简哗啦抖开,直接去看抬头上的署名,“御史、廷尉、太常、少傅……他们都要薄昳还朝?”
☆、106
薄暖的目光空落落的,“他们明明知道……是薄三害死了……先帝……”
“先帝”两个字,依然能让她声音发颤。
“不,”孙小言惊骇了片刻便沉稳下来,“他们不知道。”
顾渊遇害,事属机密,外朝百僚只知道他是丧生于乱军之中,却全然不知幕后实情。
薄暖茫然地转向他,“他们是在逼我。”她指着孙小言手中的奏简,惨然一笑,“那个廷尉黄济,曾经也是子临亲手拔擢,不成想连几斤骨头都没有!”
孙小言沉默。群情汹汹,岂是一两个公卿所能左右?薄家根深蒂固,薄昳素有令名,何况又是小皇帝的老师,这时候百官上疏请求让薄昳还朝,并不奇怪。
便是薄昳这时候说要自己当皇帝,他都不会奇怪了。
“子临好不容易收拾了薄氏五侯,”薄暖喃喃,“没想到,竟是给阿兄——给薄三做了嫁衣。现在太皇太后没了实权,侯府又接二连三地倒了,薄家满门上下,连带满朝的门生故吏,想来都指望着薄三了吧?”
孙小言微带悲哀地抬眼,看着荧荧灯火下的阿暖。实在是太年轻了啊,大约才将将二十吧?就成了皇太后,成了这座沧浪中飘摇的王朝之舟最后的掌舵人。顾渊过去将她保护得太好了,她纵然智计万方、才华横溢,却也从没有应对过这样诡谲多变的人心与朝局,由而,她也就从来不曾体验过顾渊所处的这种绝境——
这种天下人都等候着他的英明神武,而他却再也拿不出丝毫办法的绝境。
***
纵是薄暖下令将他们的奏疏全都压下,群臣却仍在前赴后继地上书请求让薄昳还朝主持危局。
他在暗中布置的力量,已经渗透军队,渗透官场,渗透民心。
他甚至已经不需要再借助外戚的身份,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带着帝王师的荣耀风风光光地还朝了。
压垮薄暖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一封加盖了天子玺印的帛书。
帛书上的字稚嫩笨拙,却是堂堂正正的天子御笔。年仅五岁的小皇帝一个字一个字地斟酌过了,向他名义上的母后呈上了这一道百余字的请愿,抑或说是威胁。
薄暖看着那帛书上的玺印,微淡地笑了。
她除了笑,也不知道还能怎样面对这个无知的孩子了。
“你是皇帝,”她说,“你下的诏书,便本宫也无权驳回。又何必再问呢?”
顾泽的眼睛一亮。
“母后的意思是,夫子终于可以回来了?”
那样幼稚的眼神,那样单纯的孩子。薄暖疲倦地闭上了眼,在她幽沉昏暗的脑海中,顾泽一身明黄朝服、通天冠、云纹履的模样竟似与另一个孩子的眉眼重合了……如果,如果是民极在位,一切会不会不一样?
不,不会。
这天下已经从里而外地朽烂尽了,不管坐龙庭的人是谁,都不会改变山河残破的事实。
她又怎么能再去责怪一个不懂事的孩子?
大正五年五月诏,皇太后兄薄昳令德素著,贤能威重,兹令还朝,拜为大司马大将军,并袭广元侯爵,益封五百户。
薄昳意气风发地迈入承明殿,冠服一新,至为尊贵的金印紫绶将他的身形衬托得更加修长出尘,宛如庭中玉树。小皇帝站起身来,满脸欢笑地迎接他的老师,他志得意满地从容一笑,撩起衣襟,行了个端端正正的大礼。
“臣薄昳,参见太后、陛下,太后、陛下长生无极,大靖享国永昌!”
薄暖坐在垂帘之后,安安静静地接受了他的朝拜。薄昳站起身的一瞬,目光似有意似无意地扫来,刹那间仿佛耀出了尖锐的银芒。
他舍弃了养育自己的父亲,舍弃了依恋自己的女人,舍弃了信任自己的朋友,舍弃了不知道多少寻常人引以为幸福的东西……才走到今日这一步。
他知道,薄暖也知道,这世上,已经无人能阻拦他采摘那最后的果实。
六月,广元侯薄昳进爵安靖公,益封千户。皇太后临朝,薄昳秉政,百官总领于昳,而太后之旨不能出三宫。
七月,定赵王太后谥号孝静皇后,起静陵。募三辅流民,编为常胜军,赴益州、淮南平叛。
八月,上祭宗庙,安靖公称摄皇帝。立明堂、辟雍,考天下风俗,定于明年改元更化,与民更始。
与改元诏书同时下达的,还有一份递往内宫的帛书。
皇太后之母陆氏,久在睢阳,冢茔不扫,贻羞王室。兹命羽林三百,护送皇太后往睢阳省墓,迎陆氏梓宫回京。
看到这一份将她赶往睢阳的诏书,薄暖再也忍受不住,腾地站了起来。玄黑的衣袍盖住了她的痛苦,而发上华贵繁重的步摇仿佛狠狠压下了她的怒火。
“他已经是摄皇帝了,”她的手在长袖中颤抖,“他到底还想怎样?”
孙小言拱手垂立,恻然:“太后……可想回睢阳去?”
她怔住,刚才还在燃烧的目光一霎便暗沉了下来。
睢阳?
那是个多么遥远的地名啊……
她离开睢阳,也不过才五年光景;可是这五年就像梦一样,所有的爱恨悲欢,全都在这五年里一把烧成了灰,将她的心烧得只剩下一个空洞的华丽的壳子,她站在这苍茫废墟上回头望,竟然已完全看不清楚五年之前,睢阳的梁宫里,那年少无知的欢喜。
寒儿低着头,她不知道睢阳有什么,但她已看懂了太后在方才那恍惚的一瞬,眼眸中透露出的脆弱的迷恋。她在睢阳,一定埋藏了很多很深的记忆吧?
孙小言轻声道:“太后,容小的说句不中听的话……这天下,自先帝崩逝时起,便已经落入安靖公的怀里了。不管他会不会真的篡逆,宣室阁上那个小孩子,都是收不住人心的……”
薄暖咬着牙道:“那又如何?这是子临的江山,子临不在了,我便要替他守住!”
“太后您忘了,”孙小言悄悄挑起了眼帘,“仲将军还在云州,他手底还有十万兵马——安靖公这会子既然要将您赶出去,您不妨将计就计……”
薄暖脸色微变,眸光一瞬千幻。
孙小言几乎有些不忍心去看她此刻的眼神。当一个人明白地知道了自己的一举一动都会影响全天下,于是便将万事万物在她的掌心里一个一个地取舍时,就会有这样的眼神。
如临深渊,明明满怀恐惧,却又隐露兴奋。
她要报仇。
***
天边残阳渐渐吞噬了长安三宫的巍峨阴影,皇太后的辇舆仪卫缓缓行出了皇城门,薄暖带了寒儿,任由车马摇摇将自己带离了那片深不见底的吃人的宫闱,仿佛有什么东西掉落在了那里,再也找不回来了。
皇太后出巡睢阳,路途虽遥远,也必要保证十分的舒适。然而路上却总见到饥民哀哀的眼神,纵然羽林郎在前肃清道路,他们也常疲弱得挪不动身子。有一些郡县令长已经管控不住辖内大乱的局势,所能摆给她看的只有一条干净的道路,而在这条道路之外,阖州百姓都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她每每攥紧了车窗上的木棂子,才能以指甲上尖锐的疼来磨钝一心的抽痛。这就是子临心心念念的江山,它已经千疮百孔,纵然薄昳是神仙再世,只怕也救不回这个世道了。
睢阳郡的郡守府移到了北城。皇太后亲临郡治,实在是前所未有的大贵重之事,睢阳郡守全家都俯伏在府前跪候了一整天。薄暖自车中下来,扶起陈郡守颤抖的身子——
她知道他为什么颤抖。因为他也不知道面前的这个皇太后还能做多久的皇太后,也就不知道自己这个郡守还能做多久的郡守。
她和颜悦色地道:“辛苦太守了。本宫想到自己过去的那间茅舍中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