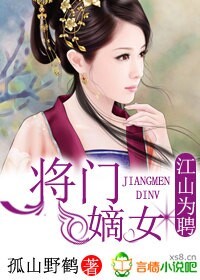江山别夜-第1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为何行此大礼?”薄昳温和地道。
薄暖低声道:“阿暖犯了大错,请阿兄责罚。”
他看她片刻,并不扶她起来,只是慢慢地道:“你与殿下有旧,我与父侯都是知道的。本朝不是那样泥古讲礼,你未及笄,他未纳妃,都是小孩子心性,今晚的事情……不过玩玩闹闹,没什么大不了。”
她惊讶地抬起头,这话绝不似兄长这样秉礼的君子说出来的。然而薄昳确实是说出来了,月色下他的面容优雅温文,她小心翼翼地回道:“阿兄对阿暖好,阿暖谢谢阿兄……”
他无味地笑了一声,摇摇头道:“这样便算对你好了?”回身欲要离去,又顿住,补充了一句:“然而无论如何,你还是应当收敛一些,除非……除非你要嫁给他。”
十一月初三戊申夜,有星孛于东井,越华盖而贯紫微,锋炎直犯天极五星,凌帝后之域,彗长亘天,白月夺色。天象剧变如此,初四日宣室殿的朝堂上响起了无休无止的论辩声。
有人说,这是孽子配嫡,陛下应尽早让梁王回封地上去,并考虑立储大计。梁王不逊,不足以承天命;太子终究还是襁褓中的顾泽合适。
有人说,这是中宫侵夺,陛下应尽早立梅婕妤为皇后,而文婕妤亦不可再随子之国,应当留侍宫中,以尽夫妇之义。
但也有人说,这长星贯紫微,与未央宫无关,而是长乐宫的问题。
当丞相仲恒说出这话的时候,承明殿上一片倒吸凉气之声。
皇帝端坐帐中,珠玉冕旒之下的神情模糊难辨,煌煌大殿之上,只听见他沉沉的声音在一百三十二根朱红廊柱间徘徊撞击:“依仲相的意思,上天是在警戒谁?”
有些精乖的大臣斜眼去瞧薄家的五位列侯,广穆侯薄宵是一贯的肃穆冷峻,广昌侯和广忠侯已有些按捺不住,广敬侯面色忿忿然,广元侯薄安位次最末,眸色淡然如水,身子前倾,却是在认真倾听仲恒弹劾自家的奏疏。
仲恒掸了掸衣襟,恭声道:
“陛下!上天有德,为天变以告命。当今外家薄氏,操持权柄,政由己出,是以天降妖星,窜入紫微帝王之垣,是以为戒!请陛下三思!”
空气静了。
忽然有一位大行令自席间走了出来:
“臣附议!仲丞相恳切为国,臣亦请陛下三思!”
大臣们三三两两,都走到了大殿中央来,其声洪亮:“请陛下三思!”
皇帝静静地看着这恢弘的承明殿中表情各异的臣僚们。有的仍然坐在席上,然而左顾右盼,已是不能安坐;更多的人是随仲恒一起跪在了殿中请命;而那些姓薄的重臣,却都是一言不发,直到——
直到广元侯薄安走了出来。
皇帝的眉头轻轻一挑。
薄安迈正步走到殿前,将儒冠先除去,恭恭敬敬地放在了地上。殿中一时没了声息,但见他双膝跪地,三叩首道:“臣等有罪,令陛下生外家跋扈之疑,今臣自请免官还第,请陛下成全!”
仲恒的目光投注在他身上,带着三分端详和七分冷淡。
薄安又叩首下去:“请陛下成全!”
皇帝突然站起身来,拂袖道:“退朝!”
皇帝弃了车,径从殿上复道往昭阳殿行去。复道上的直棱窗糊得严严实实,不透一丝冷风,然而皇帝的袍袖依然带起了猎猎风声。冯吉在皇帝之后亦步亦趋地紧紧跟随,冷不防皇帝一停步,沉声发问:“梁王今日怎么不来上朝?”
冯吉眼帘微垂,“回陛下,梁王殿下今晨派人来告了假,道是昨日游冶无度,伤了一只手,无法面圣。”
皇帝眉头一动,“伤了一只手?严重么?”
冯吉态度平静,好像他根本没有感知到皇帝话语里的关怀一般,公事公办地回答:“殿下不肯就医,似乎并不严重。”
皇帝点了点头。昭阳殿眼尖的女官已望见了圣驾,立刻准备了起来,过不多时,梅婕妤便在殿前严妆迎候。皇帝踱步而前将梅婕妤扶起,拍着她的手寒暄几句,忽然又转头问冯吉:“十月旦的宫宴上,太后似乎跟朕提起了一个人?”
冯吉压弯了腰,无人能看见他的表情:“是,广元侯流落在外的女公子前些日子已认祖归宗了。”
“朕听闻这薄家女郎还曾是梁王宫里的侍婢?”
冯吉顿了顿。
“是。”
“让她过来见朕。”皇帝说着,拉着梅婕妤的手往昭阳殿中去了。梅婕妤低声与他盈盈笑语,他的脸上终于绽开了夙日不见的笑容。
“——什么?!”
“哗啦”一声,案上简册都被拂去,顾渊“唰”地站了起来,身形笔直如剑,眉目中尽是凛冽剑气:“再说一遍。”
孙小言战战兢兢地道:“陛下、陛下宣阿暖去昭阳殿面圣,现在女郎大概已在路上了……”
顾渊一步迈过了书案,双袖平举抖了抖,“给孤更衣!”
孙小言吓了一跳:“殿下这是要去哪儿?”
“给孤更衣。”顾渊冷冷地道。
孙小言只得去衣桁上取下他的常服,想了想,又放回,拿了一套朝服来,顾渊扫了一眼,轻轻哼了口气,没有指责,那便是默许了。
孙小言给他扣上玉带钩,他自己又下意识地紧了紧。孙小言咽了口唾沫,终究没能忍住劝谏:“殿下这会儿去面圣,那才前想好的手伤不朝又怎么解释?今日朝议闹得凶,陛下召见阿暖,或许只是为了让广元侯宽心罢了……”
“你知道孤最恨陛下什么吗?”顾渊突然转过身来,直直注视着他。
这话大逆不道,但大逆不道的话顾渊也不是第一次说了。孙小言有些不敢听,低了头哈了腰不知怎么接的好,顾渊已冷冷续道:“孤最恨他用女人作饵。十三年前,十三年后,一模一样。”
孙小言呆住。
梁王已径自离去了。孙小言看着那挽起的晃动不已的梁帷,心中慢慢盘算着:十三年前……十三年前,是玉宁八年。
玉宁八年,陆氏谋反族诛,陆皇后忧死。
昭阳殿前殿。
薄暖已跪了两个时辰。
盯着那一扇十九折的琉璃镶青玉屏风,她脑海中响起了另一个人淡静的声音:“当孝愍太子在的时候,孤每到宫中赴年宴,第二日清晨往温室殿去请安,都要跪上三五个时辰……孤的母亲与孤一同跪,就跪在前殿的屏风前……等陛下跟里头的夫人出来,那屏风都快被孤盯出洞来了。”
她拧动发酸的脖颈望向殿边铜漏,却原来只过了两个时辰。不知那人每年是怎样熬过这三五个时辰的?这可不同于跪在外面。殿间那珠粉色的纱幔微微拂动,旖旎而引人遐想,令她感到窘迫——
皇帝为什么要在这里宣召她?
最最不可理解的是,皇帝为什么要宣召她?
忽然有女官自内殿走去,急急提醒了句:“陛下来了。”便去殿侧掌起灯火。一时灯烛高烧,将这暮色沉沉的前殿照得一片通明,而皇帝在冯吉与几名内侍的随同下缓步走来了,并不见梅婕妤的影子。
皇帝绕过那屏风,走到殿中央的蒲席前,屏退了左右,才淡淡地道:“起来吧。”
☆、上帝甚蹈
薄暖谢恩站起,目光沉静。皇帝端详她半晌,“你与你母亲并不相像。”
这话说得莫名其妙,薄暖却也不恼,微微一笑:“是吗?”
从无人敢用这样的反问来应答天子的。皇帝饶有兴味地挑起了眉,那神色与梁王有三分相似:“你更像你的姑祖母,薄皇太后。”
“确实有人如此说。”薄暖笑颜愈展,如上林苑中轻绽的白海棠,风姿绰约,令皇帝恍了恍神——
毕竟是一具年轻的躯体啊……柔嫩而芳香,好像没有经过一丁点人世风霜,而温柔得可爱。皇帝想,她与薄太后终究是不同的……她那么年轻,年轻得仿佛一种岁月的挑衅。
他上前,抬起苍老的手掌轻轻抚过她的脸颊。她顿时慌了,脸上的血色随着他的手掌移动哗啦一下就褪了个干净,想后退又不敢,想拒绝又不能,两条腿好像都陷进了泥地里,她简直要惊恐地朝下方看,她明明记得自己踩着的是赤纹长寿砖啊!
皇帝突然笑了,一下子收回了手,眼底一片冰凉,“你那样紧张作甚?”袍袖一挥,背过了身去。
她张口结舌,语无伦次:“奴婢,奴婢陡识天颜,心中惶恐已甚,还请陛下恕罪!”说着又跪了下去,“请陛下恕罪!”
皇帝眉头一皱,还未言语,殿外忽然哗啦啦跪了一片人,有女官尖着声音道:“殿下,梁王殿下!殿下不可!”
皇帝上前迈了三两步,而顾渊正正跨过了门槛,目光往跪着的薄暖身上一扫,一掀衣襟拜了下去:“儿臣向父皇请安!”
薄暖心头猛地一颤,双眸中的雾色又浓了几分。
擅闯内廷,这是大过!
皇帝狭长的双眸危险地眯起,双袖负后,冷冷地压抑着语气道:“梁王未经通报径闯内廷是为何?朕以为梁王是通礼的!”
顾渊静了静,“正因为儿臣好读《礼经》,所以儿臣听闻今日朝议大事,惴恐难安,不得不出此下策。”
他的话音端得很稳,薄暖悄然侧首,看见他面目冷峻,眼神一错也不错,就好像他真的只为朝议而来,而根本就不曾注意到她一般。
皇帝冷笑,若说这世上还有人能看穿梁王的九曲心肠,那必非他的亲生父亲不可。皇帝负在身后的手摆了摆,立时便有内侍入前,恭请薄暖退下。
薄暖不敢多看,随着那内侍出了昭阳殿,殿外站了一人,身躯挺拔,劲甲红缨,将银盔抱在怀中朝她欠身一礼:“末将仲隐,恭送女郎回府。”
薄暖一怔,但见黄昏的最后一抹霞光正落在这郎将挺阔的眉宇之间,俊逸飞扬,神情爽朗。她矜持地抿唇一笑,往前走了几步,那郎将立刻跟了上来。
她不得不停步,“仲将军可与仲相国有故?”
仲隐笑了,露出洁白的牙齿,映衬冠玉般的肌肤,还真不似个武将,“正是家父。”
薄暖顿了顿,再抬眼去打量这人,揣摩他的年纪与梁王应不相上下,又想及仲丞相在朝议上的表现,缓缓地道:“是殿下让您送我的么?”
仲隐微怔,他没有料到这少女聪慧如斯。“是,宫中多事,殿下命末将保护女郎周全。”
薄暖淡淡一笑,不再多话,往前而去。仲隐看着她如瀑的长发在盈盈一束的腰间轻漾,怔忡了片刻,便即随上。
“末将统属未央宫程卫尉,官拜公车司马。女郎以后再来未央宫,有末将所能效劳之处,但请吩咐无妨。”
“相国公子,何以来做这样的苦劳呢?”薄暖目光带笑,夜色降下,她的话音温和如风。
仲隐摸了摸头,就像个大男孩一般神情赧然,“末将是家中庶子,女郎切莫取笑了……”
“小女子先谢过将军了。”薄暖笑道,“改日还会再去拜谢殿下的。”
高门庶子,为博一个前程,不惜攀附藩王。这个仲隐看似少年意气,其实内心深沉,也是充满了利弊计算的吧?
薄暖微微叹了口气。已经行到未央宫门口,百级丹陛之下,便是薄暖来时乘坐的侯府轺车。夜幕如铁,将她的面色都变作了一片模糊,她朝仲隐行了个礼:“将军请留步。”
仲隐点了点头,似乎还想说什么,喉结动了一动,却是忍住了。她转身离去,衣袂在台阶上翻飞如蝶,他看着她窈窕而静默的背影,突然喊出了声:“女郎!”
她的脚步停了停,未及转身,他已快步上前,抢到她面前站定,甲胄的光将她的眼神反射出千万种神采,却又全部陷入黑夜的沉默中去了。她缓缓抬起头,缓缓地道:“仲将军还有何见教?”
他定定地注视着她的眼睛:“女郎可知如今天灾人祸,灾患不息,流民千里,乃至于易子而食?”
她惊怔地笑了:他这是在教训她吗?贫穷和与贫穷相关的一切,没有人能比她更了解了!“仲将军想说什么?”她讥讽地道,“忽然良心大发,要来与小女子发一通经世济民的议论吗?”
“不。”仲隐摇了摇头,俊颜上表情坚定,“末将只是希望女郎知道,这江山危殆,唯有梁王……唯有梁王差可救之。”
她安静了下去。
许久,许久,她向他敛衽行了一个大礼。
“仲将军言出肺腑,阿暖永铭在心,绝不敢忘。”
回到侯府,父亲薄安正端坐正厅等候,兄长薄昳立时迎上前来:“陛下如何?”
父兄脸上都没有丝毫的喜色,这令薄暖多少松了口气。她的家人,终究不愿意让她一个女子去阿上求荣的。
“陛下只是问了我认祖归宗的事情。”她淡淡道,“让阿父阿兄担心了。”
薄安忽然道:“殿下还在与陛下争辩昨夜星象么?”
她一惊,原来父亲已经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