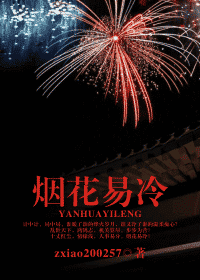烟花未冷-第4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浮屠塔断了几层断了谁的魂
痛直奔一盏残灯倾塌的山门
容我再等历史转身
等酒香醇等你弹一曲古筝
雨纷纷旧故里草木深
我听闻你始终一个人
斑驳的城门盘踞着老树根
石板上回荡的是再等
雨纷纷旧故里草木深
我听闻你仍守着孤城
城郊牧笛声落在那座野村
缘份落地生根是我们
听青春迎来笑声羡煞许多人
那史册温柔不肯下笔都太很
烟花易冷人事易分
而你在问我是否还认真
千年后累世情深还有谁在等
而青史岂能不真魏书洛阳城
如你在跟前世过门
跟着红尘跟随我浪迹一生
雨纷纷旧故里草木深
我听闻你始终一个人
斑驳的城门盘踞着老树根
石板上回荡的是再等
雨纷纷旧故里草木深
我听闻你仍守着孤城
城郊牧笛声落在那座野村
缘份落地生根是我们
伽蓝寺听雨声盼永恒
是日傍晚,古城深巷略显斑驳的大门前,一个身形挺拔的男子垂着空空的两手驻足良久,终于伸出手……
只因一篇偶尔看到的歌词,耿清泽拔腿出了家门,一路上浑浑噩噩,好像想起了和那个人的点点滴滴,又好像什么都没想,只是做了个但愿长睡不醒的梦,回神后,人已站在洛阳城里,站在她家的门前。
几个月了,他找不到她,也没有她的一点消息,但始终未敢踏入这里半步。门里是否会出现他所希望的情景,他没有半分把握,甚至连猜一猜想一想的勇气都没有。
那句一言九鼎的承诺生生钉在心头,如影随形,绝无更改的可能。他只怕见不到她,却更怕见到她……
手掌被紧闭的门扉挡住后,他俯下身,翻开最上层的台阶中右数第三块,果见那把门钥匙静静躺在里头。
直到此时,他才没来由地松了口气,开门而入。
茶几上空无一物,木架上的古筝被封在绒套里……一切都是他上次离开时的样子。他没有踏进曾经住过的屋子,停在门把上的手又将门拉上,似乎唯恐多看一秒便会教自己想起在这里品茗听筝那个夜晚。
他进了东厢房,里头的布置同西厢房基本相似,只墙上多出十来幅画,涵盖人物花鸟山水,水墨工笔写意等各种笔法俱全,左下的落款和用印确是隶书体的“关长暮”三字。
如果那天,他像多年前的陆归鸿那样进了这个房间看到这些画,那么,结果是不是会不一样?
可是,没有如果……
他的手指抚过画轴,落到窗前的书桌上将将顿住。青瓷笔筒里没有一支笔,取而代之的是满满一把烟花棒,还有一枝落在桌角堆放的大叠影集上。他拿起一看,见棒头发黑,心头一动,放下时手不小心掠过半尺宽的笔挂,指尖触到的冰凉几乎让他的心漏跳了一拍。
他迅疾走了出去,以最快的速度搜遍了整个院子。确认无果后的失望排山倒海压过来,不堪重负的心在“吱呀”一声后又忍不住狂跳……
“漱瑜小姐?”有人转过垂花门,顿时同耿清泽一样呆立当场,“耿先生?!”
“是我,胡爷爷。”
老人家四下张望,“漱瑜小姐呢?没跟你一起回来?”
他摇头,“这些日子,您有没有见过她?”
胡爷爷奇道:“她不是在S城?回来做什么?”
“我找不到她。”
看他一下子泄了气,胡爷爷便笑问:“小俩口闹别扭了?”
她不会同他闹别扭,无论事小事大,他们连架都没有吵过。
见他垂头不语,胡爷爷了然地叹气:“唉!漱瑜小姐什么都好,就是性子太拧。远的不说,就像去年她请楚先生修琴。你说这老头子也真是,一把年纪的人了,跟一个姑娘家较什么真呢!平时这么疼她,跟自个儿亲孙女似的,这会儿非要她先认错,她不认,就罚她在院子里跪着。漱瑜小姐跪在那儿,一句话也不说,任大家伙横劝竖劝,就是不肯服这个软,整整跪了一天一夜,膝盖都青了……哟……”头顶落下的水珠止住了他的絮叨,“下雨了……”
耿清泽拉他避到廊下,他灵机一动,“这样吧,回头让我那外甥女阿蓉替你劝劝她,找个机会你再好好跟她说说。漱瑜小姐再通情达理不过,说清楚了就没事了。”
耿清泽不忍拂他好意,只得点头。同时婉拒了他留他吃饭的邀请,只说自己还有事要办。
胡爷爷告辞后,他锁上大门,将钥匙放回原位,沿着记忆中的路线离开。
敲过门后好一阵,里头才有人出来。
门一开,耿清泽便问:“她是不是在这里?”
打着伞的楚先生慢慢摇了摇头,见他浑身湿透,只说:“先进来吧。”
一桌简单的家常菜,却没有一丝一毫属于易漱瑜的味道。耿清泽食不知味地吃完,胃里并未觉得好受多少,待楚先生温了酒出来,他也不客套,执了壶自斟一杯,端到唇边一饮而尽。
“哎哎哎!”楚先生赶紧移开酒壶,“上好的女儿红,统共就剩了这一坛,我还有几年活头,打算留着它慢慢喝,可经不起你这么糟蹋。”
他充耳不闻,执壶将两只瓷盅斟满。这一次,楚先生没有拦他,反倒闲闲在他对面坐下,颇有兴致地问:“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他定睛看着杯中的酒面,“老宅里的毛笔有人用过,我来碰碰运气。不然她还能去什么地方。”
“说得也是。换了我,我也不知道这丫头要上哪儿。”楚先生眯起眼,拈起一颗青豆,“自打阿暮走后,上级单位收回他们原先住的地方,漱瑜就没家了。从那时起,访筝为了供养她,开始变卖家产,又从这里搬回S城照顾她……”
“是GS对不起她。”耿清泽不忍再听,目光黯淡,声音幽沉,“我知道她过不了自己那关,也知道自己让她很失望。但我是GS的人,GS是我家三代的心血,我可以给她一切,就是不能像她要求的那样,她到底明不明白。”
“那你还来找她做什么?”楚先生像是听了什么极不入耳的话,将脸一板,即刻恢复了乖张本色,“就当她是死了,岂不一了百了?”
死?
楚先生呷了酒,又嚼了一颗豆,目光扫过懵懵然的耿清泽,眯着眼,笑道:“死算什么?人生短短数十载,长也不过百年,终有一死。有人死了,是因为对尘世无可眷恋;有人吊着一口气,也不过是无法了却一份牵挂。
“傻孩子,都是傻孩子……”不知是否酒意渐重,他越笑越厉害,好像真有什么再可笑不过的事,笑声宏扬,别说是坐在屋里,怕是站在院里都能听得清楚,“你以为你给的一切就是对漱瑜的偿还么?你以为只要你一如既往地爱她,就可以在紧要关头头一个牺牲掉她么?漱瑜就更傻……访筝拖到今天,难道只是为了要替阿暮讨一个清白?她断了同你的关联,就是守住了自己不违背关家的立场么?”
他眼里的湿意已悄悄蔓至眼角的皱纹,“我活了整整一辈子才算明白,一味执着于无可企及的目标,早已丢了生存的乐趣,这样活着,同死了有什么两样,倒还不如死了干脆。”
“蝼蚁尚且贪生。”握着酒盅,耿清泽沉声道,“但凡还有一口气,这事就完不了。”
“那你可有得受了。”楚先生无不同情地瞥过他一眼,“我给你说个故事吧——”
他顾自斟了酒,“大概是三四年前了,关家有一对青玉碗打算出手。买家久居海外,自称慕名而来,见漱瑜是个姑娘家,瞧着不声不响的,又急等着钱用,便把价往死里压,低到中人都说不上一句话;漱瑜呢,也咬死了,一个子儿不肯让,就这么僵持了有个把月。后来有天,老胡家的跟我说,这丫头看着那一对劳什子坐了一夜。果然第二天,她问那人,是不是真想要,人家听她松口,象征性地加了一点。这一回,漱瑜没有再还价,而是当着人的面拿起一只碗,看了看,‘啪’地摔在地下——”
耿清泽的心倏然一紧,楚先生却轻描淡写地续道:“——她不再说一个字。最后,人家只好留下她要的钱,带着另一只碗走了。”他垂眸微笑,“现在你明白了吧——就漱瑜这个脾气,你想她妥协,恐怕比要她死还难。”
“没那么容易。”眼底通红的耿清泽霍然起身,眉目间全是清冷的坚决,“就算她死,我也不会放过她。”
话落,他抬腿便走,却被行动矫捷的楚先生拦在门前,好像耿清泽是今晚突如其来的一个大麻烦。他不耐地摇着头,口气里似厌烦似懊恼,“发发牢骚罢了,你还当真了。上了年纪的人不经吓,我可看不得你们谁有个好歹。”
耿清泽点过头,正准备告辞,楚先生又没头没脑地扔下一句“你等着”,在书案旁找出一个塑料画筒交给他,“看在你陪我喝酒聊天的份上,这幅字送你,也不枉你我相识一场。”
却之不恭,耿清泽接过,想楚先生是个再随性不过的人,也就不作客套。不过,眼下他没有半分心情,自然也没有打算拆看的意思。
许是因着他的不赏脸而不悦,楚先生顿时沉了脸,“哼”了一声,颇有些不情不愿地说:“天不早了,我就不留你了。”
似乎也的确没有留下的必要。耿清泽知他个性乖僻,听他逐客也不多问,告辞后即刻抬腿跨出门。不过一眨眼的工夫,挺直背影已隐于茫茫雨帘,既而消失不见。
楚先生叹了口气,转手推开里屋的门,“我拿你的字给了他,你们倒好,一个不拦,一个不看。”他顿了顿,终究还是没有忍住,“我和他说的话,你都听见没有?”
“我到这儿不是来听这些的。”借着一室的幽暗,易漱瑜不动声色地拭掉眼泪,“奶奶快不行了,您收拾收拾,跟我去一趟吧。”
第55章 参商(3)
毕竟年事已高,又成天对着一个神智几乎完全错乱的病人,不过两个月的时间,心有余力不足的楚先生还是倒下了。易漱瑜无暇旁顾,不得不请蓉姨的先生送他回家。却在事后替他有些庆幸,真要让他亲眼见到祖母愈加不堪的病况,怕是更雪上加霜,之后的种种,让她一个人来面对就够了。
楚先生走后没多久,易访筝的病情又起了新的变化。突发的肺部感染导致各类器官器质性病变,别说是进食流质,就连插管喂饲都越来越困难,原本就瘦弱的躯体如今只剩了一把骨头。
钝刀割肉,生不如死。
收到三张病危通知的易漱瑜早已心如死灰,不再抱有任何指望,唯有坚韧如丝的神经还下意识地在脑海中紧紧绷住,一到晚上便不由自主地难以入睡,唯恐祖母在寂静黑暗里悄然没了声息。
其实,就算是白天她也睡不着,睁着一双乌沉沉的眼睛,一坐便是一整天。蓉姨看在眼里,急在心头,最后急到已顾不上忌讳,“眼看身子一天重似一天,还不晓得照顾好自己,万一老太太真的……里里外外那么多事还等着你拿主意。漱瑜小姐,你的命不是自己的,也要多为旁的人想想……”
蓉姨的话无不道理。可自私的她仿佛已将往昔的种种尽数忘却,自然也想不起来,自己究竟是为了什么撑到现在。
过去是历史,将来是未知,唯有现在才是上天的赐予。
那些前尘往事,容不得她再思再忆;真相大白,十多年来的惟一目标突然不复存在,她也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将何以维系;而当下,除了指望奇迹的发生,她还能做什么?
又是一整夜的目不交睫。纵是阖上眼,心也是醒着的。如同过去的几十个夜晚那样,易漱瑜枕着手臂趴在床边,守着床上的残破病体,守着一室的孤寂清冷,守着心底的一潭死水,只等着第一缕晨光照进窗口。
只身之外,只有那台冰冷的监护仪,在病房里幽幽闪着荧光。
忽然发顶一暖,有什么东西轻轻落在头上。易漱瑜微微一震,待在原地一动不敢动。呼吸滞了一滞,心口一点一点开始发凉。思维空白了片刻,她突兀地笑了笑,轻声道:“您是有话要对我说吗?”
易访筝的手无力地搁在她的头顶,指尖似有一颤。
“我知道,您要讲的我都知道。”她抚上那只手,“您舍不得把我留在这里,不放心我一个人,是不是?您一定是忘了,我现在不是一个人,再过几天,它就会来陪我……
“其实,我早就不想孤孤单单的了。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没有想过要去追究那件事,甚至一点也想不到为什么会来到他身边,好像之前的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他不知道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