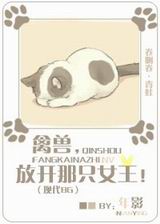小狼,放肆-第10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司马南没有那么多精力和她讲事实摆道理,他觉得自己是安琴在这样的一个圈子里的代言人,为她主持公道、维护利益的亲人。跑这一趟,让方骏说个明白是义不容辞的事。他不想告诉安琴此行的目的,怕的是这个死脑筋的女人再次犯傻劲。
此行,司马南专门带了个公安的朋友,其实也就是个穿警服的干事,平时爱在报社投稿,经常求着司马南,司马南只想借他的那身警服压压阵脚,毕竟钱是安琴自愿给人家的,拿出手的东西再拿回来,就是面对再老实的人也说不清会是什么结果。
车开在半路上安琴说记不清路了,那个公安就主动跑下车去问路。因为要见方骏,安琴坐在后坐满脸的局促不安,司马南回头看看她说:“害怕了是不是,我说你平时不要喝酒,酒这个东西能让人干逑傻事。”
安琴不明白他的意思,不服气地说:“什么事不傻?从我第一天跟着你冒充记者起就是傻。我本来就不是在这个圈子里混的料。”
司马南干脆回过身来,盯着她说:“你不识好人心啊,我还不是想帮你走出你那个圈子。南窑真的住着那么有味?你都不怕人家怎么看你。”
“大不了看我是坏女人。南窑的那些女人也不见得就坏到哪里去,倒是你们一天到晚地使坏主意,我看也好不到哪里去。”
司马南看那个公安问了路往车上走来,赶紧说:“等会儿不准当着我的朋友面乱说话。你也不看你都说些什么,要注意层次,懂不懂?很多不是那个层次的女人都希望人家看重自己,你看你咋就这么作践自己。”
那个公安过来说:“还远得很,顺这条路先到望玉镇上。”他拉开车门进来,点支烟递到司马南嘴上,骂骂咧咧地说:“狗地方真穷,穷得人都傻不啦叽的,刚才我问那个卖广柑的多少钱一斤,他光看着我笑,说‘你说多少就算多少’。真要想烧他,我就‘说一分钱一斤’,看他卖不卖。”
安琴不屑地说:“不卖又怎么样?”
公安说:“谅他不敢调戏老子。”
司马南说:“那你咋不一分钱把它全打发了。”
“咱们心软啊,看他傻不兮兮的样子,一定是被欺负惯了,占他的便宜不酸掉我的牙呀。”
安琴想这个人还算有点良心,但骨子里那种能左右人的优越感还是在言谈中一点点地渗透出来,心里想这世上凭什么就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司马南算哪一等?方骏是哪一等?这个斜叼烟的小伙子穿这么一身制服又是哪一等?待会儿见了周老师又把他算哪一等……
脑子里翻来覆去地瞎想,并不理会他们两个男人的谈话,倒是那个公安突然好奇地问安琴:“安老师,你咋就心血来潮,想起给他们学校捐款了?”
司马南马上把话接过去说:“她是喝高了,自己干了什么事都不知道。”
公安就说:“那么,那个拿钱的家伙该算是欺诈,因为你当时神志不清吧?”
安琴赶紧否认说:“不是,不是,周老师是个实诚人,再说他给我带那么一篮子的东西,礼轻情义重。”
那个公安理解地说:“你们女人就是软心肠,那一篮子东西,要按我刚才的办法,买下来不过几块钱,你的价钱给高了。安老师不知道,哪里能轻易地扶贫?光是人家考虑你的动机就让你说不清楚。”
安琴没吭声,心里想,要考虑自己的动机,真是让人说不清楚。
司马南怕小公安不小心把此行的目的透给安琴了,就打断他的话说:“去你的,今天咋搞起逻辑推理来了?”
安琴望着窗外不出声,心想这个公安不知道这钱的来龙去脉。知道了又怎么样,一个有着冷漠和无情心态的人也不能理解。
司马南说:“我还一直怀疑这钱让那个姓周的独吞了没有,要是他想自己瞒起来就好了,我还真希望他贪心,那才有意思。”
安琴不明白司马南这句话的含意,接着他的话说:“有什么意思?你不就是想让我后悔嘛,但我相信他不会独吞的,一分都不会吞。”
司马南边开车边酸溜溜地说:“好啊,终于听你说相信一个男人了,不过幸好这个男人是个窝囊废,要不我真的要吃醋了。”
安琴生气地说:“我也是个窝囊废!不是窝囊废,这几万块钱就不算钱,用得着你们两个费心在这儿评头论足吗!”
那个公安见气氛不对赶紧打圆场说:“叶编对安老师可是没得说的,他自己的钱被人骗了也不会起那么大的火,不是见不得有人欺负安老师吗?”
安琴倔强地说:“是呀,我总是受人欺负,有什么办法,有的事就是千金难买我愿意。”
司马南说:“好、好、好,算我多嘴。我这个人一辈子都干逑些热脸贴冷屁股的事。”
安琴只把眼望着窗外不作声,当车驶进小镇的时候,远远望,着了路边挂着“内可停拖拉机”的破木板门的小旅店,她就知道到了贾大富的地盘。
小镇上抱娃娃的女人、卖挂面的摊主、豆花饭店的老板一双双直瞪瞪的眼睛让司马南骂了一声:“狗日方骏是这地方的人,难怪脑子不够用。”
乡政府那个叫四娃的小伙子嘴里叼了根牙签,站在一家药店门口正在给人吹牛,看有小车过来,警觉地扭头打量车内坐的是谁。
安琴指着他说:“这是乡政府的,我记不得路的,要不要去请他带路?”
那个公安蛮有把握地说:“看我去叫他上来。”
果然那小伙子高兴地跟着公安过来,弯腰趴在窗子上看到安琴,一下子又记不起她姓什么了,机灵地说:“记者首长,你们是来参加挂匾的吧?我们乡长都去了,我给你们带路,边说他就边跑了。”
司马南看到他的背影说:“这里的人果然是有病啊!带路还跑什么跑。”
安琴猜想他是去找送人的摩托去了,就解释说:“前面的路车走不了的,人家是给我们找摩托去了。”果然一会儿就来了四个农民骑着摩托过来,有两架上面还带着绑猪的绳子。那个公安一身发抖地直笑,安琴和司马南却皱起了眉头。司马南是为坐这样的车掉价,安琴却想起了当初和方骏回乡下的情景,心里搅动得难受。
四娃得意洋洋地带着这个摩托车队上路,安琴在摩托车上问带她的那个小伙子:“今天给谁挂匾呢?”
小伙子大声地说:“方家,他们龙娃干大好事了,乡上和学校今天给他们挂匾呢。”安琴心里想这种场合来见方骏,方骏会不会感到自己来邀功请赏了!心里面有些不自在了。
四娃带他们三个人赶到月亮村时,远远地就听到了鞭炮的噼哩啪啦声,挂匾仪式已经接近尾声,司马南看到一个黑木漆金的匾扎着红绸缎已经上了方家四合院里堂屋的门框上。
四娃兴高采烈地像是立了大功一样,三步并作两步地穿过在地上哄抢没炸响的鞭炮头的娃娃们,大声报告:“乡长别散了人,别散了人!记者来了,A市的记者来了!”
贾大富机灵得像是和安琴他们是老早的熟人一样,拨开人群,一丈远的地方就伸出了双手,嘴里哎呀呀地叫着。正准备散的人不用村领导招呼自动地围拢过来。
贾大富说:“狗日的龙娃,名堂多呢!我说他不可能不回来,领导都请来了,又整我们冤枉!狗日的龙娃名堂多呢!”
安琴一听知道方骏不在家,知道司马南又骗自己了,但心里边的期待顿时又被一种轻松替代。
司马南在安琴给他介绍过后,立刻*到另一个角色中来,他两手交叉在*前面,傲慢地冲贾大富点点头,冷着脸幽幽地问:“方骏人呢,这么大的事,不出来露个面?”
人群里周老师跑了出来,一来就冲着安琴过去,拉着安琴的手说:“安老师来了好啊,安老师来了我就好给龙娃有个交代了!”他的脸因为激动涨得通红,这边拉着安琴的手使劲地摇,那边冲着人群里的女老师喊:“岳倩,把同学们都叫过来,过来给领导再唱唱歌。”
显然这些孩子们刚才都表演过了,那个叫岳倩的女老师脸上没有了上次的冷漠,三下五下地吆喝过一群涂了红脸蛋的孩子。孩子们扭呢地你推我、我推你,好容易站成了两排。
公安在后面悄悄地拉拉安琴的衣袖说:“安老师,下不了台了?”
司马南一挥手,不耐烦地说:“不唱了,不唱了,事情还没有弄清楚,唱个什么呀?”
他这一说,全场都鸦雀无声了,只有站在人群前面的二十多个娃娃,挤挤挨挨的,还在找位置,期待着岳倩老师的举手指挥。
这一鸦雀无声让司马南立马感觉到自己太沉不住气了,他缓和了下情绪,客气地对围着他的乡干部说:“大家坐嘛,大家坐嘛,我们来晚了,来晚了,本来听听孩子们唱歌也不错啊!不过有些事情不是大家期望的,需要澄清澄清。”
他的话更带来一片沉静,包括那些孩子,看到大人和老师眼里的神情发生了突然的变化,也不叽叽喳喳了。
贾大富把疑惑的目光向周老师投去,周老师又把这目光向安琴投来,安琴则把这目光投向了司马南。只有那个小公安知道这里将发生什么,幸灾乐祸地点着一支烟,仰头向天空吐着烟圈。
周老师几步上前,一把抓着安琴的手,着急地问:“安老师,怎么了,这里边有又什么事了?”
司马南推开他的手,笑着说:“你应该知道是什么事呀。”
还是贾大富机灵,殷勤的笑容一下子堆上脸来,哈哈笑着说:“走走走,咱们先上家里说去。”
他一挥手,那个四娃就懂事的,在前面引着司马南他们三个进了方家的院子。
几个人在方家院子里坐下,司马南、安琴等三人自然是上宾,一桌上有胡乡长和村长几个作陪。安琴执意要和周老师、方骏的妈妈他们坐一桌,大家扭不过,她这才有机会坐在了瞎老太太身边。
方骏的嫂子大嗓门大喉咙地说:“妈哎,你摸摸这是谁个,安妹子,你说有福相的安妹子!人家现在是龙娃当家的了,龙娃的大事都托她办的,你摸摸呀。”
瞎眼妈妈笑眯眯的,真就伸手摸索安琴的脸来了。院子外边抱着孩子、纳着鞋底看热闹的女人们,眼睛都齐唰唰地看到安琴身上,看得她一脸发烧。
扭头看看司马南,他正保持着一种高傲的神态,仿佛又走上一个舞台,上演了威严的角色。想到欺下者必媚上,谅他在比他更高的人面前一定是一百八十度的另一种态度。
左右不见方骏的影子,明知他肯定不在,但还是忍不住附在瞎老太太的耳边轻声地问:“方妈妈,方骏他现在在哪里?”
可惜老太太没有听清楚这句问话,回答她说:“我知道,我知道方骏他忙,你回来也一样,你回来也一样。”安琴看看周围的人,再不敢问什么,她怕大家听出什么破绽来。
戏的*是司马南掀起的。他皱着眉头对贾大富说:“乡长呀,这次我们来是想见方骏,但方骏不在,可能有些事情就只好给领导讲了。”
贾大富讨好地说:“你讲、你讲,我们洗耳恭听着。”
司马南问:“那笔钱,你们动没有?”
周老师赶着说:“在会计那儿,已经上了账了,当着村委会的所有人上的账。”
“这不是方骏的钱,那存折单单上不是写得清清楚楚的嘛。”
司马南讲这个话的时候,目光直逼周老师,周老师被突如其来的事件一下子打懵了,张着死鱼一样的嘴巴,一会儿看看司马南,一会儿看看安琴,整个不说话。贾大富却一下子表现了安琴从来没看到过的严肃和认真。他把手里的烟头掐灭,牙齿咬得紧紧地对周老师说:“胡逑整……”
司马南接着说:“这是个误会,这钱是人家安记者的,一个女同志几十年辛辛苦苦的积蓄。当然这事得等方骏回来才可以说清楚。你们说方骏人呢?这么个让他风光了的事,咋不出来?”
这时人群发生了不小的骚动。特别是门外那一群女人,听也不一定听清了什么,反正觉得事情有了变故,立马像麦田里被惊起的麻雀轰地一声炸了窝。
方骏的大嫂愣了愣后,立刻表现出对一个家庭最大的忠诚,她一下子跳起来,手指着和她对面坐的周老师,嘶声裂气地大骂:“狗日的周酸酸,你日弄人咋的。你给老娘说清楚,这可是你拿回来的钱啊,事情是你红口白牙编排的,你成心想打我们龙娃的脸是不?”
岳倩拢着左右身边两个孩子的肩膀,啥也不说,脸上又回复了安琴第一次见的那冷色调。
和大嫂坐一张条凳的方妈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