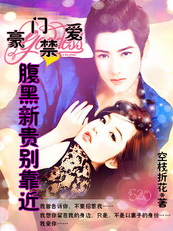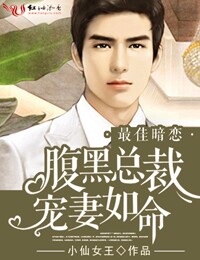腹黑女尊之妖冶宫主-第5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待人都散后歌儿捂着腹部缓缓下床。或许是晨宇极的药效果奇佳,刺得那么深都没有死。现在也只是有些隐隐地痛而已。昏迷了这么久,不是伤的深,是做了一个太尝的梦。一梦两三年。
她的这个梦却整整是她这二十年的人生。
伫立在屏风面前,想起了最初在这个屋子里醒来时的样子。她惊为天人,谁知却是她自己。当时只觉得屏风上的女子感觉有点怪,现在明白了,是那身白衣!胭脂红倾撒,白衣便成了
红色,像血。歌儿冷笑。提笔泼墨。“十步杀一人,千里不流行”惊心动魄的十个字,苍劲有力,充满戾气和血腥味。
歌儿轻轻地吹着已经浸透锦帛的墨汁,嘴角冷笑。
抬眼便对上一双同样冰冷没有感情的眸子。一身红衣,长发拖地,美得摄人心魄,和她一样的脸。心里微惊。
“奴婢乐菲蓉参见皇后娘娘。”
女子下跪,声音透彻。
“乐菲蓉?主人?”
“晨宇极”
“何事?”
“替代皇后娘娘。”
替代?她为什么要答应?歌儿静默不语等待女子的解释。
“想必娘娘已经想起一些事情,如果想彻底明白就要离开谎言。”
离开谎言?很聪明的女子!她确实被谎言包庇着。若想知道为什么在这里就必须先离开这里。
“好。什么时候?”赞赏。
“现在。主子在外面等着您。”
“我身上的伤?”
女子当着歌儿的面tuo掉衣服,在她的xiong口有一块丑陋的伤疤,不仔细看像是新伤。歌儿的眼神微微地变了变。
“皇后娘娘可以放心了。这伤疤是主子贴上去的,撕不下来,会随着时间变淡。”
想得很周到。不知道这个晨宇极葫芦里卖得是什么药。
“您只要从后门出去就有人接您。”
歌儿深深地看了女子一眼转身离开。
给读者的话:
本书要完结了啊……大家多给意见。以后还希望亲们看到纳兰的书多多支持!
安顿
安顿
在歌儿醒后的第一天晚上便被调包离开了生活了两年的君国皇宫。马车上,铺着至少十几层的被褥,厚厚软软以减少马车在土路上颠簸的撞击不让伤口挣裂。
连夜赶路,她有伤在身又不能走得太快。所以现在才走出京城来到郊区。路边的风景很熟悉,是那夜晨宇极把她从冷宫里带出来时走的路。果然须臾,他们便来到了那个废弃的宅子。
不同于上次的荒芜,这里明显有人打点过了。虽然外面看起来仍是荒凉破旧,但里面已经被收拾干净。
“上次来看你不讨厌这里,而且这又荒废了这么久对于你静养身子很有好处。”
歌儿被晨宇极搀扶着静静地听他讲话。
这里?呵呵……是命运的捉弄吗?她兜兜转转了两年还是又回到了这里。歌儿的神情有些恍惚。眼角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抑郁。
“你现在不要回宫吗?”
难道就不怕君玦发现晨国的国君莫名的消失了?晨宇极抿唇微笑不语。
许久。
“既然你可以出来,我当然也可以出来。”
这意思是宫里已经有了一个“晨宇极”?果然是聪明的人,只是他以为别人都是傻子吗?君玦早就在他身边安插了眼线,岂能这样轻易就让他蒙骗?
“当然,他在我身边安排的人一直在盯着。所以我不能经常在外面。现在宫里的你还在伤着,皇上没心思过问其他的。所以……”
晨宇极冲着歌儿淡漠一笑,有些无奈,有些……苍白……
歌儿有一瞬间的迷惑,目光定住在他的一身白衣上。
“外面风有些冷,进屋吧。”
晨宇极从那双清冷的眸子里挣扎出来,别开眼走进屋子。
“我去侧房睡。你,自便。”
歌儿并未跟着晨宇极向正屋去而是走进了那间带有密室的屋子。就是上次晨宇极打昏她的那间。她还有很多事情想不明白。需要一个人先静一静。
已经不见了厚厚的尘埃,让歌儿产生幻觉,仿佛时间还在两年前,在这个屋子里,那个一身白衣眉眼温润的男子小心翼翼地端来热水为她洗澡。弥漫的雾气,缠mian缱绻的白纱帐。被她摔碎的
玉佩……是屋子太阴湿浸透了她的眼睛吗?怎么觉得眼前这么模糊?这种感觉太陌生,当年她是独孤玄夜,是歌儿,却也一直是他的叶儿。可如今的自己,一身高贵的光晕渐渐让她变得朦胧不真切。
无名崖上的厮杀她失去了这辈子最爱她的人和……她最爱的人……
如果一直这样不记得空白着,她有的只是苍茫不安,现在却是悔恨,空荡荡还有恨。
今夕何夕君已陌路。
这个暗室里,她曾逼疯了自己的妹妹。那个怀了他孩子的女人。死有余辜!到现在歌儿的眼里还可以看见那种彻骨的恨。在漆黑的夜里如此刺目。
扶着冰冷的墙壁一路蹒跚地走回床边,被褥是刚换的,枕头是新的。晨宇极到底是何人?为何要劫自己来这?难道是想以自己来要挟君玦?他是晨国的国主,她这样想合情合理。
罢了,累了。熄灭了床前唯一的一盏灯准备睡去。
“盈盈一水边;夜夜空自怜。
不辞jing卫苦;河流未可填。
寸情百重结;一心万处悬。
愿作双青鸟;共舒明镜前。”
月光照在她的脸上形成美妙的光环,整个皮肤显出一层薄薄的雾气让人看不真切,妖娆的长发散在两边揪人心神。浓密的睫毛弯成好看的弧度,秀美微拧,神色有些焦虑。
这个女子从他第一次见到她便时时地为她揪着一颗心,她喜,他笑,她怒,他悲。如此牵动人心的女子让他怎能不动心?尽管……点了她的睡穴,晨宇极和衣拥着她。掩饰不了心里的
颤抖,没想到有生之年还能抱着她入睡。
清晨。窗外麻雀聒噪,她一向浅眠,昨夜竟然一夜未醒,酣然入睡。此时天已大亮,阳光斜射进窗内。身上的伤还有些痛,动作迟钝地穿好衣服走下床。晨宇极已经在外面等着了。
“饭好了。现在要吃吗?”
一碗白米粥,一碟青菜,一个馒头。
“你现在还不能吃硬的东西,多喝些米粥。”
冒着热气的粥,歌儿不想在记起过去。可是还是忍不住想起了暗抚宫,清晨他为她煮的粥。
“是你煮的?”
“是”
沉默,吃饭。
“我带你在院子里走走吧。”
歌儿并不反抗任由晨宇极拉着。很温暖的手,皮肤细腻不粗糙,有力却很温柔。
“为什么带我出来?”
“……”
“你想威胁君玦?”
晨宇极停下来,仔细地盯着歌儿。脸上看不出表情。
“如果是,你会怎样?”
歌儿语结。她会怎样?她会怎样?认真地想了许久。
“我会反对。”
晨宇极定定地看着她仿佛要看进灵魂里,然后没有表情地转身拉着她的手继续走。
给读者的话:
米人留言么……么么~~郁闷……快结束了,舍不得大家啊。记得以后多支持纳兰……
相处
相处
晨宇极的态度让歌儿很不解。这是个怎样的人?沉默,内敛,那双温润的眼里似有千万年的沧桑和在压抑下却还是露出一点点的感情。在这样一双眼睛的注视下
歌儿无法稳住自己的心神。
“你……和他成亲多久了?”
“两年。”
“孩子?”
“不是我的。”
是那个疯子的。怪不得总觉得倾儿与自己有太多不像。她最疼爱的孩子,那个乖巧可爱的稚子竟然是别人的。维持了两年的亲情却敌不过事实。
“你既然带我出来,就该知道我曾是谁,我的过去。还有……我不知道的事情。”
晨宇极淡淡地看了歌儿一眼,没有说话。只是把她带进后院,前面是那个被抬出来的破碎的玉床。
“这床……是你的?”
“嗯”
她曾在这上面跳过舞,抚过琴。还有一个叫魅姬的女子。
“你的事情你还记得多少?”
“都记得。除了……无名崖上昏倒之后。”
她不记得自己是怎么离开无名崖的,怎样躺在了皇宫里的。又为什么一身武功尽失。这是她最想知道的。
都记得?晨宇极微微错愕。牵着她的手走过玉床。来到一座小亭子。纷飞的白纱帐,清脆的铃声,像七重宝塔檐边挂着的风铃。召唤着飘向远方的人。
有风过,思绪凝结。伫立停滞。两个人都不语,晨宇极的一身白衣与满眼翠绿相衬,与轻纱相融。
“我曾遇到过一个同样喜欢穿白衣的男子。那是……一个,像莲花一样的男子。”只是被她逼地沾满血腥。
闭上眼能看到那个坠入悬崖的红色喜袍的身影。
“是吗?然后呢?”
晨宇极的声音平淡,或许他并不想知道只是出于礼貌才有此一问。歌儿无谓,无名崖上痛彻心扉的感觉还在,现在只想找个人倾诉。
“后来……后来,他成亲了。被我杀了。”
声音随即没落,沉寂、琉璃色的眼睛蒙上了一层凄切,让人揪心。晨宇极搂过她单薄的身子,心里唏嘘。什么时候她已经这么瘦了?眼底一片荒凉……
不染纤尘的白色衣领,又阳光的味道,还有一丝和雾辰身上很相近的清新味。歌儿苦笑,人都已经死了两年了还在这幻想什么呢?
晨宇极带着歌儿拾级而上,徐徐缓缓,小心翼翼。亭子中央的桌子上摆着一张琴两杯冒着热气的茶。从昨夜到今天都不曾见到有什么人,难道这院子里还有隐形的人?
没解释她的疑惑,有些事……现在还不是时候。随即撩开衣袍落座。歌儿坐在他的对面。
苍白手指,七弦琴,焚香,沏茶。亭中的男子优雅淡定,眸眼却深似千年潭。
“知道我以前做什么的么?”
她明白他知,他于她是陌生的,他却熟悉她的一切。问他只是想让自己能在过往里活得更久些。
“我曾是京城最大的qing楼‘怜忧阁’里的歌儿,琴,舞,曲自不必说。只是不知为何这两年我从未碰过琴,也更为弹过一首曲子。”只有那次在君玦的两个妃子面前跳过舞。
“……”
晨宇极不语,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把琴向歌儿边上推了推。
“在下愿闻。”
抬起水眸略瞥一眼苍白温和的男子,歌儿叹息一声。有些颤地伸出手,两年了,不知道手指是否还灵活?
调试一下音调,缓和了心情,想起了旧日曾唱过的曲子。
“点青莲,花漫目无边
翼徊天,寥寥是无眠
他笑朱砂落眉间
他恼碧落入黄泉
蝶翩翩,遗剑恸离别
情未揭,玉箫曲当年
扁舟叶,翎羽散灰湮
凤凰去,烟雨秋天自难忘,自思量,独自伤,闲时谈如断肠
醇酒香,品芬芳,燕子归,剪不断愁绪吹
又看eng月笑华月
碧音归,弹指几春回
雪天泪,霜镜美人醉
海棠蕊,微兰暮迟睡
双花容,映天下心碎
予为水,新月映潋滟
重莲翩,泪断沉梦魇
竹林涧,寒山拾残叶
菡萏淡,凰过尘烟”
在丞相府上,这是她的最后一曲。‘弹指几回春“?几回?几回……
酒宴上的那个一身红衣的女子浑身霸气凛冽,像开在刀尖上的妖娆,媚人也伤人……如今风撩起她拖在地上的长发,红色的衣摆像燃烧的火焰灼伤了人眼。晨宇极几次yu言又止却又
硬生生地别过头。
曲罢,落寞。琴歇,人老……从十岁那年到十八岁,她身边一直有爱的人相陪,不管雾辰也好,曾经背叛过她的云桑也罢都已经是过眼云烟,烟消云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