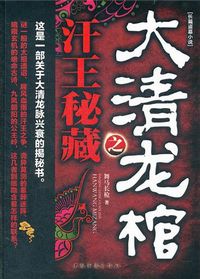大清宰相厚黑日常-第10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张廷玉道:“叫个信得过的丫鬟,连着李卫来照顾他,莫要出了事儿。”
从头到尾,顾怀袖都没插嘴。
他们在外间看着,里间罗玄闻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却是不知。
张廷玉牵了她的手,“现在还困吗?”
“困。”顾怀袖说的是实话。
“困,咱们就回去睡。”
说罢,张廷玉拉着她便回房了。
两个人宽衣躺在床上,顾怀袖用尖尖的手指戳他胸口:“你怎么想的?”
“你二爷我菩萨心肠。”张廷玉借了一句顾怀袖的话,她常常说她自己善良,心肠好,久而久之地,张廷玉也学贫了。
顾怀袖毫不犹豫啐他一口,揪了他一把:“净会说瞎话,即便你是头强龙,也压不过地头蛇啊,干什么跟沈恙对着干?”
别的不说还好,一说这话,张廷玉就有些似笑非笑了。
只是床帐里黑糊糊的一片,看不分明罢了。
顾怀袖敏锐地察觉到了几分危险,想躲已经来不及了,张廷玉一把捞住她,却将她放在了自己的身上,叫她分开腿跨坐着。
她只拴着肚兜,张廷玉的手却从肚兜下面伸进去揉弄。
“你干什么?快天亮了都不老实。”
张廷玉好整以暇,“我不高兴。”
“二爷你有病,有癫痫病!”
顾怀袖翻身想要下去,他手却往她腰眼子上一按,让她坐得更紧。
于是,原本便朦胧着的一层纱,便像是被捅破了一样。
顾怀袖一下觉察到他意思,手都软了一下。
“别……”
张廷玉捏着她,压着她螓首,亲吻她嘴唇,教她身子软成一滩烂泥了,才肯停歇片刻。
顾怀袖还不曾试过这等姿势,她羞耻心起,有些受不住,屡屡想要逃窜,却被他按得更紧。眼角发红了,嘴唇咬紧,偶尔一松,吐出来的全是咒骂。
她越是挣扎,二人便绞得越紧。
顾怀袖软得不行,就差告饶了,他腰上稍稍使力一顶,她便颤个不止,“别了……太深了……唔二爷饶我……”
饶?
张廷玉觉得好笑,扶着她光滑的背部,弄捏她胸前柔软,却压低声音道:“二少奶奶不矜持一些了么……”
顾怀袖一下惊醒,床帐里瞪他一眼,咬紧下唇死活不肯动。
她不动,下头自有人不老实,折腾得她死去活来,才算暂歇得一刻。
顾怀袖只恨自己不是条死鱼,那般至少不会被他撩拨起来,让他在这床笫之间大逞威风。
完事儿了,她手脚都是瘫软的,有个出气没进气,只哼哼着:“我要死了……”
张廷玉不正经道:“欲仙,欲死。”
“呸!流氓东西!”
她踹他一脚,却没能将人踹下床去,身上没力气,干脆闭眼睡去,“明早别叫我,谁叫我跟谁翻脸!”
作者有话要说:二更,脸都大了一圈=__________________=
☆、第九十章 出题
中秋灯会之后,整个江南的局势都稳了下来。
扬州最富乃是盐商,沈恙刚刚插足这一行当,就遭遇刺杀,当中因由更多由当日漕河之事起。在众人皆以为沈恙十死无生之时,这人却一下蹦了出来,惊落一地的眼珠子。
只是大的清洗也开始了,八月的整个下半月,仅以顾怀袖所见而言,真可谓是半城商铺都空了。
不是萧条,而是换了人。
沈恙无法容忍自己身边存在的不稳定,所以辣手从头到尾地梳理了一遍。
上至沈恙身边的主簿和会馆的掌事,下至各个店铺分号之中的账房和掌柜,里里外外全部理了一遍,等到事情结束,也便差不多是九月半了。
秋日里落叶已满江,天霜河白,又是九月初三钩月凉甚。
忙完了的沈恙跟一直不怎么忙的廖逢源终于碰了头,两个人坐到一起,听闻张廷玉夫妇九月底便打算回桐城,索性请了两人过来坐坐。
顾怀袖跟张廷玉,对那罗玄闻之事皆绝口不谈。
这一位背叛过沈恙,可谓是个有野心的人,就是本事上差了一点,眼力上差了一些。如今沈恙还在江宁,罗玄闻根本不出去,整日里只待在小院儿里,曾问张廷玉借过几本书看,倒也安生。
咬人的狗不叫唤,顾怀袖平白对罗玄闻的存在产生了一种奇异的预感。
他也不是没有过飞黄腾达的时候,曾在沈恙手下做事的罗玄闻,可谓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手底下每天过去的是成千上万白花花的银子;如今他没了一指,虽只是左手,可毕竟不再是个全人了,还一无所有,是报应也是代价。
张廷玉肯救罗玄闻的原因,其实很简单。
一则,罗玄闻多年跟随在沈恙的身边,对他的事情几乎是了如指掌,包括对沈恙整个人;二则,此人能在沈恙手下爬到二把手的位置,代他管着那么多的事情,并且处理得井井有条,可知此人颇有能耐;三则,此人沉不住气,正如顾怀袖此前之断言——不堪大用,他会在不合适的时机背叛沈恙,固然是沈恙技高一筹,可若是他自己够聪明便能沉住气,另谋时机。
这样一个很有本事,也算是聪明,可有一点点致命缺陷的人,最好掌握了。
张廷玉看中的便是这种有瑕疵的人,更容易拿捏。
蠢人太蠢不能办事,真聪明的人不会真心为你办事,只有这样有本事又不算顶顶聪明的人,用起来才放心。
所以张廷玉且养着罗玄闻,也不担心他是不是要跑。
张廷玉的身份,就是他的护身符,到底是张英儿子,一点也不担心。
顾怀袖曾讥讽他官二代,张廷玉也不喜欢旁人提到他的时候只说他是张英的儿子,可真正要到可以动用这身份的时候,他却毫不犹豫,从不会觉得有什么羞耻。
厚黑厚黑,精髓便在此处。
顾怀袖与张廷玉,皆算是精通此道之人,彼此心照不宣,所以基本对罗玄闻的存在只字不提。
沈恙那边一大堆的事情忙,似乎也终于没继续找罗玄闻了。
而今,那边发了请帖来,却是到了秋天赏花的时候了。
廖逢源作为巨贾,在江宁扬州等地都有几处园子。
沈恙这样的人就不必说了,听闻平日里熬粥用的是珍珠粉,泡茶的水来自虎跑泉,喝汤只喝第二碗,水晶蒸糕只吃皮儿……
你要问喝汤的第一碗哪儿去了?倒门口祭财神爷了;你要问那水晶蒸糕馅儿怎么办?沈爷吃剩的东西一律往江里倒,断不给人吃……
总之这一位沈爷每天吃穿用度都要花出去千儿八百的银子,好歹用的是他自己的钱,顾怀袖听了只当是个败家爷们儿罢了。
沈恙在江宁统共有三座园子,一座在郊外,依山靠水;一座在外城,半园子的花草,半园子的女人;一座在内城,这倒是清净,全仿着苏州园林的精致细巧走。
假山湖石,红枫□□,绿池青瓦,雕花窗,圆洞门……
顾怀袖与张廷玉一道走着,走到一半便道:“光是一个沈铁算盘便如此奢侈,我看皇宫里都未必有这精致气。”
张廷玉跟她摇了摇手指,“这话可说不得。”
可这偏偏是实话。
真论精致婉约,北方园林可没法儿与南方相比。
他们往前走了一路,过了回廊竟然看见一片小湖,一条长道延伸出去,最中心有一座两层的湖心亭,可那长道却没接到湖心亭上。
木板铺的栈道前面系着几只小船,船边摆着几根桨橹,两名小厮跟两名丫鬟请了张廷玉与顾怀袖上船,然后摇着船,这才到了湖心亭。
顾怀袖皱着眉,一副嫌弃表情,扶着张廷玉的手上了楼梯,这才瞧见两位正主儿。
今儿都是带着后园女眷来的,沈恙有几名妾室,都生得弱柳扶风,韵味儿十足;一旁的却是顾怀袖认识的廖逢源夫人刘氏。
她二人先相互厮认了,这才见沈恙那几名妾室。
顾怀袖一看便知,沈恙这几名妾室,都是瘦马出身。
扬州的瘦马分三等,一等瘦马学琴棋书画,歌舞诗词,舞文弄墨妆容点缀,无所不通,床上功夫也是一流;二等瘦马则略通文采,多学管账记账打算盘,可谓富商巨贾操持家务;三等瘦马厨艺女红,亦是相当出色。
这些人每每从贫苦人家挑选出来,姿容艳丽,养上几年,由弱柳扶风而成倾国倾城之态,便由牙婆和养瘦马的人货与商贾。以扬州盐商养瘦马之风最盛,因而谓之“扬州瘦马”。
传闻第一等的瘦马往往要上千两银子,便是千五也不为多。
如今站在顾怀袖面前的,可不就是一溜儿的瘦马?
人太多,顾怀袖也记不住名儿,只依稀记了个姓氏,知道给沈恙管内宅账本的一个姓陆,可若问她到底是哪个,又说不清了。
前面几位爷开始叙旧喝酒,湖上却过来两条画舫,下面站了个身段窈窕的姑娘,便在乐声之中起舞。
顾怀袖看得一皱眉,倒是刘氏仿佛习惯了,旁边那几名瘦马更是习以为常,根本见怪不怪。
沈恙只隔了一道屏帘,一手搭着酒壶,抬了小指指着下面那起舞的:“这是前儿有人送上来的瘦马,廖老板看看怎样?张二爷?”
廖逢源咂咂嘴,“下面人送给沈爷的,必定是最好的,哪里用得着老头子我来品评。倒是张二爷,往日不怎么来江南,怕还没见过吧?”
见是没见过,可听过的就多了。
张廷玉只笑道:“张某不懂。”
“料想你们二位也不懂这里头的意趣。”
沈恙摇了摇手指,却起了身,走到栏杆旁,将手中一壶酒的酒盖给拧紧了,里头有机关,一扭便不能出酒。他抬手便将这一壶酒扔下去,“听爷的话,跳支绝活儿,爷赏你酒喝。”
顾怀袖这边已然好奇,只问沈恙那几名小妾:“绝活儿?”
一身穿大红水袖衣裳的杏眼女子道:“张二少奶奶有所不知,那是前一阵下面人送上来的新人,似是姓苏,叫什么不清楚。下面人调o教过,能在活的算珠上头起舞,以双足拨动算珠衍算,厉害着呢。”
这算是什么怪癖?
顾怀袖是不能明白。
一旁又有个人拈酸道:“还不是看着沈爷对算数痴迷,所以投了这机?”
她这一说,杏眼女子便不说话了。
杏眼女子便是沈恙小妾陆氏,原是二等瘦马出来的,可因着能打一把好算盘,还颇通算学,很快得了沈恙的喜欢,一路到了今天这位置。她原是因着算数而起来,今天也有人能在算盘上起舞,大出风头,引沈爷喜欢,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沈恙园子里的女人太多,她们勾心斗角她们的,沈恙只作壁上观,一点也不阻拦。
现在,他只看着下头苏姓瘦马在特制的算盘上起舞,姿态柔弱不胜风,冰肌玉骨,随着乐声轻轻打节拍,沉醉其中。
“啪、啪、啪啪……”
这是玉足轻点着算珠,使其碰击出来的声音。
苏姓瘦马体态轻柔,颇有当年赵飞燕鼓上起舞的轻盈弱态……
然而,沈恙的眼底其实没有美人,只有那算盘的声音。
一上一,二上二,三下五去二,四下五去一,五去五进一,六上一去五进一,七上二去五进一,八……
啪。
沈恙瞬间皱眉,“错了!”
乐声戛然而止,那苏姓瘦马吓住了,站在下头画舫里抬眼看沈恙,却只见到这传说之中的沈铁算盘面无表情地看着她。
半晌,沈恙扫兴地转身回了席间,却道:“女人就是头发长见识短。”
连个算数都跳不好,也没意思了。
下头那瘦马已然不知如何是好,周围人没得指示,也不敢做什么。
可沈恙这话不该说,至少不该当着顾怀袖的面说出来。
她就在后头听着呢,这时候一下便火大起来。
沈恙也就是一个好色之徒,坐在这里她都嫌恶心,登徒子……
顾怀袖冷哼了一声,立时隔着长长的曲屏反唇相讥:“敢情你们男人头发不长,个个都是庙里贼和尚!”
“噗……”
这楼上不知多少人喷了出来,愕然至极。
张廷玉一按自己眉心,便知道今儿不能善了了,他还没来得及出声儿,也不敢出声儿。要是现在他开口说话,那就是帮了沈恙的腔,回头不定会被顾怀袖给削成什么模样呢。
他忍了,沈恙却憋了。
廖逢源愣愣不知错措,一边一直装糊涂的邬思道继续装糊涂。
张二少奶奶可跟火药桶一样,一点就着,谁敢找死地呛声儿啊?
唯有被顾怀袖顶了一句的沈恙,面子下不来台。
顾怀袖说错了吗?没说错啊。
顾怀袖说对了吗?怎么想都不对呀。
错也不是,对也不是。
沈恙郁结了,张乐半天嘴,只道:“张二少奶奶嘴皮子利索,沈某人说不过。”
呸!
顾怀袖将酒杯一扔,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却道:“既然诸位对算学这样感兴趣,不如我来出个题,给大家助助兴。”
她可憋着坏呢。
前面男人们也感兴趣了,这上头可有不少的丫鬟仆人,都竖着耳朵听。
顾怀袖道:“这里有一根时而粗时而细的不规则长绳,从头烧到尾要半个时辰。现在我手里呢,有许多条这样的绳子。那么,请问诸位,或者说请问沈老板,如何才能用烧绳子的法子,计五刻钟呢?”
这刁钻的题目一出完,顾怀袖便高兴了,她起身拍拍手,便招呼青黛:“青黛,走,同我下去划船游湖,这上头太闷了。”
前面的爷们都皱了眉,有些反应不过来。
如何才能用烧绳子的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