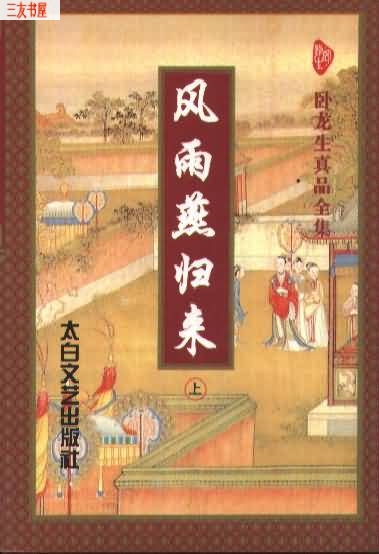风雨孤独-第4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古风一挥手喝道:“不要再说了。”
冷峻止住了,眼里流露的是讥嘲。
为个女人这样,至于吗?他想不通。
这时杜雨拍了拍冷峻的肩膀语重心长地说:“老弟,很多事不亲身经历是不能真正体会到那种刻苦铭心的痛的。别再往别人的伤口撒盐了。”
冷峻拈灭烟蒂,又端起茶杯,说:“或许是我的盐太多了,总想撒出去的缘故吧!正如刚才有人说的,火烧眉毛时,总该先考虑下眉毛吧。”
“有什么好考虑的,大不了豁出去了,兵来将挡。水来土淹,难道咱们师兄弟之人还会怕谁不成?”杜雨囔道。
“话不能这样说。问题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殷飞龙夺刃之后又不派上用场,他到底有什么鬼呢?”古风说:“另外,我总有种咱们被利用的感觉。似乎有个渔翁在盯着我们等着蚌鹤之争后得利。”
“何以见得?”杜雨问。
“杀手的直觉。”古风说。
杀手对危 3ǔωω。cōm险总是感觉灵敏的,尤其是长期处在危 3ǔωω。cōm险之中的杀手。古风不仅是一个一流的杀手,而且长期处在黑白两道的夹击下,形势更为严峻,感应当然也更为强烈。
“你们曾说过,你们在飞龙帮火拼的时,有高人相助?”冷峻突然问道。
杜雨说:“你怀疑他?我能保证他就是我们身边接近的人,而且是个好人,这勿须置疑。”
冷峻苦笑:“那我们岂不是毫无头绪?连殷飞龙的详细情况都不掌握不了,我们怎奈何得了他?”
“我长年刀口舔血,行踪极为隐秘,人送名号‘风影’,为什么一出去就被殷飞龙盯上呢?”古风又说:“没有人会隐身术,神秘仅是吹嘘而已。”
“你一直就在天马帮吗?”冷峻早就想明白一个问题。
“对,从踏进未名城的那天起。”古风说。
“那你的任何费用都由杜雨去付?”冷峻又问。
古风愣了片刻,不知他怎的又转到这个话题上了,但依然回答了他:“对杜雨来讲,那点钱仅是九牛一毛,但我不喜欢欠人账,我只花自己的钱。”
“那你的钱……”冷峻抬眼望着他说。
“从那些该死的死人手中拿的。”古风的眸子很冷酷。
冷峻笑了,让人看不出是什么成份的笑。因为愈复杂表面愈单纯。
古风继续说道:“我杀的都是可杀之人。他们手中的钱财,我只取十分之一。”
“意思就是说某人有一千万不义之财,你就提取一百万?”冷峻说。
这一举例,旁人即使数学再差劲,也看得出之间的悬殊。纯粹地拿一和十分之一比较,谁都会觉得十分之一微乎其微。算不了什么。但各自延长的时候,看似微小的就成了大。
古风当然听出了语中意味:“如果让你亲自装备,侦察、准备、行动,可能只有让你亲自去试试,才不会再说出这么弱智的话!”
杜雨也插话说:“是呀!计划杀一个防护严密的大贪巨奸,就必须去掌握他的日常活动,性情喜好。他进什么场合你就得进什么场合,有关他其它方方面面的情况都得掌握清楚。而这些都非得有充实的经济基础为物质保障。这个世界是无钱寸步难行。很简单,风哥说是独行侠,但真做起事来,没有耳目眼线怎么可能?”
冷峻眼光温和了些。为什么人们总把万能钥匙称为金钥匙?因为金是万能的。
既然解开了心中的疑团,也就没什么偏见了。
而古风仍冷冷地说:“我以为你真的见多识广,没想到越交往发现你越幼稚,真不知道你是怎么维持平日的那种莫名其妙的自信?!”
“谢谢你的抬举。”冷峻不屑道:“我从没认为自己很了不起,我只认为别人没什么了不起。”
“这有什么不同!”杜雨问。
“当然,前者是自谦,后者是自信。”冷峻说。
“应该说前者是自卑,后者是自大!”古风冷哼一声说。
“一词尚有多意,我不一棍子将你打死。”冷峻说。
杜雨只有劝道:“你俩咋喜欢掐呢?还是谈谈正事吧!”
冷峻问:“你说什么才是正事呢?”
杜雨不耐烦地说:“下一步该怎么走呀!”
“该怎么走就怎么走。”古风说:“天无绝人之路。”
杜雨哭丧着脸,无话可说。
冷峻张了张嘴唇,但又闭住了。
老天真的无绝人之路吗?为什么又有一句说习惯的话“走上绝路呢?”
鲁迅话说得好:路本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走的人多了,自然就成了路。
但若横在面前的是悬崖绝谷,还能往前踩吗?
杜雨见他欲言又止,问:“老弟你想说些什么?”
冷峻苦苦一笑说:“你知道的,我老是喜欢想些与主题无关的事情,我能有什么好说的呢?一头雾水罢了!”
“万事皆有定数,无须强求。”古风不知对谁在说话!“路,的确是走出来的。”
冷峻盯着他片刻后才说了句:“谢谢。”说罢起身告辞。
杜雨并不劝留,只说了句:“保重。”
春花秋月起身欲为冷峻开门,被他挥了挥手说:“不用了。”
于是,四个人便看着他的背影消失。
那瘦削的背影,有些凄怆。不该有不相称的凄怆。众人都觉得喉咙甚是苦涩。
窗外,一片小小的黄叶也在飞。
第六十八章 挑衅校长
路还是那条路。但走在上面时的心情却与往日完全不同;校园还是那个校园,他却感到陌生,自己和它多么地格格不入,他想。
校园里挺静,他迈出的步子有些犹豫,并不是由于迟到的原因。
他终于还是向自己的教室走去。
这一节是政治课,由一向严厉著名的副校长亲自授课。
冷峻出现在教室门口,班里的同学有些骚动,他面无表情地继续往前走,一句话也没说。副校长一直盯着他,也不讲话了,教室突然一下子又十分安静下来。
冷峻仍不吭声地朝前走着,已快到副校长的眼前。
“站住!”副样长喝道。
冷峻望着他,眼神黯淡灰蒙,似乎仍沉浸在苦苦思索中,而脚仍在前进。
“你听到没有,我叫你站住!”副校长禁不住逼了过来,脖子上青筋显露。
冷峻终于“回过神来”,眼睛亮了起来,眼神也犀利起来。他静静地盯着这位中年的副校长,很平静地盯着。
副校长只觉得一凛,竟后退了一步。他也搞不清自己怎么竟后退了。
人在许多时候做的事,的确连自己也搞不清为什么,反正做了就是做了。如果非要问到底,那也只能说“鬼使神差”。
于是,一股似羞似怒的激流涌向他的心头。他懊恼自己一个令学生敬畏堂堂副校长,竟然面对一个无礼的学生束手无措,还反倒先退了一步,多么丢人,多么地没面子!他的严厉缘于他脾气,这时他的眼珠已有了血丝,眼睛瞪得可以气死牛,吼了声:“你给我出去,现在就给我滚出去。”
全班同学都是大气不敢出,都替冷峻了把汗。
尤其是温婕和李思奇。自从冷峻失踪又复出后,她们就觉得现在的冷峻变得好陌生,他的眼神变得异常平静、冷漠、犀利,他的言语也变得异常平静,生硬,没有了往日的幽默风趣,没有了往日的潇洒飘逸,他似乎被什么压抑着,压抑得死死的透不过气来。好像被巨蟒缠住了,且缠得严严实实。
他到底受到什么刺激呢?短短的几天怎么说变就变,而且变得这么悬殊?为什么他从不向外人提起呢?对于冷峻的改变,她们感到惶乱,甚至还有些恐惧。难道他与黑帮有些什么深仇大恨,不然怎么会被他们折磨得那么惨不忍睹?
纯真的少女,最不愿看到心爱的人与黑社会有牵连,在她看来那就是堕落,就好像男人最不愿意看到自己心爱的女人作三陪或舞女般,不管她是不是洁身自好都是堕落,因为那种场合肮脏。社会对学生就是那种令人(炫)畏(书)惧(网)的场合。
在那些群体中,洁身自爱的人实在太少。现实中的人们,是不相信有出淤泥而不染的自爱者。不管韩宝娥将《舞女泪》唱得何等的凄恻,不管郑伊健将《古仔》演得何等的仗义,返回到现实中,人们对他们仍仅有鄙弃——或许也有人会给予同情的施舍吧,但只是少数。
冷峻沾染了黑社会,接近了黑社会。想象时,在他的身上就理所当然地有了黑社会的恶习:烧、杀、抢、夺、奸、淫、嫖、赌……
她们心里都隐隐在痛。不然,冷峻怎么会变得这般无礼?!
冷峻盯着副校长,一直盯着他,静静地说:“不麻烦你的唾沫了,我在你刚才说那句话时,就已经不再是你的学生了,所以请你说话时给我注意点儿,否则,我翻脸起来,你可别说我没给你打过招呼。”
同学们又是一惊:冷峻怎能用这种语气和老师说话?
副校长逼进冷峻跟前,呼出的热气和唾沫星子全洒在他的脸上,气之至极地说:“喝!不是我的学生又怎的。我照旧把你送到政教处。”
“那就看你有没那个本事?”冷峻轻蔑地说。
“什么?我没本事?!”说着,副校长就要过去扭冷峻的胳膊。
冷峻胳膊一挥,副校长就被拂得直趔趄,在他刚站稳,正欲怒喝时,却发现冷峻举起右手在讲桌上用力一拍,平滑厚重的讲桌上,立刻出现一只赫然的掌印。
副校长的眼镜随着眼角的一瞥,“啪”地一声,掉在地上。
教室里连呼吸声也没有了,空气仿佛凝固了。
“你说你有啥本事?”冷峻嘲笑道。
副校长不吭声,眼睛一直盯着桌面那个清晰的掌印。
“我可以走了吗?”冷峻说。
副校长仍不吭声,眼睛仍盯着那个清晰的掌印。
冷峻忽然笑了,笑得却很苍凉。他是笑着走出教室的。
温婕再也忍不住了,趴在桌上“嘤嘤”地哭了。
李思绮则红着眼圈,冲出了教室。“冷峻,你给我站住。”她气冲冲地叫道。
冷峻止住脚步,沉着脸说:“你有什么话快说。”
“瞧你那副德性,你以为……”李思绮很是气愤地说。
“请你说话时,注意一下分寸,并不是谁都喜欢听你骂人的。”冷峻说。
“你……”李思绮气得说不出话。
“我就是我,怎么呢?你要命令我?”冷峻问。
思绮变得温柔起来,像一个受了委屈的小姑娘,带着哭腔说:“冷峻,你不要这样好不好。我们是最好最好的朋友,你有什么委屈,有什么苦衷,尽管对我说,咱们一起度过难关。”
冷峻笑了下,说:“委屈?苦衷?谁能让我什么委屈?我能有什么苦衷?‘一起度过难关?’别太自作多情了。”
李思绮的眼中有两行清泪徐徐流出,她哽咽地说:“冷峻,你为什么要瞒着我们呢?我知道你不是这样一个人的。你知不知道,你这个样子,我们难过。”
冷峻咬了咬嘴唇说:“你不觉得你太自作多情了吗?”
思绮猛地抬头恨声说道:“你就真的这么狠心,这么无情,完全不顾别人的感觉?”
“难道你今天才看出我这个人的本质?”冷峻挑眼望着她。
思绮一抬手“啪”地狠狠甩了冷峻一耳光,然后掩面哭着跑开了。
冷峻望着她渐渐消失的背景狠吸了口冷气,猛地一甩头,昂首阔步地朝校门外走去,脚步很沉重,却也很毅然。
风吹过,漫漫黄叶坠落。若不弃我,怎保一树安妥?
天,很冷,冷得坚硬。
第六十九章 卧亭独酌
长坐枫晚亭,寂愁思古人。
饮者已久去,风中仍有音。
“自古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能饮酒并不能说就是贤者,而贤者却多半能饮酒,由于”古来才大难为用,“多少的幽怨、凄凉,只能寄于酒。酒的颓废也是酒的文化,酒后的佳作难道还用举例吗?”
无人理解的孤独,没人相伴的寂寞,才大难用的幽愤,离他而去的失意,还有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金榜题名,更是无酒不可,忧也是酒,喜也是酒,无酒便了无情趣。尤其是苟活者。
藏在人群缩在街隅,将头深埋进膝盖内。在自制黑暗的沉默中,倾听着耳鸣与心跳的回音。呻吟,凡庸淡漠的阴郁,灵魂脱壳的空虚。道貌岸然的狰狞,有夜空中的幽泣。借风随云,传达同病的人。苟活者。又提起酒瓶。
生活在不想要的生活里,却又无可奈何地挣脱只能称苟活。
苟活者最爱做什么事?其中当然喝酒为重。
枫林连绵至原始森林,层林尽染的枫林如一片火林,却又使人感觉不到火的热情,处身于火海之中,仅有的只是萧索悲凉。
蜿蜒的溪水源至原始森林,由于森林穷山恶水,地势险恶,野兽出没,也没人知道水的源头,它随着雨季而涨落,穿过枫林,与城北的湖水汇合。
枫晚亭据于溪水折流时一块突兀的巨石之上,亭下有个小池,是自然而成,溪水在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