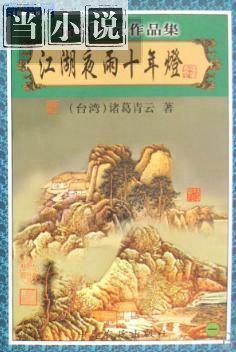十年沉渊-第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天劫子瞪起眼睛:“那你想怎样?”
这下,谢开言运气于胸,利索说道:“听闻大师有处藏书阁,晚辈想见识一下,开眼界,启发混沌心识。”
作者有话要说:已补全,我们这边下雨,肩周炎犯了,所以更新有些受影响,但我尽量不断更,请各位谅解:)
族长
天劫子百岁高龄,所藏书籍实属珍宝,帛面干燥无渍,字体如云流畅。就是那一捆捆竹简,也保持着烤过的青瓷色。谢开言踏进地下书室,迎面而来一股古朴松香,满壁的辉煌令她屏气静声,垂眸站在了桌案后。
待细细聆听天劫子的护书告诫后,她才洗手焚香,虔诚地翻阅古籍。
天劫子见她面色恭谦,替她滞留了琉璃灯盏,当先离开石室,放下了门户。
石室上方凿开通风孔,插入竹节,逢雨水,必定滴滴答答作响。石龛四壁置放香木,驱虫熏兰,指间便跳跃着一种书香。谢开言孜孜不倦地学习,每读一册,于胸中回顾一遍,不知不觉中,她的头脑如同破开了混沌,乍泻出一丝天光。
这些精利小篆、端正楷书,一个个跳跃起来,连成一幅画卷。画里,描金朱漆坊门大开,笔直的青石街道呈现在眼前,她骑着白马,一阵风地越过石阶、对楹,飞驰在悠长沉霭的巷子里。
“大小姐回来了!”
“大小姐回来了!”
众多稠色深衣的身影从楼阁里走出,在阑干上悬起了玉兰灯盏,一户接着一户,似是拉开了夜的帷幕,点燃了通往天阶的眼睛。她的白马朝前飞奔,宛如游龙,一刻不停息。马蹄敲击在方砖上,也是一种急雨般的讯号,谢族的姑娘婶娘们全部放下手中事,素腕执灯,红袖妆照,笑盈盈地看着她远去。
整个世族,只能她有如此殊荣,不解箭、不下马,由着众人簇拥着她,任她带走光明飞驰。谢一的名称,生来就是族长的预接号令,她们唤她大小姐,族内弟子唤她大师姐,尽管她年纪最小,不过十六岁。但是,一旦预置令下,她的地位就不能更改,除去刑律堂的谢飞叔叔,无论何人,必须敬她三分。
那时的她,如同初生的白虎,乳声令同林震惶。她的肩上,担负着谢族五万子弟的教驯。从街坊外跑到乌衣台,她数过,以横列五排对应谢族五堂,铺垫了整整五万块玉石方砖,右角上镌刻了整整五万个名字,笃笃的马蹄踏在上面,告诉她,每一个名字都是她的责任。
路的尽头通向巍峨宫殿,阶前第一块是金砖,四岁时,谢飞叔叔牵着她的手,亲自替她刻上了“谢开言”三字,并告诉她,日后族内兴兵操练,她必须站在这里,属于她的位置上,带领身后的子弟勇敢向前,成为南翎国坚不可摧的屏障。
她似懂非懂地点头,谢飞叔叔带着她,走向特设的石室。那里,也有满壁的书香、满袖的兰熏,灯烛照耀着一道小小的影子,数十年如一日。
影子慢慢长大,无论生病损伤,她都必须
读书、学礼、骑马、习箭,甚至是接受高深的丹青音律教识。她能背下诗书礼经,辨析繁复难测的天文星象,熟习马仗阵法,说出每一支翎羽的特征,却没法梳理好自己的发丝,穿整齐一套衣装。
因为那些,谢飞叔叔说过,身为预备族长的她并不需要。
终于有一天,她病倒了,几乎奄奄一息,怎么也不能清醒过来。谢飞叔叔日以继夜地照顾她,唤着她的名字,将她从司命手里拉回意识。他用更加严厉的管教训斥她,不准她生出死逃之心。
休病中,她看着窗外的灵鸟,扑腾着翅膀飞走,转到树后,突然走出一个精美绝伦的小姑娘。
她真的吃了一惊,那个小姑娘告诉她,她叫阿照,由金丝雀所化,特地来照顾大小姐起居。
从此,白马身后总是跟着一个身影,锲而不舍地追逐着她,一边喊着:“谢一谢一,你跑慢点。”她越跑越快,阿照摔跤了,头破血流。她纵马回来,阿照突然跃上马背,抱紧她的腰,呵呵笑着说:“我抓到你了,你是我的。”
秀气的脸蛋,玫瑰色的嘴唇,湛黑的眼珠动一动,倾洒出一片流离光彩。这就是存贮在谢开言记忆中阿照的影像,干净灵秀,像是青天外飞来的灵鸟。
可是如今,这只美丽的金丝雀已经飞出金粉世家,坠入了寻常百姓中。
谢开言不知道阿照去了哪里,长达十年的冰封生涯,雪藏了她的所有记忆。
细缕风声从竹节灌入,嗤地一响,引得灯盏跳了跳。
谢开言回过眼神,轻叹一声:“阿照……”半晌又说不出什么。南翎已亡,谢族覆灭,她记不住霜华般岁月所发生的,老天强压住她悲喜,让她成了活死人。
谢开言静坐半晌,克制内心苦痛,翻阅医典,对着自己所中症状琢磨。典籍由古代流传下来,记载颇丰,列述诸多症状,对沙毒及桃花障也有详解。
“沙者,地火也。烈毒犯冲,洗内髓破天心,炙热聚顶,灭六魄三生。”
“桃花障为情毒,戒嗔戒念。一层破孤闷,肤冷;二层断肠根,骨清;三层泯神智,血凝。此为大忌。”
亲眼看见毒病入骨之深,谢开言默忍半晌,才查找处方。医典上未交付沙毒解药,只设置一法,谓之热蒸。就是将中毒者放置于笼龛,倒入药汤,以沸水蒸荡,开气孔引毒血,血质变清才可。
桃花障由气瘴所入,性阴寒,亦谓之寒毒。采红景天、雪莲、杜仲等珍贵药材做引,融特制乌珠水成药,汤炼七七四十九天,得一粒丸药,唤作“嗔念”。即是戒嗔戒念。
“七七四十
九天……文火不熄……”
谢开言默念,瞳仁明光凉了半截。
如此珍贵的解药,先不说药引难配,还需要人工煎沸,聚齐这些条件当真难之又难。
莫非老天真的要亡她?谢开言细细思量,可转念一想,她不能服从这样的安排。命虽有天定,但她要翻转,否则愧对两世为人。
在少时学习,她读史,阿照陪侍一旁,读诗。阿照笑话她不似女儿,心肝不比千江水,来不得半点钟灵毓秀。她将古籍翻开,侧目说道:“越主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二十年之外,使吴国百宫为沼泽。这难道不是英雄之举吗?”
小小的她尚且懂得含冤负屈的重责,十年之后的她怎么可能不理解,命运究竟掌握在谁手中。
风入襟,谢开言苦读数日,不觉腹饿,唯当冷风雨露为伴,坦然安坐。这天,清露滴响,阴雨缠绵,天劫子叩门问讯,见无异样,下山配药离去。
谢开言走至山崖,腾空翻跃,习仿黄鸟打了一套拳。舒展开筋骨,她挽藤一荡,采集野果充食。树前雨水冲刷她的头发,露出光洁的额角,发根处隐隐带有一块兰青色印记。她不觉痒痛,不习梳妆,自然不知自身变故。看到天劫子不在山顶,她连忙抓住药铲,将藤蔓缠在腰间,徐步荡下,花费一些时间来到山腰处的那方绝壁石窟。
洞窟内一切如故,土壤泡水,变得松软了些,呈灰褐色。她执起药铲敲击四壁,并未发现任何离奇之处,当然,洞内藏宝的那些传说也成了奢望。
谢开言顺好额前发丝,察觉四肢起热,忙吐纳调息,放松心神。就在她灵台渐开之时,突然又听到一个声音,叮咚一响,像是钟乳石滴下一粒雨露那般轻微。
山是飞岩,本应浑然一体,却在雨水侵蚀下洞开一方石窟。石壁坚硬,本无中空,却在静寂处传来水声回响。谢开言觉得自然造化太过神奇,忙扑□子,竖耳倾听。
又是叮咚一声脆响,她没听错。
她找了找石窟地面松软处,两手握铲,使力挖掘。那泥土不知有几尺厚,直挖得她浑身燥热,差一点又要引得烈息游走血脉。药铲挖断了,她折断几根树枝挖掘,不屈不挠地,终于被她挖到了一个漏斗形的地洞。
谢开言运气于掌,猛地击向洞口。沙石土壤飞起,扑了她满脸,她跳到石窟外,接雨水擦洗干净,再继续用力震裂地洞。反复二十次后,地面豁然裂开,露出一道虚空的洞穴,黑魆魆地透不出光。
她翻转罗裙,将内里亵裤撕下裤腿,缠在松枝上。想了想,怕火把不够,她只得咬牙扯开袖罩
,涂了防冻止裂的獾油,再裹上一层。准备妥当,她晃开火折子,点燃火把,小心沿着洞口爬下。
洞口狭窄,仅容一人。游走几尺后,她将火把插在上方,跃下洞底。洞穴幽深,黑而潮湿,在暗影里张开口,如同一个怪物。借着光亮走了两步,突然从前方传来一个苍老而浑浊的声音,在问:“姑娘,你是谢族人吗?”
作者有话要说:谢谢各位厚爱,谢谢你们的长评,鞠躬ing~
回忆
洞底形如三丈见方的古井,四壁生满青苔,杂乱岩石堆砌过来,挂着十丈高的斑驳水迹。叮咚一声,从钟乳石尖滴下一粒细小的水珠,砸在了地面的化石身上。成片的烟灰与盐笋,像是银白的迎春藤,爬上了化石底座,累积成半尊雕塑。湿濡濡的水渍如菌花散开,侵蚀了塑像,掉落一片一片岩灰鳞。
“姑娘,你走近点。”那道声音就是从化石堆里发出,又说了一句。
谢开言借着微光,看清了前面的景况:一张枯槁的脸长在钟乳化石里,睁着两粒银黑色眼珠,正一动不动地注视着她。而那尊雕塑,就是老者石化的身子。
这怎么可能?谢开言听闻一切,心底浮现起第一个想法。
一个年过八旬的老人竟然风化成半尊泥塑,在这么静寂的洞底,在这么艰苦的地方!
谢开言环顾四周,眼底带着一丝震撼。听到老者在唤,她连忙走到两米开外的距离,盘膝在他面前坐下。洞顶的乳化石水叮咚滴下,淌开在塑像的脸里——倘若那还能称之为脸颊的话——老者伸出一截细利的舌头,朝右一卷,蘸到了那滴水。
谢开言观察到,老者为了汲水,将舌头拉伸成黑红的软鞭,如同蛇吻一般灵活。然而,他的手、脚、脸、舌都异化于常人,可见活得分外艰辛。
谢开言目视苍老的脸,运气鼓声,用腹语说道:“前辈是何人?”
老者后背紧贴在湿润的石壁上,赫然与洞穴生成一体。一截枯败的银臂慢慢抬起,像是冬天披雪的枝桠。他努力伸出手指,无奈只是动了动,根本不能撼动久积成石的身躯。
“我是谢族族长。”他才说了六个字,却用了很长时间。
谢开言稍稍抬起眼睫,瞳仁中便倾泻出微光。据她残存记忆,谢族百年来没有正式族长,历年由刑律堂长老代理职责。因为自谢族在越州乌衣台开创根本起,就立有规矩:族长必须由前一任委以信物,诏令天下,方能行使统领全族之权力。
二十二年前,刑律堂谢飞叔叔力排众议,上书南翎国君,请了一道圣旨,擢谢族四岁子弟谢一为预备族长。诏令书准备在谢一十八岁生辰上拆开,正式委任她族长一职。只是后来,她去了华朝,几经波折来到这里,中间有十年时光被雪藏,记忆如同炼渊之底的那道极光,慢悠悠地从她裸足边溜走。
回想往事,谢开言心内震惊,以腹语说道:“可我族百年来,一直没有族长。”
族长之位悬空百年,所有谢族人都清楚这个典故。
老者吃力说道:“这样看来,我留在这个山洞里,已经有一百年了。
”
谢开言眼中的讶然之色久久不散,但她保持着安静,给历经苦难的老族长一种安详的气息。
老族长说道:“一百年前,天下三分混战不休,我南翎国力衰微,即将覆灭。国君意欲与北理结盟,共同抵抗华朝。依照盟约,我国必须奉上皇子做人质。国君信任我,委派我护送皇子去北理。我带着不足三月的皇子乔装进入理国国境,这时华朝追兵赶到。我将皇子交给心腹之人,嘱托他先走,去都城伊阙等我消息。心腹连夜奔逃,我带兵冲进峡谷,掠起烟尘,吸引华朝军队来攻。华朝人炸断山脊,引发泥石冲下,带动山脉大片滑坡。那石流太过霸道,顷刻间就封住了所有出口,华朝人来不及跑,和我们一起被压在山下。我抓住马鞍,随着石流游走,被冲到了一个罅隙之中,折断了双腿。这一百年来,山体不断累积,我受困在这方小小洞穴里,吃青苔喝岩水,吊着最后一口气。”
谢开言的目光浏览在老族长已经风化泥塑的身子上,几乎不敢与这位沧桑的老人平视。
老族长喘息极久,才说道:“我不敢死。如果我死了,这个秘密就会和我的尸骸一起长埋于地底——我们南翎国不会灭亡,理国还埋伏了一支南翎皇族血裔,他们有个特征很好辨认,那就是双重耳廓。因为只要是南翎皇族,天生就是重耳人。”
老族长嘶哑地呼气,声音像残破的风箱。每说出一个字,都花费了巨大力气。他的四肢被困住,动弹不得,痛苦只能从身上的石灰岩鳞片上渗透出来,稍稍吐纳,便落下一片片惨白。
谢开言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