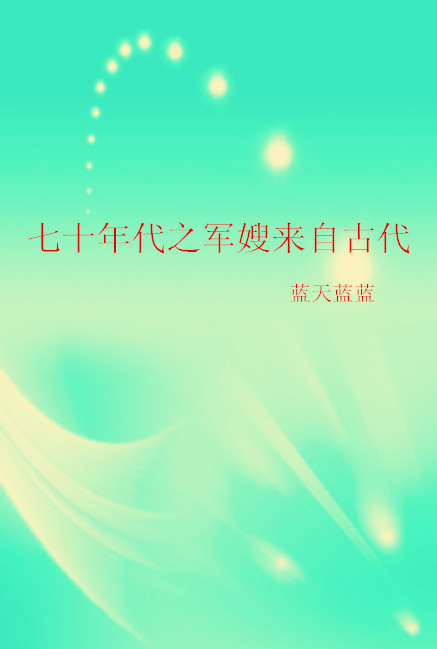地煞七十二变-第4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几名守夜的护卫一跃而起。
“谁?”
“谁在哪里?”
“藏头漏尾之辈,出来!”
乱糟糟的叫喊中,来者慢慢显出身形。
却是两个人,只呆在光与影的交汇处,瞧得见轮廓,看不清面容。一个高大雄壮,一个修长矫健,正是燕行烈与李长安。
燕行烈上前几步,走入火光照耀之中,冲那张执虎拱手说道:
“小将军,你身后那名女子乃是朝廷要犯,可否交给下官?”
“放屁!”
不出意料,这张执虎毫不犹豫就拒绝了,且戟指着大胡子,口中骂道:“分明是你这髯贼见色起意,竟然假托公务,强掠良家!”
“色欲熏心。”
燕大胡子摇摇头,知道话语讲不通,拔出剑来。
“竟然如此,就别怪燕某不客气了。”
“不客气?”那张执虎听了大胡子的话,却突然哈哈大笑起来。的确,若是平时,就自己这几个人的确不是燕大胡子的对手,哪怕对方受了伤,可现在么他拍了三下手掌,话语中还带着笑音。
“都出来吧。”
话音方落,那本寂静的林中忽然响起淅淅索索的声响,接着黑暗中接二连三燃起一个又一个火把。
火把下是一个个披坚执锐的精悍武士。
大盾在前,长兵在后,竟是隐隐将两人围了起来。
“髯贼!”
张执虎得意笑道。
“你那点儿纸人纸马的伎俩,早就被青妃看破了。”
他瞧着两人,好似在看两尾投入网中的游鱼,抬手下令道:
“拿下。”
老将心里烦闷得很。
倒不是因为燕行烈手段厉害。
诚然,这燕行烈确实名不虚传,虽然身陷重围,但仍旧能借着林中复杂地势,护着旁边的拖油瓶左突右冲,虽自个儿添了几处新伤,但身旁那道士却连衣角也没被挨着一下。
但在老将的安排下,合围的武士并不急于建功,只是牢牢稳住阵型,保持合围之势,渐渐压缩对方的行动空间。
若无意外,燕大胡子败亡只是迟早的事儿。
然而,老将烦闷得恰恰是这一点。
这可是镇抚司的燕行烈,擒之杀之都是小事,就怕因此恶了朝廷。介时怪罪下来,小将军顶多不疼不痒地挨几鞭子,他可就得拿脑袋背锅了。
不过么,好在他也留了一手。
老将摆下的这口袋阵,看来虽严密,但实际上却是留下了一个口子。
眼看包围圈渐小,知道事不宜迟。
“朱蛤子!”这老将忽的大喊一声,“给老子稳住了。”
但却背过白袍小将的方向,悄悄使了个眼神。
那朱蛤子心领神会。
突然“哎哟”一声,脚下拌蒜倒了下去,顺手还勾倒了身旁的同伴。
顿时,十面埋伏便只剩下了九面。
然而,接下来一幕,却差点没让老将骂娘。
这渔网明明开了个口子,但鱼儿愣是不往口子跑!
燕行烈拖着道士模样的累赘,愣是没往那口子钻。
老将也不好做的太明显,所以只照会了做人做事一向机灵的朱蛤子,其他人可完全不知道他心中纠结。于是乎,这口子转瞬就被其他武士合上了。
这小插曲没掀起什么波澜,其他人自然也没瞧出什么道道。
只有那红衣女子目光闪了闪,忽的开口说道:
“没成想这贼人竟然这般厉害,这么多人也敌不他。”
此话一出,张执虎顿觉面上无光。
“宵小之徒,有什么厉害的。”
他翻身上马。
“青妃看我如何把这髯贼拿下。”
说罢,他策马向前几步,忽的张弓拉箭,但利箭所指,不是燕行烈,却是李长安。
到现在他如何认不出,这道人便是替他了却三千烦恼丝的李长安。自打那以后,他头上是一直又疼又痒,偏偏他又是个极其注意外表的,从此,一顶头盔在头上就没取下过。
仇人见面自然分外眼红,他抬手一箭,含恨而出。
而另一边,重围之下的燕行烈逐渐左支右绌,这突如其来的冷箭他哪里看护得住。
这一箭竟然正中李长安背心!
第七十一章神射()
这一箭穿过人丛的空隙,精确落在道士的背心,而后又带着道士飞了出去,钉死在树干上,手脚晃动两下,便没了动静。
场中气氛微微一滞,而后又爆出一阵欢呼:
“将军神射!”
官兵们欢呼鼓舞,那小将却反而露出些疑惑:“我何时有这气力?”
而场中那朱蛤子同样满脑子官司,他可是亲眼瞧见过这道士身手的,怎么会死得这般容易?
莫非,这也是个
脑中灵光一现,他忙举着火把往道士脸上凑过去。
惨白的脸上两团艳丽的腮红,两双毫无生气的眼睛本呆滞看着地上,这火光靠近时,却忽的一动,吓得那朱蛤子手上哆嗦,火把就直直杵在了道士脸上。
然后。
“哄。”
一个大活人居然就这么被点燃,瞬间化作一个熊熊燃烧的火人。
“这”
张执虎汗毛倒竖,他猛地一个回头。
红衣女三人仍旧站在原地,在她们身后是一片约有三丈高的断崖,月盘高悬崖上,而不知何时,一个人影在崖边扶剑而立。
“青妃,当心”
此时,那人已然拔剑出鞘,背倚月光,自崖上一跃而下。
夜风飒飒,袍带当风。
背光中看不清面容,唯有一双眸子,森然凛冽好似宝剑生光。
最先反应过来是一个黑袍人。
他仰起头,握手成拳猛击自己腹部。
立时,便听着一阵好似野兽磨牙时喉头鼓动的怪异声响。
这黑袍人的眼、耳、口、鼻喷涌出大量的黑雾,汇聚在一起朝着李长安迎头兜去。
这黑雾怪异得很,虽是雾,却不似寻常雾气轻散缥缈,反而如大量黑色颗粒混在一起,翻滚蠕动给人粘稠的质感。
燕大胡子心里一个咯噔。
虽在重围,他一直不忘留意这边情形,眼见着诡异的黑雾,一个名字炸雷般响在脑中。
“巫家兄弟!”
这两兄弟是有名的邪派术士,却不知何时也作了白莲教的走狗。
这两人最厉害的手段,便是一口采自积尸地的阴煞之气,销魂蚀骨最为歹毒!活人迎面撞上,怕是连滩浓水儿也留不下。
燕行烈扫开乱糟糟刺来的兵刃,又抓住一根背后偷袭的长矛,顾不得矛头将手掌割得鲜血淋漓,只是急急开口提醒:
“小心,那是阴煞”
“斩妖。”
道士冷眼见身下黑雾翻涌,左手作剑指往剑刃上一抹,三尺剑刃立时青光缭绕。
迎着那黑雾,一剑斩下。
剑刃与那黑雾甫一接触,便好似热刀入牛油,那黑雾顿时一分为二,化作轻烟四散。
“不可能”
黑袍人满脸大惊失色,不等他作出下一步反应,青色的剑光便一闪而灭。
那惊愕的神情便僵在他的脸上,直到脸上浮现出斜切过整张脸的红痕,红痕中又泛起细密的血珠。
终于,半截脑袋沿着倾斜的红痕滑了下去。
“大兄!”
另一名黑袍人悲鸣一声,恨恨结起法印,口中迅速念诵:
“都天阴煞”
可惜三步之内,咒术快不过刀剑。
只见剑锋在月光下,倏然而现,这黑袍人喉头间便绽出一朵刺目血花。
“别动!”
道士施施然震落剑上残血,左手却早已抵在女子下颌,手指间吐出一枝小剑,剑尖微微陷入羊脂似的皮肤中,渗出一点晶莹血珠,沿着在月光下透着氤氲色泽的脖颈慢慢滑落。
这女子仍是一副娇柔妩媚模样,只是瞧着李长安,忽的开口说道:
“妾身真是有眼不识泰山了。”
“当不得圣女谬赞。”
道士笑着回应。
“圣女还是把手拿出来,莫作些多余动作。”
“妾身哪儿敢?”
这女子娇笑着,却是老老实实把背在身后的手拿了出来,忌惮地看了眼道士剑上渐渐散去的青芒。
“妾身又不是铜皮铁骨,可当不得道长一剑。”
此时,忽的插进一声咬牙切齿的怒骂。
“贼道人快放开青妃!”
“哎呀。”
李长安抬眼一看,熟人啊!
“这不是秃瓢小将么?”
这小将顿时涨红了脸皮,闷声不再言语,只是策马一枪刺来。
李长安却是笑嘻嘻道:
“小将军为何如此不解风情,佳人面前何必动刀动枪。”
说罢,竟是一把将女子拖到身前作了盾牌。
这妖女倒也配合,扮出可怜兮兮模样,期期艾艾唤了声:“张郎。”
一声下来,便是百炼钢也软作了绕指柔。
明明一枪下去,便能将那可恨的道人捅个通透,却偏偏会先伤及美人。
张执虎再三咬牙,终于硬不下心肠。他叹了一声,一勒缰绳,这狂奔的马儿竟是将将在女子身前转了个方向,这足以说明这小将马术之精妙。
然而,偏偏这时那贼道人却探出半个身来,在小将目眦欲裂中,抬手一剑戳在马屁股上。
“嘶聿聿。”
马儿吃痛之下,撒开四蹄就跑,带着小将一头扎进了林子里。
只剩下一句气急败坏的怒吼:
“崔老三,给我宰了这俩狗贼!”
然而,李长安只回以一身嗤笑。
他抬手指向前方,深吸一口气,平生第一次竭力调动法力,催行神通。
口中只一句:
“风来!”
语毕,群山呼应。
自山岭之巅,自峡谷之渊。
狂风携着腥气、寒气,夹着飞沙、草木、走石呼啸而来!
场中的火把没两下便被熄灭,人也大风裹挟冷不丁滚倒一地。
所幸这大风来得快,去得也快。
待那老将呼呵着众官兵起身,点燃火把,四下一看。燕行烈、李长安、红衣女,三人都已不见踪影。
“在那儿!”
一个眼见的官兵忽的指着一处林子大声叫道。
然而,话音方落,只听“嘣”的一声弦响。
这官兵便腾空而起,重重砸在身后树干上。在他的胸前,一根黑色四羽大笴穿胸而过,将其牢牢钉在树上。
接着,弦声如霹雳连响。
每响一声,必有人中箭而倒。
最后,更有一名兵士仗着身披重甲手持大盾,呼号向前,却被连甲带盾一箭洞穿。
场中立刻噤若寒蝉。
而林中也不复发箭,只有燕行烈的警告仿若掷地有声。
“追,则死!”
众兵士面面相觑,终究不敢向前踏出一步。
第七十二章无遮大会()
鸡鸣五更天。
徐氏夫妇早早起了床。
推开门户,四野寂寂。破败的茅屋塌伏在寒露中,门里门外都是空荡荡的,与郁州大多数百姓一般,家里窘困,黄狗也养不得一只。
依着往日习惯,徐氏捡起了锄头与背篓,身后却响起一声呵斥:
“你这婆娘,糊涂了不成?”
这么一提醒,徐氏拍了拍脑门,木讷的脸上难得露出笑容。
是矣,今时可不同往日。
两夫妻本不是这郁州人士,只因前些年李虎作乱,一家人为躲兵灾辗转来了这郁州,一路上盗匪劫道妖鬼捉食,一大家子便只剩下三口人尽数做了大和尚的佃户。
但这大和尚的“佛业田”也不是好种的,两口子竭力耕作也养不活三口之家,眼见得年幼的儿子夜里饿得直叫唤,两口子一咬牙就把独子送上了山去。
既入空门,与尘世就再无瓜葛,山上的幼子理所当然的断了音信。只听得只言片语,说是交了好运,被某个大和尚看中做了门下弟子,取了个法号唤作“本愿”。
徐氏夫妇本以为今生再也见不到儿子,直到昨日,寺里传来消息,儿子学佛有成,证得肉身佛。
要于今日的无遮大会上,登坛讲经。
这可是光耀门楣的大好事啊!
徐氏脸上的笑容有些僵硬,兴许是笑这种事情,自孩提之后,便已然生疏。
她喜滋滋放下手上农具,转头烧来热水,翻出一年也用不上几次的皂角,与丈夫一起细细梳洗。
完了,又取出一个包裹来,打开却是两件打满补丁的衣衫,褪下身上褴褛,小心穿上衣衫,这可是管邻家借来的,坏了可赔不起。
一番收整下来,似乎有了几分富足模样。两口子对视一眼,一人把住房门,一人到墙角刨出一个布囊,取出来数出几个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