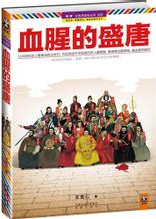盛唐余烬-第15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除去没到的于阗国王、毗沙都督尉迟胜,这三人代表了安西镇的地方势力,就连封常清到此,也只能以礼相待,更何况二人不过他的儿子和女婿,准。
“刘稷,见过诸位都督。”
“封浩。”
封大郎随意地一拱手,对他而言,这些人是国王还是别的什么,都没有区别,因为自己根本就不需要求到他们头上,这些人自然会知道该怎么做。
白孝节毫不在意他的态度,依然带着和煦的笑容,热情地招呼他们,仿佛自家子侄一般。
“二位能来,白某蓬荜生辉,不如进去坐坐,包管让你们满意。”
伸手不打笑脸人,他的这付架势,让刘稷无可奈何,如果只有自己一人,大可以拂袖而去,但是封浩在这里,就不能这么做,因为那样的话,等于为封府得罪了安西四镇所有的蕃国,也包括了不曾到场的尉迟胜,这决不是封常清愿意看到的。
不过他也想看看,这些土皇帝,倒底想做什么?难道真得以为,可以压服自己么。
“久闻都督府上,有最好的龟兹乐舞,我等今日有幸了。”
“呵呵,但愿能入二位的法眼。”
白孝节与众人俱是一笑,与他们一齐走向府内,他的宅子没有多少汉制的痕迹,反而带着一种西方建筑的味道,圆形的穹顶,拱形的廊柱和院门,精美的雕塑和壁画,当中是一个小小的喷水池,用的是自压式出水法。
两旁的回廊里,许多仆役在往来穿梭,他们的正面是一个极大的厅堂,大门洞开着,从里面传来隐隐的音乐声,还有一些调笑,看样子人不少。
直到走入大门,他才发现,这是一个极大的大厅,顶上装饰得金壁辉煌,四周的柱子呈镂空状,里面竟然烧着火炭,数十根柱子散发出的热气,将整个大厅里映照得温暖如春。
大厅里的两旁分别坐着两排人,看穿着根本分不出种族,每个人的身边都有一个服侍的女子,并非府中下人的打扮,而是青楼女子的装束,难怪那个小吏说,城中所有的女伎都被召了来,一眼望去,媚眼如飞、脂粉相闻,好不热闹。
刘稷不得不佩服他们的安排,在这种环境中,人最容易放松警惕,至少他身旁的封浩已经看得直了眼,完全没有一点将门衙内的矜持。
他在心里暗暗地鄙视了一番,便在众人热情邀请下,坐到了靠前的位置上,这里实行的自然是分餐制,每个席位上,都有一位侍酒的女子,他们自然也不例外。
入座之前,刘稷打量了一番身边的女子,是个年青的汉女,长相十分清秀,脸上的脂粉不算多,动作也不像他人那样主动,反而别有一番味道,看来主人是照着他的胃口安排的,知道自己偏爱良家,特地找了个人来扮演。
既来之则安之,刘稷端起几上的杯子,慢慢地品味着里面的美酒,等到所有人都落座,白孝节作为主人,并没有坐到首席上,而是站在最前方,突然伸出双手在空中拍了几下。
只听得一阵丝竹声响,从厅外进来一队女人,厅中所有人的目光全都集中在了她们的身上,就连刘稷也停下了杯子,目不转睛地瞧着。
那是一队胡女,全都做当地人的打扮,在十一月的天气里,身上只穿了一件薄纱裙,露出大片的肌肤,里面的亵衣紧紧地贴在动人的躯体上,观之令人血脉贲张。
一队八人的龟兹舞女,来到大厅的中央,排成一个菱形,很快,音乐声就变成了欢快而富有节奏的曲调,这些舞女随之做出动作,伸臂曲腰,昂首翘臀,跳起了一种十分优美的舞蹈。
“此舞名为‘拓枝’,安西诸镇,属这府中舞伎跳得最好。”
见他看得入了神,一旁服侍的汉女靠过来,为他添上酒水,刘稷闻到一股甜甜的腻香,不由得心中一动,一把将她的腰肢搂住。
“小娘子定然精于此舞,不知跳得如何?”
汉女的面上有几分羞涩,抬起一双妙目,轻声说道:“奴跳得如何,五郎不是看过了么。”
尼玛,又是熟人?
刘稷暗自骂了一句,低下头,在她耳边说道:“那日酒喝得多了些,光看人去了,娘子莫怪。”
“那不如,改日奴做东,单单跳与五郎一人看。”
汉女的手指在他的胸口上划过,眼神中秋波流动,声音舒媚入骨。
“可好?”
第二十六章 过节()
刘稷哈哈一笑,捉住她的手,飞快地在她额上印了一下,眼中已经瞥见,白孝节端着一个杯子走了过来,后头还跟着一个男子。
男子约摸一米八五左右,生得极为健壮,浓密的胡茬布满了整个下颌,使得他看上去有些大,实际上,从眉眼前,刘稷能肯定他最多不超过三十岁,令人奇怪的是,此人的面上颇有些不情不愿,看到自己,甚至露出了一个不屑的表情,一闪即逝。
正戏来了,他不动声色地与怀中的汉女作亲热状,直到听到白孝节的声音响起。
“五郎果然是少年风流,让人好生羡慕。”
“都督这是?”
刘稷作出一个惊讶的表情,手上依然紧搂着女子的腰,女子将身体埋在他的怀里,似乎羞不可当,倒底是专业人士,演技就是好。
此时,白孝节已经走到了他的席前,男子落后两步,眼神在他怀中的女子停留了片刻,随即便偏过头去。
“五郎莫怪,今天请你过府,一则是洗尘,二则么,与你赔罪,当日你二人的此许不快,全因此女而起,我做主已经将她买下,就此送与五郎,不知可能消了这等过节?”
刘稷一愣,难怪此女作良家打扮,并不是她想玩角色扮演,而是一早就被赎了身啊。
白孝节的话,让他想起杨鹄子当日说过的一件事,自己在抢了张连翘之后不过一天,就将人丢开,又跑去与某个人争花魁,难道指的就是怀中女子?
想到这里,他将女子放开,端起斟满的酒杯站起身,却没有举起来。
“都督吩咐,原本应当照办,可此事,不过是我二人寻常嘻闹,怎能劳动都督亲自过问呢。”
白孝节见他不领情,也不着恼,回身踢了那男子一脚。
“老七,说句话。”
男子足足比白孝节要高过一个头,却似乎很怕他,转过身不情不愿地冲刘稷一拱手,粗声粗气地说道。
“那日是某的不是,这厢与你赔礼了。”
刘稷定定地看着对方,能让白孝节亲自做陪的,这番过节定然小不了,他记得杨鹄子说当日事情闹得很大,连封常清都压不下,这才跑去了军中,其中未必没有躲避的因素。
问题是,这龟兹城的花魁,质量不行啊,还没有他抢进府的几个女子好看,难道是古人的审美有异?刘稷怎么看,都只觉得席间女子根本就不值得一争。
反观那男子,时不时就会瞥一眼,女子不敢看他,却也暗暗偏过头去,动作虽然极其隐蔽,又怎能瞒得过刘稷的眼睛。
此中定有隐情。
这个男子姓白,排行第七,与自己有过节,甚至不输于自己,他的判断慢慢清晰起来,若是没有料错,此人应该就是与之齐名的安西四害之首。
白虓噉!
当然,这是他的诨号,真名叫做白孝德,龟兹王族出身,安史之乱中一举成名,此时不过是个普通军校罢了。
“怎么着,白虓噉,你不服气?”刘稷有意说道,只见男子抬起头,目露凶光,没等说出什么,就被白孝节瞪了回去。
后者赔着笑脸,推了他一把:“老七性子倔,你莫怪。”
等到男子返身走远,白孝节放低了声音说道:“我已经安排他前往河西从军,不日就将启行,日后这龟兹城中,你再也不会看到他,五郎,算了吧。”
人家都低声下气成这样了,刘稷也不好再说什么:“其实大可不必如此,本就是小事,不是都督提起,我一早就忘了。”
“忘了好,忘了好。”白孝节举着杯子,刘稷与他轻轻一碰,都是一饮而尽,彼此心照不宣地揭过此事。
奇怪的是,事情说完了,酒也喝过了,白孝节却没有离开的意思,刘稷顿时明白,所谓的赔罪,不过是个引子,真正的戏肉还在后头。
果然,在他的示意下,原本坐在刘稷身边的女子,借口去梳妆,很干脆地让出了位子,等她一离开,白孝节便毫不客气地坐下,连服侍的人都不要,竟然亲自与他把盏。
礼下于人,必有所求,刘稷不动声色地与他举杯畅饮,想要知道,对方究竟是个什么打算,会不惜送女还要做出低姿态。
“听闻五郎此次立下大功,他日必有封赏,前途定然不可限量,但不知,是回到安西镇呢,还是另有高就?”白孝节一边看着堂上的歌舞一边问道。
刘稷同他一样,都是作出一付欣赏歌舞的模样,大堂上那队舞伎已经换了两只舞,此时正在跳着一只动作简单但却让人赏心悦目的舞蹈。
胡旋。
她们的身上挂着银铃,随着动作幅度的加大,清脆的铃声不绝于耳,身上的纱裙转成了一条线,露出雪白的大腿和曼妙的腰肢,就连腰间的肚脐都清晰可见,蒙着面纱的脸颊只露出一双眼睛,每个观赏都能感觉到,她们眼中释放的秋波,一时间无不是呼吸急促,连眨眼的功夫都舍不得。
白孝节一直在用余光观察着这位闻名暇尔的枭五郎,原以为不过是个色中浪子,没曾想,对方虽然作出一付色魂与授的模样,可眼里却没有一丝淫光,这种年纪,竟然有着不输于老司机的定力?与之前的那些表现显得格格不入,他有些不信。
毕竟传闻真实与否,普通百姓可能并不知情,他这个城中的地头蛇却是一清二楚的,哪一天抢了什么人,抢去做了什么,何时进的府,家人有何反应,全都瞒不过他的眼,根本就作不得伪。
就在白孝节以为他没有听清楚,打算再问上一遍时,突然听到一个声音,清晰地进入耳中。
“一条商路尔,值得都督如此煞费苦心,连害民之贼都要放过么?”
白孝节陡然听闻,心里就是一惊,手上的杯子一荡,洒出几滴酒水来,他万万没有想到,对方不仅猜到了他的意图,还给出了再也明确不过的答案,那就是。
毫不妥协!
第二十七章 私怨()
都督府厅堂后面是一个具有本地风格的天井,在水源匮乏的时候,人们往往会将屋子建筑在它的周围,当然,此时的水井以装饰的效果居多,两边的回廊里,府中的仆役进进出出,十分忙碌。
离席的女子来到廊下,靠在一根合腰粗的柱子上,露出一个厌恶的表情,不料被人从后面一把抱住,吃了一惊。
“阿妙,是某。”
女子停止了挣扎,面上还是有几分惊讶:“七郎,你怎会到此,不成,这里人太多了,会被下人看到的。”
“看到又如何,哪个敢说嘴,老子结果了他。”
白孝德毫不避忌地抱住她的腰,低下头,一边嗅着她的发香,一边去蹭她的脸,满是胡茬地在娇嫩的肌肤上滑过,刺得女子痒酥酥地。
“不能。”
女子不得不奋力推开他,整了整自己的衣襟,歉意地说道:“奴不能出来太久,一会儿还要回席,你也早些进去吧。”
白孝德受不得她的冷淡,恨恨地一拳砸在廊柱上,发出“咚咚”地声响。
“阿妙,你是某的人,某的人!”
“那又如何,奴的身契在都督手上,说白了,不过是他的一个玩物罢了,你若真有此心,当时为何不替奴赎身?也是,你就算接了奴去,家中悍妇如何容得,只怕一转手就卖与他人了,如今,都督将奴赠与刘五郎,你知道他的名声,此生怕是再见无望了。”
“某不服,谁得到你都成,为何偏生是他?”白孝德最听不得这个名字,眼睛一下子红了。
“服不服地又能如何,你我好歹相识一场,七郎,奴要走了,你多保重。”女子伸手抚了抚他的面颊,现出一个凄美的笑容。
眼睁睁地看着女子走过身边,一想到她要去曲意逢迎那个人,白孝德就无法忍受,就在女子即将走远的一刻,他突然间一个箭步上前抓住了她的手腕,力道之大,让女子忍痛不住,差点就惊呼失声。
“你做什么!”
“阿妙,跟某走,离开这里,咱们去河西,从此再也不分离,好不好?”
“你先放开。”女子挣脱他的手,揉了揉手腕,忍痛说道:“你疯了,这种话也说得出口。”
见他依然心有不甘的样子,柔声劝说:“奴是倡伎出身,如今赎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