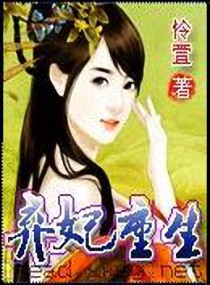毒局之静妃重生-第1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这有什么不敢的。”没让她咬上,可是恍惚间仿佛回到宫墙外的夜晚,福临的心跳像是被绳子系着摇晃的石头,他有点难以自制。
“你敢封她试试。”慧敏嗔着推他一把:“你这个坏蛋!”
“嘿,我就封她试试。”这一推就在胸口,福临的心火被点燃了,他很想逗她:“我凭什么不敢,吴良辅,吴良辅!”
守在门外的吴良辅很紧张地应了:“您有什么事儿?”
“马上去永和宫,说朕封……唔!”
慧敏突然翻身把他抓紧,按下去,她的唇,紧跟着往下压。
“我封……”好刺激的闪躲,像你追我赶的游戏,福临偏不服输,在亲吻间一次次躲她,说下去:“我要封……花束子……为妃!”
总算成功了,慧敏坐起来,一脸懊丧地对着他,瞪着他。
福临顺了顺气,扬扬下巴,十分自得:“还不快去,等什么呢!马上去!”他的手伸出帐外,指啊指。
慧敏“气得”把枕头也扔出去了。
他更加高兴。
吴良辅目瞪口呆:“啊?”
啊也没有用,君无戏言,说是什么就是什么。于是,最荒唐的一次的册封就在这个深夜降临。
花束子好像做梦似的接过印封的册子,她傻了。
“呵。”吴良辅一边想着明天该如何收场,一边给她道喜:“谨贵人,不不不,谨妃娘娘,您大喜,皇上着急,仪式简陋了点,回头给您补上,您别生气啊。”
怎么会生气,这是天大的喜事,恐怕连太后也会相当震惊。
“什么?”第二天,接到这个消息,太后也呆了:“怎么回事,为什么没人告诉我?”
吴良辅在下边趴着,快要哭了:“太后,皇上他不让说呀,奴才,奴才。”
“他不让你说你就不说了,他让你去死你死不死啊?”太后把梳妆台上的玉榔头往下。
“那那,”吴良辅想“当然只好去死”,但他绝不敢这么答,只有不停地磕,希望能够得到宽恕。
低头之间,太后看见她的玉榔头砸到他的帽儿上,直嵌了进去,随着他低头又抬头的,样子很好玩,不觉笑了出来。苏麻赶快趁机说:“主子,算了吧,皇上已经封了,难不成还改口。她是大阿哥的额娘,也不算太过份。”
“好吧。”太后隐约地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却又说不出来,过了一会儿,她想起来了:“福临昨晚在哪儿歇的?”
说曹操曹操就到,福临满面春风地走进来:“给皇额娘请安。”
“坐吧。”一大早就过来请安,太后很欣慰:“怎么记得这么早过来,这可少见。”
“哦,我是先进来的,慧敏在外边呢。”福临想想昨晚的浪漫情怀,一时怔迷,待太后提醒才又说了下去:“皇额娘,您还生她的气啊?要我看就算了吧,我都给您出气了。”
他把手放在母亲的膝上,轻轻地推。十足孩子气的撒娇。
太后有点明白了:“原来你……”她嗔怪地拍了一巴掌:“那你要封也要跟我说一声,从贵人跳上来,可不是小事!”
“我又不常见她,管她是贵人还是妃。”福临叹息一声:“要说她也不容易,好歹捡回条命,就当补偿吧。”福临心情超级好:“皇额娘,皇额娘。”
“好了好了,你别推了,答应你了。”太后侧身看看院子里的慧敏,很安静很乖的样子,想必是花束子封妃刺激的结果,心里也很痛快。
这对母子,就这么自以为是地各自想心事。
又聊了一会儿,觉得罚站够了的太后终于决定把皇后召进来。
“那好,我去叫她。”福临摸摸肚子,蹦跳着出去:“我早就饿了!”
“等等!都当了皇阿玛,能不能稳重点儿!”太后很无奈:“还有,你记着,别老往她宫里跑!要不然她更无法无天了!”
“知道啦,知道啦!”福临乐颠颠地出去了。
以后不知道如何,现在,他真的感觉像吃了迷药似的。这是为什么呢?
他跑出去,看见慧敏抬眼时温柔的笑,就觉得很开心,可是这笑容背后是什么,他却完全没有察觉。
慧敏被他拉着往里走,此间轻瞥一眼屋内的太后,心想:姑姑,你不是说,先封个嫔,以后再看吗?你不是觉得花束子低贱吗?咱们俩,谁赢了?
第十八章 一枝红杏
年轻就是最大的本钱。只要够能忍,总能等到胜利的那一天,唯一需要注意的就是方向一定要正确。
在歪斜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只会加速灭亡。
自从花束子的身份提高以后,宫内人对她,对皇后的态度也变得微妙起来。
莫名其妙的,在这天早晨,吴良辅竟向慧敏递起了话儿:“皇上明儿去督练营,问您有空没。”
“我?”刚用过早膳,绿叶端着水盆给她净手,慧敏坐在那儿,挑了挑眉:“刚才他怎么不说?”
“皇上忘了,最近他事忙。主子,您是去,还是不去啊。”吴良辅偷偷地察言观色:“要不,天冷,您就别去了吧。”
“不,我要去。”这种态度明明就是盼着她,慧敏怎么能让他失望。
看来,腊月着急了,着急到吴良辅都恨不得有人来帮她顶雷了。
最近督练营不怎么太平,皇上心里烦,谁陪着他,谁就有危险。这是盼着皇后把皇上惹恼了,然后好乘虚而入。慧敏想,这样我就怕了吗?
就是没有这桩,又怎么舍得不去走这一趟?
绿叶等吴良辅走了,才告诉她:“主子,好像最近督练营很‘热闹’,您要不要避避,您还是……”
记得,永远也忘不了,虐杀逃兵的事儿嘛。还记得,博果尔和济度他们为了这个弹劾下了狱。如今,既然时光重新走一遍,怎么也要帮这个忙不是吗,要不然,亲痛仇快,慈宁宫的那位该笑得合不拢嘴了。
再有,根据记忆,这段时节,应该是乌云珠跑得最勤的时候,她既然这么热情,又怎么好意思不给她浇冷水?一件事,如果是真心去做,当然应该人人赞赏。可是,做得太过,那便画虎不成反类犬了。
可是现在,最重要的不是这个。
鉴于上回在宫里的表现,也许,是时候再给她一点教训。让她学会,什么叫做安分守己。
军营里的士兵们都说,再好的女人,也比不上襄亲王府的福晋。脚伤还没有痊愈,就天天往岗位上送饭,风雨无阻,人人称羡。
博果尔幸福得快要醉倒了,就连鄂硕,最近也是抬头挺胸的。似乎,不久之前的那些传言,已经消失得像根本不曾存在过。
爱是长久的坚持,一天天,一趟趟,连续半月下来,就连太妃的态度也有所松动。
天下每个母亲最心疼的莫过于自己的孩子,倘若乌云珠是真心相待,她又如何能不心软。博果尔是她的命啊。
一个聪明的女人,在自己丈夫上“投资”的关怀,绝对不会亏本,只要他是爱她的。
半月的观察,太妃终于不再像之前那样呼呼喝喝,开始叮嘱她也注意下身体。
蓉妞乐疯了,待她走后,慌忙地向主子报喜:“主子,您的苦心没有白费!”
“好了,你别说了,别说了!”委屈求全的活着,一想到像行尸走肉般的日子还要继续很久,怎么能真正的快活。
为了阿玛,不在人前丢脸,为了博果尔能够放心,为了名誉,只有接着忍吧。
只盼有一天,守得云开,能够一偿所愿,那便死而无憾了。
老天总是公平的,这天,蓉妞走前想到兵营后方小解,突然听见两名士兵的窃窃私语。
“哎,不是说皇上要来吗,怎么老没动静?”一名手握长枪的高个子先开了口。
“这两天肯定不行,”另一名矮个子接道:“汤监正不是病了吗,要我说,皇上出宫肯定先去看他。”
“他?”高个子想了一想:“哎,他是钦天监的监正,皇上这么尊敬他,这宫里的药,他想用多少,谁还管?”
“那肯定是不想让皇上担心呗。年纪太了,头疼脑热常有的事,值得大惊小怪。”
隐约觉得是个机会。蓉妞忍不住走去插了句嘴:“两位大哥,你们说的这个监正,是不是汤若望?”
当然点头。
蓉妞喜上眉梢:“那,皇上什么时候去教堂?”
竟有这么愚蠢的丫头,两人望她一笑:“这我们可不知道,你得问皇上。”
碰了个软钉子,没趣地回来,蓉妞有点不服。
乌云珠一听,早已喜出望外:“你快点帮我打听,我要见他一面,我一定要见他!”
死性不改。真是不到黄河,不闭眼。
满心欢喜,早已将危险覆盖,乌云珠管不得后果,一心念着此事,敢想敢做,竟制定了一套计划。
说来也是天意,这些天,天天帮博果尔送饭,天天往外跑,想来开个小差,也是理所当然,不会被注意。所以,竟一时鬼迷心窍,胆大包天。
西山树林是携径,午时前给博果尔送饭,然后到这儿换装,进城去教堂,再回来,一个时辰,应该够了。
“主子,咱们的衣服,放这儿?”蓉妞回头看看草堆,很不放心。
“只有这样了。”换上男装进城,是为掩人耳目,至于包袱放在这里,也是为了不让外人发觉里面放得是什么,以免节外生枝。
“好吧,那我们得快去快回。”蓉妞说着,心里很怕:“主子,您把把式和下人都撵走了,咱们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赶车护送的侍卫,被乌云珠借口赶回了家,此刻,只有她和蓉妞两个。
为了心中所想,已经管不了这许多了:“我知道,蓉妞,可是我要见福临,不能让他们看见!”
“好吧。”蓉妞无奈地依从:“主子,那咱们小心点儿!”
随后,这两个穿着男装的女人鬼鬼祟祟地行动。
教堂很快就到了,却是关着门的。消息打听不来,只好坐在对面的茶馆里等,直等了两个时辰,才看见汤若望和一名传教士谈笑风生地走来。
虽然鹤发鸡皮,却是神采奕奕,并不见半点病色。
从前见过的,乌云珠一眼就认了出来。隐约觉得糟了,却不知道错在哪里,她急步出去,捏着嗓子问道:“您,您……”
福临看来是不会来了,总不好一开口就问人家为什么没生病。汤若望觉得眼熟,把她上看下看,看得她心虚,话也顾不得问完,只好和蓉妞跑了。
其实还是蓉妞拉的她,不然不死心还要再等。天色变了,蓉妞说就要下雨,才把她拽回树林。一路上真的倒霉赶上,像倒水似的往下流,满身都湿透了,衣服紧紧地贴在身上,眼睛也看不清路,真是悔不当初。
即便如此,该找的衣服,还是要找回来。好不容易顶着风雨赶到那棵做了记号的大树上,伸手一捞,却是空空如也。
像从噩梦中惊醒,蓉妞转了个圈跑过去看,真的没有。
怎么办?
天色渐渐暗了,乌云珠不得不当机立断赶快返回。这样的情况不敢直接回王府,想想,厚着脸皮,啪啪,拍响了娘家的门。
到王府已经华灯初上。脸如醉红,步履蹒跚。博果尔今晚回来吃饭,比她到得还早,伸手一摸,烫得不行,急道:“你去哪儿了,怎么回事!”
乌云珠没脸回他,倒在怀中晕了过去。
高烧不退,一连病了四天。蓉妞跟她一样,心结解不开,整天疑神疑鬼,生不如死。
衣服到底为什么没了?怎么会这样,到底为什么?
从早到晚,念着这个问题,就是好好的人也要生病,更何况又受了风寒。
真是后悔莫及,后悔莫及。
乌云珠心中暗想,早知如此,我何必非要见他不可,我若是能忍得一时,或许……
有所悔改,应该给一次机会。于是,在第五天,出门散散心的乌云珠和蓉妞经过路边的回春堂,突然看见小二站在门口招手。
蓉妞看了两回,确定是指向自己,才跟乌云珠禀报走了过去。
刚走到面前,她就吓傻了。小二交给她一块手帕,还有一封信。
那块手帕是粉白色的,蓉妞激动地对乌云珠:“主子,这是!”
乌云珠急忙摆了摆手,把她拉去街角。她才有机会说完后半句:“这是奴才的,这是奴才的!”
是她们那天放在树林包袱里,这块帕子,不过其中一件零碎。
看信吧。乌云珠感觉到,跟这块帕子比起来,也许,这封信才是真正要紧的。
封皮无字,信上也无字,只画着一枝弯折了的红杏,红杏的花瓣还是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