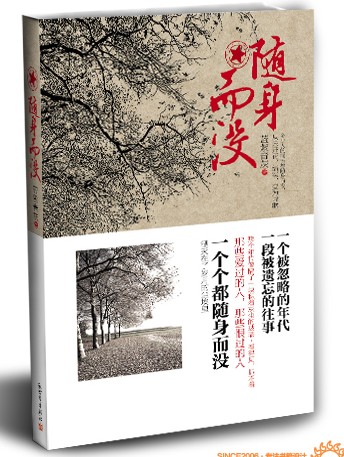随身而没-第1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那夜小毛贼又摸了进来,被埋伏了好久的童队长抓个正着,童队长摸出腰间的枪来顶着毛贼,差点就要扣板机,好在最后理智占了上风,只是捆起来交到厂部让领导处置。
方主任看看这情况,心里也为难,通知了村支书来领人。村支书看到自己村里本来老实巴交的子弟竟然成了毛贼,又被人用枪顶着,心里窝火,这次再不肯与厂里好说好散,只说你们的狗咬了我们的人,你们砍了我们的树,你们占了我们的地,你们教坏了我们的孩子。你们这些讨厌的上海佬,你们滚出我们的村。
方主任和童队长一听就发了火,说你们偷了我们的雷管炸药,你们偷了我们职工的钱财物品,怎么反倒是你们有理了?我们好好叫你们来领人,又没说要把贼交给公安局派出所,也是看在我们是邻居的份上,你们领回去好好教育才是,怎么反怪是我们来了?
村支书说你们来之前,我们这里从来就没出过这样的事,你们一来,什么都搞坏了,树被你们砍了,地被你们占了,子弟被你们带坏了,你们拿了枪对着我们,我们可是贫下中农!
童队长冷笑说,你贫下中农了不起?我们还是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就不会偷东西了?如今人赃并获,你还有这么多说的?我告你一个包庇罪犯,连你也逃不了罪责。
两边吵得不可开交。方主任也火大,扣下那几个偷窃的,不肯交给村里了。这一来更是把事情激化了,不但是村支书不走了,连那几个青年的父母爷祖也来闹了,七大姑八大姨也来了,三舅六叔也来了,这一个村子都是一个姓,全是本家,呼啦一下,全村几千人都来了,扛着锄头举着镰刀,一派要攻占山头的模样。厂里的职工一看这么多人来进攻厂子,班也不上了,从仓库里拿出枪械来严阵以待,逼村民离开厂子。
锄头镰刀哪里是枪炮的对手,村民也识得些家伙的厉害,先自退了。这一仗村民算完败,但村民中有见识有魄力的哪肯就此罢休,组织了能言善辩识多识广的人进城上访,坐了车到了上海,跑到革委会门口去哭冤,说你们的厂子在我们当地欺压我们,派狗咬伤我们,砍我们的树,抓我们的人,拿了枪要杀我们。
毒狗砍树都是小事,拿出枪来对着阶级兄弟就是大事了。市革委会书记马天水亲自出面过问,先安抚了上访的村民,劝他们先回村,又派调查组跟着他们到了厂里,问清了事情的经过,答应放了那几个青年,工人农民是一家,都是阶级弟兄,怎么能闹到枪对枪刀对刀的呢?又把方主任批评了一通,对童队长更是严厉,连带他的手下那几个拿出枪来的人都撤了职,村民们才算满意了,带了本村子弟回家去了。
但职工们却义愤填膺,觉得委屈得要死,围着调查组说你们黑白不分青红不辨,再这样下去,我们的财产和人生安全都会受到威胁,我们不干了,我们要回上海。既然人家不欢迎我们在这里呆下去,那我们走好了。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到处不留爷,爷去投八路。八路都不给我们撑腰,我们就去睡在南京路上,上海市民总会给我们留一块地方睡觉的。
调查组看安抚了那边,这边不干,只好继续和稀泥,拨了一批紧俏物资来供应,才算平息了这场风波。
但经过这么一闹,上海人和本地人之间的矛盾深得不可调和,再无往来。楚河汉界,壁垒森严,“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这样的浪漫故事,只会存在于后来城里人的想象之中,在当时,那是完全不可能的。
自古道,财帛不可现人眼。便若三岁小儿身揣万贯家产招摇过闹市,旁人自然会起觊觎之心。这是人之本性,原是怪不着谁。这些上海人来到山里,凭空移来了一座城市,吃的穿的用的花的,全比本地人要好,既要显得与本地人不同,又不肯与本地人分享,那就怨不得本地人要眼热加仇视。这样的矛盾和冲突,原是迟早的事,就看是那一件小事触发了暴发的情绪而已。
七六年
一九三月八日,吉林下了一场史所罕见的陨石雨。下午三时许,一颗光芒耀眼如同太阳的巨大火球从东往西掠空而过。天空中惊现两个太阳,一个太阳还在凌空飞行,这一天文奇象顿时让所有当地人惊骇不已。低空飞行的硕大火球在天空飞行一分五十九秒之后,再一次令人震惊地,在吉林市北部上空爆炸了。
爆炸声惊天动地,燃烧的火球化作团团火雨坠落下来。爆炸声像夏日暴雨前的雷声,轰隆隆回响不绝,持续有四五分钟之久。伴随在雷声之后自然是暴雨,燃烧着的火雨在空气中焰光渐弱,最后变成几百块石头像雨点一样抛洒进了地球。
最大的一块陨石挟着从几千万米高空坠落的速度,带着亿万年的星光尘埃,穿过一点七米的冻土层,砸进六点五米的粘土层里,在地面留下一个直径两米的凹坑。陨石落地后,泥土飞溅,黑烟滚滚,地面上升起了数十米高的蘑菇云状烟柱。
这一天,这一地区,成千上万的人看到了这一场陨石火雨,更有百多万人听到了它爆炸时的轰然巨响,几天之后,全国八亿人都知道了这一场陨石雨。
紧接着是四·五天|安|门事件,再后,是七·二八唐山大地震。
窦娥冤而六月雪,孔明死而将星坠。伟人谢世,天崩地裂。
一九七六年,中国龙年。
这一年三大领袖齐殒。
周恩来总理殁于一月八日,朱德总司令殁于七月六日,毛泽东主席殁于九月九日。
十月十四日,徐长卿从帐子里钻出来,一脸的惊诧,对仇封建说:“不得了了,北京要出大大事了。”
“不要大惊小怪,有事快说,不要开玩笑。”仇封建抓了只毛笔,像抓筷子,也在练字。
主席刚逝世不久,全国人民都还沉浸在悲痛之中,牌也不打了,棋也不下了,鱼也不捉了,鸟也不捕了,去师傅家吃饭这样的美事好久没有过了,童队长自从被撤了职,查夜也没人查了。总之这一段时间大家修身养性,厂子处于半停工状态,上班也不过是围在一张桌子前折白纸花。折得堆满一桌子,再一朵一朵扎到花圈上。厂里白纸扎的花圈从厂门口直摆到六车间里头,到处都是青纱缠臂,白花佩胸。天天开会悼念主席,哀乐一起,哭声一片。
悼念伟大领袖的横幅挂满了厂子的每一幢大楼前,墨汁用脸盆装,毛笔如森林状,整捆整捆的白纸用大片刀裁了,需要的人都可以去工会领一叠,回宿舍写字。徐长卿的毛笔字是下过苦功夫的,很拿得出手,专机组又都女同志,多数没上过几天学,字也不好,于是专机组的标语横幅便全由徐长卿包了。他们宿舍的桌子上,墨汁毛笔纸一直摊着,要写随时抓起笔就写。写毛笔字这种事,是会让旁边人看着手痒的,他写,这一个宿舍的人便都练上字了。仇封建一只手掌可以抓起一只篮球,抓起毛笔来,就有点僵,写不了几个,扔下笔就不写了,过一会儿又去写。晚上八点是徐长卿雷打不动的收听美|国|之|音的时间,他躲进蚊帐收听敌台,仇封建就写字玩。
徐长卿把嘴附在他耳边轻声说:“不和你开玩笑,是真的。电台里说,北京把江青给抓了,还有瘦猴精张春桥……”徐长卿说着,自己也有点不敢相信,是不是听错了?还是美帝反动派在造谣?
仇封建张大了嘴,惊得目瞪口呆。手一松,笔掉在纸上,污了好大一团墨迹。
徐长卿和他两个人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一时不知该怎么表达惊骇的情绪。是欢呼?是害怕?是马上告诉别的人,还是再等一等,等中央的文件?
仇封建问:“你确定没有听错?”
徐长卿摇头说:“我敢百分百确定。不过暂时还是不要传得大家都知道,明天再听一遍就知道了。”
仇封建点点头,“这下要出大事了。”
这么大的事,还不算大事吗?只是各人被这一年太多的大事折磨得早就不知所措了,人们脑中的神经反反复复、反反复复地拉抻弹回,拉抻弹回,已经兴奋不起来了。知道这是大事,知道会有巨变,但是是怎么的巨变?又会给人们带来怎样的希望?抑或更大的失望。
第二天,这个消息还是传遍了整个厂子。有收音机的不是徐长卿一个,收听美|国|之|音莫斯科广播电台的也不只徐长卿一人。他会沉默不语静观其变,别的人可不会。当夜便有人窜迹于各间宿舍,不到熄灯号吹响,差不多的人都知道了。但大家也都将信将疑,说好第二天继续收听。
晚上大家都聚在收音机旁,听着太平洋彼岸美国传来的进口消息。这个年代,大家早就不相信电台报纸上说的了,要知道什么新闻,听美国人怎么说。
美国人说了,大家听见了,先是沉默,后来小声议论,人群散后,还在窃窃私语。这个年代,人们的胆子都比芥菜籽还小,平时骂天骂地骂爹骂娘,真有大事发生,却又惶惶不安,谁敢去向领导求证这足以让人掉脑袋的消息?只要问一问你从哪里听来的,一条“收听敌台”的罪名,便可让人去吃牢饭。难道真的要亲身去实践一下“两人同戴一幅镣铐”的情景?
来听收音机的人走完,师哥舒关了门,刘卫星一向爱胡说八道的人,也老实了,只是不停地说一句话:“要出大事了。”
十六日上午,厂里的高音喇叭播放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确确实实,“四人帮”被抓起来了。
一下子全厂的人都欢呼了,把可以抛的东西全部抛上天,白纸花也摘了,青纱袖箍取了,伴着高音喇叭里振奋人心的消息,把每个人心头的渴望渲泄出来。
他们共同的心愿是:“四人帮”垮台之日,便是他们的出头之时。
历史的必然是,总会有一个挺身而出,挑起顶天的大梁。在北京,是叶剑英元帅,在厂里,是老叶师傅。
高音喇叭里“四人帮”倒台的传达报告一结束,老叶就把朱紫容,徐长卿,刘卫星,仇封建,还有师哥舒几个人连推带拖地拉了就走。朱紫容被他拉了走得飞快,要小步跑着才能跟上。嘴里问:“干什么去?你拉我跑了这么快干嘛?还带上他们?大家都在听报告呢,你要去哪里?”
老叶不回答,只是说“快点快点”,转眼便把几个人带到了车库。看守车库的人跑去听报告了,门也没锁。老叶挑了一辆大卡车,把四个小青年赶上车厢,叫朱紫容坐进副驾驶位子,朱紫容被他一脸的严肃和神秘的举动搞得莫名其妙,再问:“老叶,侬要做啥?侬昏头了,侬要开车子?”这时老叶已经发动起了车子,朱紫容尖叫一声,“老叶,侬要把车子开到啥地方去?”
“等会儿你就知道了。”老叶仍然不说,打着方向盘,倒着车,把车头掉往厂门口的那头,按了按喇叭,哈哈一笑,说:“开路依马斯。”
老叶开着车,一路上使劲按喇叭,却又把车开得慢慢的,“啼——啼——啼”的声音响彻整个山谷,朱紫容就坐在他身边,被这刺耳的喇叭声惊得坐不安稳,尖叫一声说:“老叶,别按了,吵死人了。”老叶脸上透出兴奋来,说:“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车子进入厂区主干道,一路高鸣而过,引得旁边的人都来看,车间、仓库、宿舍、住宅楼,办公室……里头的人涌了出来,跟在卡车后面,七嘴八舌问是怎么回事,老叶要干什么?就像是战争片中坦克轰隆隆地开在前头,后面跟着步兵一样,坦克打头阵,步兵紧跟。这卡车也同样起到了指挥官的作用。
车子开得慢,有急切好事的男青年伸手搭在车厢上,徐长卿他们帮一把手,拉他们也上车来。更多的男青年加入到这个行列中,不多时车厢上就站满了人。每个人的脸都兴奋得发红。
到了主厂区,老叶把头伸出车窗外,大吼一声说:“打倒‘四人帮’,我们得解放!”他口号一喊,后面车厢里的徐长卿他们马上心领神会,也齐声大喊:“打倒‘四人帮’,我们得解放!”
车子后面跟着的职工顿时被惊醒,在徐长卿他们喊完后,也跟着大喊:“打倒‘四人帮’,我们得解放!”
打倒“四人帮”什么的,不就是推翻他们当政时犯下的路线错误吗?三线厂投入巨大,产出有限,不搬回去还留在这里干什么?人们一听老叶的口号,便觉得是喊出了他们的心声,于是一浪又一浪的口号喊得整个山谷像山洪爆发一样,听不出哪一声是主声,哪一声是回声。
老叶却意犹未尽,斗志正高。他把车停在厂部办公楼前,跳下车,对车厢上的徐长卿说:“老徐,去拿锣鼓去。”
徐长卿他们一听便明白了,也不下车,直接从卡车车厢上搭上办公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