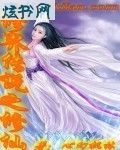后宫琳妃传-第9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奕渮的笑意柔和,却隐隐含着一丝凌冽,若细细辩驳,似乎能看到一抹哀戚与怆然了:“听闻梁府突发大火,本王心里也很难受,毕竟梁太医服侍了太后七年,事无巨细、皆妥妥帖帖。只是本王得到了些许消息,梁太医为太医院院使,却为官不正,更曾牵连后宫,下药夺人性命,不知太后娘娘作何感想?”
朱成璧大惊,电光火石间已做好了万全的准备,她正一正耳垂的金累丝灯笼耳环,凝视着奕渮在自己面上逡巡不定的目光:“竟有这样的事?哀家倒是疏忽了。不知,是否只是误会?”
“不是误会,但也不怪太后,他也是为人做事,尽一尽奴才的忠心罢了。”奕渮的唇角似噙着若有若无的笑意,却步步紧逼,“若是旁人便也罢了,左不过太后昔年亦是为难,只怕你不出手害人,就会有人来害你。只是,如果事情牵连到昭宪太后,本王就不得不追究了。”
朱成璧下意识握紧拳头,心头的疑虑与震恐已如潮水一般涌来,这样铺天盖地的席卷,让人心头一窒。
朱成璧后退一步,却已被奕渮牢牢持住双臂,奕渮的眸光是亮泽的恨意与痛悔交加:“你知道!”
玄凌忽的站起,怒目瞪向奕渮,扬声道:“摄政王!上下尊卑有别!你怎能在太极殿失礼!”
奕渮毫不相让,犀利的目光如迅疾的白色闪电劈过,直欲将玄凌狠狠击中:“皇帝!这里没有你的事!你出去!”
情势突转急下,竹息亦是惊骇万分,她死死扶住朱成璧微有颤抖的身躯,低低劝道:“摄政王!您这是做什么!”
奕渮冷冷迫视朱成璧极力掩饰着惊疑神色的容颜,呵斥道:“住嘴!竹息!本王素来对你礼让,你也不要逼本王,你们都出去,本王有话,要亲自来问太后!”
朱成璧定一定心神,将那颗几乎跃出胸腔的心极力按住,用舌尖拼命压住颤抖的牙齿,须臾,淡淡道:“竹息,带皇上出去。”
玄凌情急道:“母后!”
“出去!”朱成璧的眸光冷厉如剑,直直射向惊怒失措的玄凌,丝毫不见动容,“母后的事情,你不用过问!”
待到一干人等出殿,朱成璧方徐徐望向奕渮,似是波澜不惊:“你一直抓着哀家不放手,是又想闹得满城风雨吗?”
奕渮的眼中划过深深的阴翳之色,如坠入墨汁的一池清水:“本王自是不愿意这样,但本王也很好奇,本王对当今皇太后轻薄,自然是惹得世人纷纷指谪,只是,当年太后你给皇兄、给母后下药,难道就不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了吗?”
朱成璧皱一皱眉,欲推开奕渮相持的双手,孰料奕渮却更加重了几分力道,朱成璧一时吃痛,怒目道:“放肆!你指责哀家给先帝、给昭宪太后下药,你有何证据!”
“证据自然是有的,否则本王怎会在府里呆那么久?”奕渮剑眉一挑,逼视朱成璧道,“我只消你一句话,你做过,还是没有做过!”
“当年,昭宪太后是自己不肯吃药,不关哀家的事!”朱成璧的眼角似有莹然泪光泛出,“你欲加诸‘莫须有’之罪,何苦跑来责问哀家!”
“母后为何不肯吃药!”
“先帝怀疑她与昭慧太后之死有关!”
奕渮哈哈一笑,那笑声极响、又极悲怆,他紧紧看向朱成璧不欲相让的目光,“你看着我的眼睛,你用你我相识二十三年的情分发誓,母后被怀疑,与你无干!”
朱成璧心里一痛,几乎是要撕开心肺,又仿佛是艳阳六月的天,被人兜头盖脸泼来一盆冰水,那样的冰寒,是裹挟了全身、从每一处毛孔渗入的痛苦,连一腔热血的心扉,都冷到了极彻底。
朱成璧极力忍住欲躲避的眼神,含着泪意望向奕渮乌黑色的瞳仁,似照见二十三年前、彼时烂漫天真的自己,纵使心里再痛,也要凝成这一字一顿、掷地铿锵:“昭宪太后被怀疑,与我无干!”
一滴泪,忽然滑落在奕渮的手背上,似被灼痛一般,他猛地缩回手,不敢置信地望着朱成璧。良久,波云诡谲的气氛在太极殿里漾着,仿佛有一丛又一丛的水草,在波光荡漾里摇曳着身姿,紧紧扼住朱成璧与奕渮的喉咙。
“你变了,你真让我失望。”奕渮呛然退开两步,摇着头,仿佛从未见过眼前这个女子,他不住地摇头,步步后退,似要躲避、又似想看清,“你变了,你真的变了。”
朱成璧嘴唇干涩,待到辩解,奕渮的话却如惊雷一般在耳畔炸响:“梁诺轩在本王手里,郑慕宁也在本王手里。本王给过你机会,让你说实话,可笑,你我二十三年的情分,都只是你掩饰自己的道具。”
朱成璧愣愣看着奕渮转身离去的背影,心里被极锋利的刀片割过,涌起的疼痛猛烈得几乎要麻木了,她突然感到,这世上所有的真心与情爱,离自己,实在是太远太远了。
朱成璧忽然想起年少的时候,奕渮拿了一句话来与自己玩笑:比翼连枝何日愿。而彼时的自己,却只是掐了一朵彼岸花在手里把玩,闻言脸上一烧,只嗔怪道:“害不害臊!”
如今看来,比翼连枝的念想,是从来,都不属于自己的,哪怕曾有那样多、那样好的机会。
原来,擦肩而过,真的是,再不能相见了。
第四十章 比翼连枝何日愿(2)一
第四十章
比翼连枝何日愿(2)
竹息惊惶失措地进入太极殿的时候,朱成璧斜坐在橙金色的地砖上发愣,她的目光那样远,远到几乎融入了天际飘摇不定的云端,远到几乎捉摸不到、触之不及了。
“太后娘娘!”竹息急急搀起朱成璧,唤道,“您到底是怎么了?摄政王与您说了什么?”
“来不及了。”朱成璧机械般地摇头,大滴大滴的泪珠滚落,在地砖上破碎成粒粒晶莹,“再也来不及了。”
颐宁宫,紫金朱雀灯下,朱成璧面容疲倦,只斜斜倚靠在织锦掐金的玫瑰色贵妃长榻上,一寸一寸抚摸着膝盖上的一柄镂金嵌珍珠玉如意。一旁的竹息低低劝道,“太后娘娘,您好歹也进点食吧,您都一整天没有吃东西了,身子若是受了损可怎么办呢?”
朱成璧有气无力道:“皇帝呢?”
“去了枕霞阁。”
“端妃性子清冷,齐正声战死后,又染了风寒,安柔荑性情温顺,最能安慰皇帝。”朱成璧语调虚弱,盈盈无力,一语未必,已是低低咳嗽起来。
竹息急得直跺脚:“都什么时候了,您还惦记着旁人!太后娘娘,就算您心里再不好过,也不能委屈了自己啊。”
“委屈?我还能怎样?左不过过一天是一天,等着摄政王来逼宫,赐我一条白绫,我现在一心求死,什么都不愿再想了。”
竹息愕然,抿一抿嘴道:“太后娘娘,摄政王不会如此的。”
“我害死的不是旁人,是他的养母,贵嫔当年是自愿把他交到淑妃手中,而并非像昭慧太后那样被算计。更何况,是我害得昭宪太后死后灵位不入太庙,梓宫不入皇陵,只能葬入妃陵,后事极其清冷……”朱成璧紧紧握着手里的蹙金撒松花帕子,直到指关节微微泛白,“即便,即便这些他都能原谅我……但我数番欺骗于他,他如何能忍受……”
“太后娘娘!”竹息急急唤道,“即便今时今日,过往的事情摄政王都心知肚明,但您毕竟是他至生所爱。”
“正因为如此,这种被所爱之人算计和欺骗的感觉才最会让人风魔……”
竹息怔忪片刻,低低一叹:“当年的事情,太后娘娘也是无奈。”
朱成璧的笑意凄惨,仿佛秋起黄昏枝头被寒风摧残、摇摇欲落的颓败黄叶:“时至今日,我才真正佩服昭宪太后,杀母夺子的事情,瞒得这样滴水不露,七十余载的富贵荣华,直到四十五年后才被哀家发觉了蛛丝马迹。再看哀家,不过两年多,就东窗事发。”
“太后娘娘,并非是昭宪太后技高一筹,而是她心狠手辣,杀母夺子,做得干净利落,任何有所牵连之人,具是死无葬身之地。太后娘娘心软,虽然也有决断,但到底并未行株连杀戮之事。”竹息的叹息绵长若檐间风铃的低回婉转,“昭宪太后事破,是因为滥杀无辜,激起了仇恨;太后之所以东窗事发,是因为您不愿牵连太多的人,让那有心之人有了可乘之机。”
朱成璧微微一怔,眸中已有寒意凝聚:“那人是谁?”
“谁是摄政王的心腹,谁就有嫌疑,自然,宫里头的人,也不是没有可能。”
“你是说梁太医?”朱成璧有些许的迟疑,望向竹息道,“他会背叛哀家吗?”
“奴婢想着,大约是不会,他若是告密,自己就难以独善其身。”竹息忖度着道,“如今他与郑慕宁都在摄政王手里,摄政王之前远在漠北,又怎会留心到这些?必是梁府之事让人怀疑,这番顺藤摸瓜、才会查得这样清楚。”
朱成璧点一点头,随手拈过案上的一枚奶油芙蓉糕,孰料甫一入口,胃里就是一阵的翻江倒海,忙不迭地吐了出来,竹息忙奉上一盏安神茶,轻轻拍着朱宜修的背,疑惑道:“太后娘娘这是怎么了?可是哪里不舒服?”
朱成璧摇一摇头,正兀自思索着,忽而心头一震,转首紧紧握住竹息的手,低低道:“去请顾太医来,快去!”
顾太医静静诊着脉,面容沉静,朱成璧却明显感觉到他搭脉的手指微微一跳,不由紧紧按住了胸口。
“太后娘娘。”顾太医收回手,眸光微沉,平静道,“您有了三个多月的身孕了。”
朱成璧大惊,右手死死抓住茶案的边缘,一枚水葱样的指甲竟生生折断:“当真么?”
顾太医忙道:“微臣万万不敢欺瞒太后,只是太后有孕以来,似乎心气浮动、五内郁结,故而胎气十分虚弱,且今日胎象更为不安。”
朱成璧惊疑不定:“哀家常有服用紫茄花汤,按理说,是不会有孕的。”
顾太医心里有数,从容不迫道:“紫茄花汤是有避孕的功效,但并非是实打实的效用,恕微臣直言,太后娘娘自皇上即位以来,身体状况几是每况日下,更有紫茄花汤推波助澜,如果不加以调养,只怕此胎难保不说,也会让太后凤体受损。”
朱成璧有些发怔,只下意识护住小腹,须臾,目光从案上的绿松玉锤上划过,直直落在腕上的碧玉莲花镯子,低低道:“竭尽全力,保住哀家这个孩子,哀家能否翻身,全在这个孩子身上了。”
顾太医拱手道:“微臣定当尽心尽力!”
朱成璧细细打量着顾太医恭谨的神情:“梁太医曾跟哀家提过,你悟性甚高、可当大任,哀家便许诺你,若你能办好这件事,院判的位置,哀家便留给你。”
顾太医心里连连冷笑,只是不敢露出分毫,再度行叩拜大礼:“微臣谢太后娘娘恩典!必定谨而慎之,不负太后娘娘所托!”
夜幕低垂,月华似水,星光熹微,朱宜修一步一步,缓缓行走在永巷,一袭铁锈红折枝梅花披风将她牢牢罩住,掩住了隆起的肚子,看起来似乎只是宫里头寻常的女官,并不显眼。朱宜修身侧,剪秋亦是装扮简素,小心地提着琉璃宫灯,一壁扶着朱宜修,一壁引路。
永巷尽头,一个黑色的人影孑然伫立在那里,一动不动,仿若一尊雕像,朱宜修微一屈膝:轻启朱唇,“摄政王安好。”
奕渮徐徐转身,语调波澜不惊:“你真的来了。”
“摄政王许给本宫想要的,本宫就许给摄政王想得到的。”
奕渮微微一嗤,似有几分嘲弄的意味:“前番你我似乎还有冰火不容的时候,没想到现在倒是站到一起了。”
朱宜修面不改色,盈盈一笑:“从前是从前,现在是现在,本宫是愿意与摄政王合作,但是,合作也只是暂时的,你与我,到底并非是一条船上的人,说得好听点,不过是为了利益一拍而合罢了。”
奕渮点一点头,不欲多说,明快地问道:“那人是谁?”
朱宜修却不急,只淡淡一笑:“本宫先问一问摄政王,前朝的祝修仪能在封宫五年间活得好好的,是何人暗中相助?”
“沈太医沈一贯。”
“沈太医有个学生,不过并非是明着摆上台面的师生关系,那人如今是梁太医的学生,毒死凝脂、传信于钱小仪、散播流言的人就是他……”朱宜修望着奕渮微微蹙起的眉峰,一字一顿道,“顾太医顾九雷。”
奕渮惊诧不已,追问道:“这件事情梁太医可知情?”
朱宜修摇一摇头:“依本宫手里的线索,恐怕并不知情。但是,散播流言一事,只怕梁太医也撇不清关系。前番本宫宣召梁太医,侧敲旁击,的确发现一些端弥。不过本宫可以肯定的是,当年太后逼死祝修仪,让沈太医对太后深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