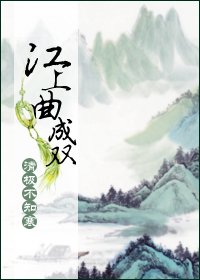僧尼成双-第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动u的大门,总觉得有一个条无形的线将她往后坠,越往前跑,那股后坠的力量就越大,她不敢回头,一旦回头,她也许会像昨晚那样失去理智的抱着然镜,不管是劫是缘,方才她说,他们最好的结果是沙场相见,胜者为王,败者暖床;
她有必胜的决心,但是没有必胜的把握,然镜也是如此。
阖上红叶庵厚重的大门,幽闲跌坐在冰冷的石阶上,然镜,你背我过了河,可是前面的那段路,我必须自己走。
然镜的视线先是被升起的迷雾阻隔,后来那扇大门彻底截断了幽闲的身影,他默然回寺,床榻之上,还留着昨晚的迷乱。
端起茶杯,不为解渴,只为品尝她唇间的香醇;
盖上棉被,不为驱寒,只为寻找她残余的芬芳;
阖上双目,不为睡眠,只为重温昨夜圆满缱绻;
昨晚,我们负了如来,其实也负了彼此。
昨晚,我们结尽同心之时,缘分已在不知觉中溜走。
缘起即灭,
缘生已空。
☆、花火
秋风秋雨的黄昏,不定会愁煞人,换个角度想想,其实也是挺和睦的天气,在这种天气,你觉得最惬意的事情是什么?
有家的,吃着火锅唱着歌,抱着老婆逗着娃。
单身的,抓一把瓜子闲磕,看着暖茶氤氲的热气散开,再看一眼窗外行色匆匆的过客,一股莫名的满足会陪伴你整个夜晚。
出家的,煮一壶清茶,讲经谈禅。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十方和尚晃着脑袋,视线不知不觉的飘向窗外。
无疏师太曲中指,叩了叩柔软的松木桌面,“十方,你上一句话说的是什么?”
“哦?□□,空即是色,因空见色,由色悟空。”十方和尚老老实实移回视线,端坐在蒲团上,比佛像还要庄严。
“恕无疏愚钝,您上一句还念着般若波罗密多心经‘由色悟空’,下一句接着‘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是什么意思?”无疏依旧波澜不惊,可言辞下已有不满。
咳咳,十方尴尬的顿了顿,见红泥小炉上的泉水已沸,于是解脱般提起陶壶冲上一壶花果茶,这是他今天登门送的礼物,无疏师太向来脾胃不好,这花果茶对她再适合不过了。
待白瓷壶里的汤色渐浓,十方又加进去四颗冰糖,摇了摇壶身,见冰糖消融在花果茶水里,这才倒进无疏面前的茶杯里。
茶水成线,欢快的聚集在杯中。
待腾起的热气模糊了视线,无疏的眼神显得并不那么凌厉了,十方才嗫嚅道:“这个嘛……我听说你把幽闲关在屋子里三天三夜了,还不准送饭送水,这孩子还小,做错事略示惩戒即可,今天
晚饭,就放她出来吧。”
“十方,你果然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无疏放下手中佛珠,端起花果茶轻抿了一小口,眉头往上抬了抬。
“咦,是不是觉得有些酸?再放一块冰糖可好。”十方殷勤的拿起糖罐。
无疏不置可否,十方挑了块最大的冰糖加上,这块糖在茶杯里一时消融不了,在亮红色茶水里,灿若水晶。
“不管你信不信,我并没有把幽闲关在房里——是她自己不出来。更可况,如今我已经没有本事关住她了。”无疏轻叹一声,“她和然镜的事情,我没打算管,我自己失去的东西,为什么要逼着别人也得不到?在你眼里,无疏就这样的人吗?”
“不,不,不。”十方脖子蓦地一紧,接着连连摇头,“我们相识那么久,我相信你的,还不是因为我那个倒霉徒弟然镜嘛,幽闲三天三夜没出来,然镜表面上没有什么变化,可实际上,唉,我都能听到他内心长吁短叹,实在挂念的紧;这个别扭孩子自己又没有过来找幽闲的意思,我这个做师傅只好自作主张来这里探消息,回去也好交差,求求无疏师太您开恩,让我见幽闲一面,红叶寺的石墙都快被那小子的叹气给叹塌了!”
无疏师太哭笑不得,初见十方时,他还是个耿直木讷的军人,没想到出家做了和尚,却改了性情,油嘴滑舌的胜过市井商贩。
“你要见她,自己敲门就是,她翅膀早就硬了,我红叶痷都要看她的脸色行事,前日我一气之下,逐她下山,并不是因为她和然镜破了色戒,而是,看看这个,你就明白了。”无疏师太从满案经书里抽出一本半旧的无量寿经递给十方。
十方疑惑的接过,翻开一看,却是一本账册,越往后翻,脸色越发沉重,直到翻过最后一页,他将账册还给无疏,不自然的谄笑道:“恭喜师太,你们红叶痷的产业至少能卖下一座城池了。”
无疏师太蹙眉,“这些只是幽闲手中财富的一部分而已,她十二三岁就独自在云游,做了什么事情从来不对我讲,后来掺和进来一个商人顾念久,她就跟个野人似的在外跑,在红叶庵呆不了几天。”
“孩子翅膀硬了也好,自己能飞,你终究不能护住她一辈子。”十方安慰道,“她是个知恩图报的好孩子,赚了钱也知道放在红叶庵名下一部分。”
“知恩图报?”无疏师太笑了,笑声中带着苦涩,“幽闲从未给过红叶庵一个铜子,她打着红叶庵的名义,只不过是为了避赋税罢了,过不了多久,这些产业会神不知鬼不觉的被转走。”
“六合各国律法,寺庙的产业都是免税赋,幽闲这番瞒天过海的手段,贫僧佩服。”十方呵呵笑,“贫僧也佩服无疏你,她捂得再严实,不也是被你觉察到了么?”
“是她自己出了些纰漏,需要我帮忙打点关系,这才坦白实情的。”无疏将花果茶一饮而尽,忿忿道,“我不想再提她了,你有话自己去问她。”
“好说,好说。”十方慌忙站起身来辞行,走到门口,又回转过来,给无疏续上一杯花果茶,来回搓了搓手,欲再搭上几句话,见无疏双目微阖,右手支颊,神情疲惫,只好将话又吞了回去。
走了几步,又滞了脚步,回来往火盆里添上几块木炭,站起来,脚刚跨出去一半,又收回来,蹲下,拿起火钳拨旺了火,鼓着腮帮子吹火星儿。
“你怎么还没走?”无疏师太不耐烦的睁开眼睛,冷冷的瞅着十方。
啪嗒!
“对——对不起,吵到你了。”十方和尚受惊,手中火钳掉进火盆,溅起的火星仿若绽放的焰火,这烟火显然没长眼神,迸到了无疏垂下的衣袍上。
“你——没烧到你吧!”
十方扑灭无疏袍角的火星,顿时“花容失色”!
“你——你走开!”无疏急忙推开十方的手,“这里没你什么事了。”
“哇!”十方惨叫。
“糟糕!”无疏惊叫。
十方缩回手脚,动作过急,没站稳,一个踉跄绊倒了火盆,宽大的棉袍顿时着了火!
他在地上很没形象的打了好几个滚,无疏师太提起半开的热水往他身上浇,火苗终被扑灭。
可是地上散落的木炭已经将经书和杂物点燃了,这些天一直阴雨绵绵,都有些潮湿,所以火苗夹杂着浓烟到处肆虐,十方可怜兮兮直道对不起。
“来人啦!主持禅房着火啦!”
提着一瓦罐泉水的无寐师太回来了,招呼几个小尼姑过来救火。
无疏将十方推开,“你赶紧走,别在这里帮倒忙!”
被人嫌弃的滋味真难受啊!十方从窗户里跳出去——真是丢人丢大发了。
……
咚咚咚,门在响。
幽闲先是将门开了一条缝,看到面黑衣破的十方和尚,愣了:
“十方大师,您被人给烤了?”
十方窜进屋内,健硕的身体比猴子还灵活,扯了手巾浸上水擦脸,无奈他的脸皮比宣纸吸墨,面皮都搓红了,那烟熏色只是减退了半分。
幽闲蹲在一旁看热闹,“不要再擦了,这个颜色很好看嘛——和刚出炉的烧鹅一个样,令人馋涎欲滴。”
十方不理她,蘸了些皂角,继续蹭,像蜕皮的蛇。
幽闲捂嘴,窃笑,“您等着晚上再回寺吧——反正天黑别人也看不清楚。”
一盏茶过后,十方和尚红光满面——蹭的!
幽闲同情的抓了把干果,塞给十方,“大师,您慢用。”
几颗花生,一杯冷茶下肚,十方和尚尴尬之色渐褪,他看着面前嬉笑的幽闲,纳闷:这哪里像“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模样啊!脸颊比前几日还圆润了些,分明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样子嘛!
“我听说你三天三夜没出门,无疏主持也没派人给你送饭。”十方诧异,“莫非你这些天吃的是蟑螂老鼠?”
“非也,非也。”幽闲将地上的红漆食盒提上来,“这是奶娘炖的酱牛肉和猪蹄,我连吃了三天,好油腻,真想吃顿斋菜哦。”
十方很后悔:担心幽闲挨饿,不如担心母猪上树;他屁颠颠的来红叶庵探消息,烧了无疏的禅房,丢了脸,被小尼姑耻笑,最后,还……还被肉食引诱,真是倒霉。
为了慰藉自己受伤的灵魂和烧坏的新棉袍,十方和尚做了个艰难的决定:吃肉!
十方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他带走了一个猪蹄。
再挥一挥衣袖,带走了半斤酱牛肉。
扫荡完幽闲的残羹剩饭,十方满足的砸吧砸吧嘴,转身就要离开。
“喂!你找我是要干嘛?”幽闲叫住了十方。
“没大没小,喂也是你叫的吗?”十方拧起幽闲的耳朵。
“师傅,十方师傅。”幽闲赶紧改口,呲牙咧嘴,“喂只容许无疏师太一个人叫!您老慢点拧——小心伤了您老的手哇!”
十方放下“屠手”,立地成佛,他敲了敲幽闲的光头,感叹道,“然镜这傻孩子到底看中你什么?你躲在房里三天,就没担心然镜怎么样了?”
幽闲嬉皮笑脸,抓耳挠腮,“十方师傅,请您高抬贵手,别敲我的头哇,敲坏我的头,最多碗大个疤,抹点药膏就行,万一伤了您的手,无疏师太会让我永不超生的呀!”
☆、凶案
天色已暝,钟声唱晚。
“我走了啊,你确定没有什么要说的吗?”
十方和尚一步三回头,第四次问幽闲。
幽闲摆摆手,赶苍蝇似的,“没有,您回去吧。”
“你没什么话带给然镜?”十方很失望,想到然镜一副“纵我不往,子宁不来;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苦兮兮怨妇的模样,又软了心肠,再次问幽闲。
冤孽,冤孽啊,当年小幽闲还在红叶寺当小和尚的时候,她天天抱着木鱼跟着然镜,然镜打坐念经,她趴在蒲团上玩蚂蚱,打苍蝇,玩着玩着,就枕着木鱼,猫儿似的蜷在蒲团上睡着了,口水滴答在佛珠上,连成丝,扯成线,一弹一弹的,就是掉不下来,眼瞧着就要碰到地面,却嗖的一下又粘回去了。
那个时候,幽闲和然镜的关系,就像口水和佛珠;然镜经常找机会甩开幽闲,藏来藏去,蓦然回首,幽闲却在,灯火阑珊处,抱着木鱼嘿嘿笑,“然镜,师傅叫你回去吃饭啦。”
而如今,变成幽闲躲着然镜了,令十方和尚折腕长叹: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百思不得其解啊!
“唔,十方师傅,你就说,幽闲未老,尚能食饭。”幽闲瞧着十方那副模样,知道不说点什么,休想送这尊“佛”离开。
“好,好。”十方乐颠颠的打开房门,刚迈出门槛,又扶着门框回首说道,“有空来红叶寺谈禅,我亲自下厨做罗汉斋。”
“知道了。”幽闲阖上房门,这一招又急又快,十方脑袋没来得及缩回去,鼻头和门框来了个热吻,他鼻梁本来就扁平,用幽闲的话来说,就是“像塌方的煤矿似的”,这下撞得更塌了,还红红的,配合脸上没擦干净的烟灰,烧焦的僧袍,十方和尚的样子可以直接去戏台上唱丑角,还不用化妆的。
乒乒乓!
僧敲月下门。
十方捂着鼻子大呼,“幽闲!你这倒霉孩子,贫僧快破相了!”
幽闲不堪其扰,打开房门,愣了愣,“咦,无疏师太,您……。”
啊!
十方捂着脸狼狈而逃。
“嘿嘿,这么不经吓,杯弓蛇影,无疏师太才懒得来我这里呢。”幽闲望着十方飞逝的背影,摇了摇头。
关门回屋,没有十方的聒噪,屋内顿时冷清下来,幽闲跳上床,扯过被子蒙头大睡,被窝已经凉了下来,又隔着几层衣服,良久都没暖和过来,幽闲冻得缩成一团,思绪却纷乱芜杂,似冬日初雪;那夜的床帷,暖得直冒汗呢,他的手真烫,所到之处……。
乒乒乓!
没有眼色的敲门声,打断了幽闲的一帘“幽梦”。
她蒙上被子当乌龟,艰难的继续回味,可敲门声犹如滔滔江水,绵绵不绝,又如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坚决的扼杀幽闲最后的痴想。
“十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