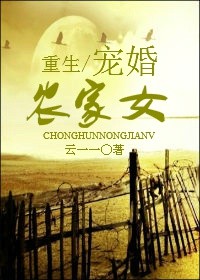二流小说家-第1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35
摘自J·杜克·约翰逊所著《两点两瞪眼》第一章:
“莫尔德凯·琼斯?有意思,你不像犹太人。”
她淘气地笑着走进我的办公室。我听过这个笑话。我身高六英尺二英寸,心情好的时候体重两百磅,心情好不好皮肤都是深棕色。今天?还很难说,得看一个身材火辣、眼睛冰蓝的俏皮金发小妞说清楚她要什么了。
“我母亲是埃塞俄比亚犹太人,”我解释道,“犹太教的传统是母系传递,所以从原则上说我确实是犹太人。”我伸出手,“但我并不严格遵守教规。您是……”
“雪莉·布雷泽,我在玩家夜总会跳舞。酒保豪尔赫向我介绍了你。”她抖出一根万宝路特醇100,我觉得这根烟揭示了自相矛盾的性格,“我想请你找个失踪的人。我老爸。朱尼帕·布雷泽。”她在手包里翻找打火机。
“你最后一次见到他是什么时候?”我取出火柴。
“十年前。”她说。
我隔着桌子给她点火。“不容易,但有可能。”我说,“他当时在哪儿?”
她看着我的眼睛,噘起红唇吐烟:“他的棺材里。”
来到高低酒吧,两杯过后(她喝柠檬威士忌,我喝芝华士浇冰块),雪莉·布雷泽努力说明情况。现在很清楚了,这姑娘要么是疯子,要么在撒谎——也可能说的是实话,但如果是这样,我一定是发疯了才会去掺和。
她老爸是个吹小号的,朱尼帕·“白皮”布雷泽,绰号来自吹奏的音色和他的肤色,五六十年代他这个白人混爵士圈也算一景。据说他技巧高超,高音能点中你心窝深处最柔软的部位,但到雪莉降生时,那种好日子早就是历史了。这会儿的老爸是条毒虫,在廉价酒馆卖艺,拎着个手提箱养活小雪莉。在四十二街你成长得很快,她十八岁那年,老爸一针下去过量而死,雪莉没有哭泣,而是跳上舞台。如今她二十八岁,看上去还相当不赖——只要你别看她的眼睛,就像我此刻这样。
“咱们别兜圈子了,”我又帮她点了一根特醇100,“为什么来找我?”
“我梦到了他。”
“梦?”我混日子时听过很多故事,夜里听到的就更多了,但这个还是头一遭。我笑道:“好吧,我认输,说来听听。”我又叫了一轮酒。
她没有笑,也没有生气。她慢慢喝酒,慢慢抽烟。她看着我的眼睛,开始讲述:
“大约一个月前,我做了这个梦,我父亲在我的房间里演奏一首曲子。《再见了平顶帽》,他最喜欢的曲子。但在梦里他不是用小号演奏的,声音确实是小号的声音,但是从他的嘴唇里发出来的,他噘起嘴唇像是要亲吻谁。总而言之,梦里他抓着我的手,领着我走进壁橱,就是我现在家里的壁橱,但里面是一条长长的走廊,出去是我们以前在时代广场住的旅馆房间。他兴奋起来,演奏得越来越狂野和高亢,指着床底下要我看。最后我低头去看,床底下是他以前放小号的手提箱,里面满满都是鲜血。老爸开始尖叫,小号吹出的那种尖叫。我把手伸到血泊里,摸到一把匕首,然后就惊醒了。”
“吓人。”我承认道,“我昨晚也做了一个疯狂的梦。我奶奶骑着大象走在百老汇大道上。每次我半夜吃大力水手炸鸡就会做这种梦。”
“我明白,”她赶开烟雾,“人人都做怪梦,所以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我一次次做这个梦。我发现自己在哼那首曲子。我没法从脑海里赶走那个旋律。洗澡的时候,坐地铁的时候,工作的时候。快要逼疯我了。”
“你确实遇到问题了,但我还是认为你需要的不是侦探,而是去海滩休息一个星期。”
“我也这么想过。”
“那就好。”我掏钱包。
“直到我老爸开始给我发电子邮件。”
“什么?”我的耳朵终于抖了一抖,鼻孔张开,像是猎犬闻到了新鲜的气味。
“对,信都很短,全是只有他知道的事情。豪生饭店他演出结束后我们吃热奶糖圣代,他典当小号给我买校服鞋子,我会跳舞但不会唱歌。”她喝完那杯酒,“你怎么看?我需要的是不是侦探?”
我从她的烟盒里取了一支烟,剥掉过滤嘴,说:“你认为侦探应该从哪儿开始找?”
她拿起火柴帮我点烟,说:“当然是墓地了。”
36
再一次见到达利安·克雷那天,天气凉爽晴朗。你能看得很远,连最遥远的山脊上的树木都清晰可辨。会见室里当然不存在天气,时间也永远不变:单调的日光灯下,说是正午或者子夜都行。我坐进固定小桌前的固定座椅。水泥地面刚清洁过,松香味很刺鼻。
“很好,非常好!”克雷笑嘻嘻地评论我写的玛丽·方丹的故事,“你捕捉到了她的性格。尤其是那些小细节。比方说我给她烙印时,她使劲咬住马嚼子。”
“谢谢。”我被恭维得很不安,然后打了个喷嚏。
“上帝保佑,”克雷说,“这个季节必须当心。我每天吃维生素。”
“我没事,谢谢关心。”
他向后靠,若有所思地摸着下巴。他没刮脸,胡茬和我一样有黑有白。“玛丽是个小胖子,对吧?”
“不是。”我耸耸肩,“好吧,稍微有点肥。”
“我并不介意。”
“不,她很可爱……”我附和道,在脑海里又看见她,听见她的假笑。我翻看笔记,像是要隐藏关于她的记忆。我开始录音。“那么,你说你想谈谈念书时的事情?”
“哎呀,艺术学校,但我没去。”
“为什么?”
他哧哧地笑道:“被他们拒绝了呗,就是为了这个。谁知道否则我会成什么样呢?著名艺术家也有可能。”
“有道理。好吧,咱们谈谈这个。你怎么会开始从事艺术?你是什么时候开始知道自己想当摄影师的?”
“来,我告诉你。是在我的寄养母亲家,格雷琴夫人。我恨她。”他伸展双腿,融入故事,露出监狱拖鞋里厚实的白色运动袜。“真正的老婊子。喜欢用汽车天线抽我。抽大腿,疼得要命。她应该蹲监狱,而不是坐在老房子里看电视。她的男朋友喜欢扒光我的衣服,用冷水给我冲澡,然后把我光着身子扔到门廊上让邻居看。为了羞辱我。”
“为什么?”
“尿床。”他亲切地说,看着我的眼睛。
“好,好吧。”
“但他有一台照相机,明白吗?旧尼康。他拍了很多日常事物。她在院子里。他的车。松鼠之类的。树叶。他把照相机放在三脚架上,允许我看取景器,但绝对不许碰快门,免得浪费胶卷。于是我背着手,在脑袋里假装拍照。”他笑着举起戴着手铐的双手模仿照相机,用咬掉指甲的手指框住面孔,“咔嚓。捕捉这个时刻。咔嚓。”
他顿了顿,我按捺住插嘴的冲动,我参加餐会遇到尴尬的沉默时总喜欢乱说话。克雷交织手指,将双手叠放在大腿上,继续说道:
“他在地下室有一间暗房,允许我帮他打下手。他不在的时候我偶尔也溜进去。我喜欢化学药品和地下的泥土气味。暗房很小很黑。谁知道呢,我反而感觉很安全。我喜欢看着照片在显影水里慢慢浮现,就仿佛水下的生命渐渐活过来。总之,”他向后一靠,跷起腿,“我迫不及待地想拥有自己的照相机。我攒起每一毛钱,到处打工,偷零钱。最后我总算买了台二手佳能。那年我十五岁。我兴奋极了。相机漏光很严重,每次上好胶卷就得用胶布贴住,但这有什么啊,我是摄影师了。可是我还是只能假装拍照,因为买不起胶卷。”
你能在磁带上听见我和他哈哈大笑。
“再后来,”他说,“我开始真的拍照,拍了很多东西。天知道都去了哪儿。估计现在能值几个钱的。收藏家会感兴趣。”
“什么样的东西?”
“一切。树木、狗、其他孩子、邻居。我带着相机到处跑,摸爬滚打像童子军似的。学会保持耐心。你明白的。等待。拍照的要诀。就像猎人。等待你在寻找的东西自己露面。”他向前俯身,双手比画成一杆长枪,顺着大拇指瞄准我。我微笑。
“但你大部分时候拍的是模特,对吧?我指的是摆拍。”
“一样的,完全是一样的。这是你和被摄物之间的关系。等待,说服,诱骗,观察,等待你需要的东西浮现出来。那种不可言传的东西。这是最困难的部分。”
“等待?”
“对。等待,还有让被摄物保持静止。”他哧哧地笑了两声,开始啃手指。我拔出钢笔,在笔记簿上打了个毫无意义的勾。
“你是什么时候决定以此为业的?”我问。
他吐掉舌头上看不见的什么东西,耸耸肩说:“就在我知道我是这块料的时候吧。刚开始我想做新闻摄影,你明白的,例如战争、火灾之类。比方说驻外通讯记者。逃离这儿。后来我发现,嘿,杂志社也需要人拍照,哈。还有海报、公告牌,等等。到处都有照片和拍照的人,对吧?”
“但你想拍的是艺术摄影。”
“对,我跟过一个老师。巴恩斯沃思先生。他借书给我——妈的,其实是图书馆的书——但总而言之,他看见我抱着相机在学校附近的野地里乱转,就拿了几本书给我:斯蒂格里茨、布拉塞、沃克尔·埃文斯、黛安·阿勃斯——我最爱的就是她。这时候我意识到,摄影师也可以是画家一样的艺术家。他可以创造画面。表达但不仅仅记录。可以创造符合他意识的画面。”他重新放慢速度,眼睛跟着我上方半空中的什么念头。小小的火花,塑料灯具的反光,在他眼里移动。
“于是你申请就读艺术学校。”我提示道。
“对,申请了一堆学校。”他似乎第一次露出恼怒的神情。他举起双手挥舞,铁链擦过头顶。“他们不要我。石头缝里蹦出来的穷孩子。烂学历,烂成绩,所以我不可能拿到奖学金。明白吗?我哪儿也去不了。总之,艺术学校就是这么回事。给有钱人装逼的地方。谁他妈需要呢?但他们有他们的体系,明白吗?你必须念艺校,进入画廊,学习怎么谈论那些狗屁。扯淡,他们学的就是这个。”
“但你学过课程?”
“对,在社区中心,老师是个混球。据说是个职业艺术摄影家。在巴尔的摩办过两次展览,了不起。他说我不成熟,好像我弱智还是怎么的。说我需要调和,好像我是一碗汤似的。然后我就自己干自己的了。艺术不就是这样吗?谁说了算?谁能下判断?只有未来。也许一百年以后,我的作品会挂在博物馆里。也许价值连城。妈的,他们说艺术家死了作品就会值钱。谁知道呢?也许等我们死后,你写木乃伊和火星精灵的书也能卖个一百万本。”
他轻声自顾自地笑了一会儿,然后陷入沉默。我再次管住自己的舌头。闭嘴,我命令自己,听他怎么说。
“艺术还是什么?”他最后说,“复仇。哈。还有正义。照片就像证据。就像留给未来的瓶中信。我在梦里见到但要很久以后才能实现的东西。我对此有信心。我不怕死。我知道我的作品会继续存在,一百年,两百年。你会永远活在其他人的心中。还有被你触碰过的所有人。我不需要宗教和其他人的上帝。艺术就是我的天堂。”
37
回到家,公寓空无一人。克莱尔的母亲在去棕榈泉和欧洲购物的间隙短暂停留纽约,克莱尔必须去见她,维持“家族束缚”。于是我去主大道的北京烤鸭店排队,轮到我的时候用手势和窗口的店员交流。蒙着蒸汽的玻璃里,一个戴着厨师帽的男人将金黄色的烤鸭放在砧板上,用切肉刀剁成闪闪发亮的碎块。另一个人把碎肉塞进面饼的开口,加上黄瓜和大葱,涂上一抹黄酱。我在单身食客的长桌前坐下,对面的中年男人身穿油漆点点的连体工作服,旁边的年轻女人身穿医院工作服和雨衣,我们盯着彼此之间的空位咀嚼。说话的人都只说中文。语言不通真是让我松了一口气。
吃过饭我回到家,浏览电子邮件、普通邮件、语音邮件和《纽约时报》。我冲个澡,剪指甲,用棉签掏耳朵。我再也控制不住好奇心,于是打开互联网。我像蜘蛛似的守在网络一角,默默观察血族T3。这算是赛博跟踪还是只是赛博潜水?藏起来等待一个女人——不,仅仅只是一个化名,一个也许是也许不是特蕾莎·特雷奥的小光点,我在自己面前感到羞愧。这是新的下限,不但变态而且可怜。变怜!
血族T3:嘿……
猩红1:嗨。
血族T3:最近可好?
猩红1:挺好。你呢?
血族T3:挺好。我还是不敢相信,我居然真的在和你聊天,西碧莱恩!
猩红1:我也是。我是说,我也不敢相信。
血族T3:你不敢相信你在和我聊天?
猩红1:我指的是我通常不和粉丝聊天,并没有特别在说你。
血族T3:但我是你的粉丝啊。lol。猩红1:lol?棒棒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