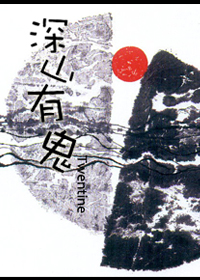山有木兮木有枝-第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在步下马车的须臾间,敷儿顺着宫灯所映的光影,轻轻环顾自己周遭的方位。
两旁的街市,干净而整洁,足有四架马车并行的宽度,沿着视线所及之处再轻轻望去,正好望见对面一座府邸。不过相距五十步,虽不是迎面而对,两家也算是隔街而建。正门之上,一块长形匾额,清晰书着两个醒目的大字:方府。
我不禁驻足,兀自望着那两个端丽浑厚的笔触出神,敷儿似在哪里见过这块匾额?
一旁的云英上前数步,小声提醒着:“秦姑娘,时辰已不早,请早些入府安置。”
她话音未落,远处,即传来几下更鼓遥响,不容我再耽搁,两旁的护卫已齐齐向我施礼,催促我移步。
敷儿无奈,只得随着他们踽踽行入,丝履刚迈入十数步,只听身后是落锁的声响。
其中一名领头的护卫随即向我躬身施礼道:“回姑娘,燕王殿下有令,姑娘既进得这宅院,就出不得!”
高挑的宫灯旖旎,照出我足下的方寸之地,我盯着他,心知此事与他无关,却,始终说不出片语只言。
什么叫既进得这宅院,就出不得?!
他是要将我软禁在此么?从此,果真不见天日?
那名将领再道:“末将莫尘,奉燕王殿下之令,和诸位弟兄一齐负责保护姑娘安全,不到之处,还请姑娘恕罪。”
罗敷何尝不知,此语虽是请罪,实是警示?
意即——自此之后,这阖府之中,我一言一行莫不受其监管,而他所奉的,不过是上峰的意思,他们都不过是按差办事。
见我不答,他再道:“这位是何凤,末将不在之时,由他代为执事。”原来连副职都已一并安排妥当。
那何凤上前一步,向我躬身再施一礼,高声道:“末将何凤,见过秦姑娘。”
莫尘再指着云英身后的一位髯须长者道:“这位是府中的管家丁宥德,末将人等只负责护卫,其余饮食起居,俱由他全权打理。
那位老者闻言,率着足有二十位不止的佣仆一齐向我行礼道:“……见过姑娘。”
我只是轻轻屈膝还礼,却,仍未出言。
此刻,敷儿口拙只是借口,我算是哪门子姑娘,不过是寄人篱下的布衣草芥,如今更被他禁了足,等于是幽禁于此。
原来,他原意即是如此。
怪不得他临别前,敷儿问他何时归来,他只但笑不语。
我侧过小脸,只望着天际那一轮圆月,默然。
素颜之上,既无泪,也无凄怆之色。
既来之,则安之,走到这一步,再追悔已于事无补。
先生说得好,敷儿能留下一条贱命,已是天可怜见,这一生,等于是偷来,所谓苟且偷生之人,岂能再有埋怨?
此刻,万般一切,诸已由不得我喜也好悲也罢。
我垂下眼睫,兀自在前走去,也不管他们这些人,只向着自己面前那重重的庭院行去。
一连数日,我都不曾再说过一个字。
我与这些人,原本就素昧平生,敷儿,在这世上,已无亲人。
每日,有饭有菜,且,菜式可算得清淡可口,精而又精。连敷儿的衣裳,也全是上好的绫罗绸缎制成,清一色的绿,只深浅不一而已。甚至,连足下的丝履,也左右不过是这些颜色。
每日,除了一日三餐,都有云英另为我奉上汤药。
我并不推辞,她给我,我就喝。
一连服了半月有余,敷儿的身体竟一日不如一日,每一日,只觉得步履虚浮,面色日益苍白,后脑处,更隐隐传出钝痛,似是旧伤复发之状。
据先生当日讲,敷儿初到云落院之时,后脑本就有伤,一连服了数月汤药之后,瘀肿才渐渐散去,随之疼痛也稍稍缓解。
如今看来,这份旧疾却随着敷儿的沉寂,再度袭来,且,一日比一日甚,一日比一日难耐。
云英见我形容不对,又不肯出言,遂,向这府中的管家丁宥德禀报。老管家并不敢怠慢,连夜为我请来了大夫,诊了脉,重新开了方子,换下了先前的那一副。
就这样又过了两月有余,敷儿,虽来这院中日久,却始终不曾再说过一句话。
天气,渐渐闷热,又是一轮明月高挂长空。
晚风习习,却吹不去这湿热。
云英领着一名小丫鬟进入,示意她将盘中之物奉于我。我随意看去,原来是我当日遗落在燕王府的翠玉长笛。
我认得她叫灵儿,云英曾当着我的面唤她,我半靠在软榻之上,兀自不动不言。
云英等了片刻,见我犹不动,遂,亲自拾了,交予我手中。一面轻道:“姑娘,奴婢前日见这府中有一高处,上建有凉亭,正好可以让姑娘吹这笛子,奴婢领姑娘前去可好?”
我接过,手指轻轻摩挲过每一只笛孔,直至此时,我仍没有一滴热泪。
敷儿的泪痕自进得这宅院,就干了。
我并不搭腔,只从这软榻之上起身,独自走出房中。
屋外,果真是月色如水,树影婆娑,宛如当日一别,历历在目。
只是景犹似,物是,人非。
我执了笛子一路缓行,虽换了一副药方,不适之感比之先前要好过许多,但,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身子日渐虚弱之后,怎可能一时间就恢复如初?不过才行了半盏茶工夫,我便已虚汗淋漓,如此气息,可还能吹得响这玉笛?
再往前行了数十步,果然看见那一处凉亭,正位于一座缓坡之上,有数十级台阶通往。云英赶紧上前几步,扶住我的身子。
借着她的臂力,敷儿勉强才攀到亭内,只见四周空寂无人,万籁俱静。只有隔壁人家的灯火,隔了一道迤逦的院墙,弱弱映入彼处。
云英说的极对,确实是一处极佳的处所。
我将玉笛轻轻置于唇边,素手轻移,再一次,吹起那阙《越人歌》,那一阙由敷儿自个所谱的曲调。
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
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
……
月轮年年相似,此刻,浩淼的洞庭水上,应也是同此皎皎月色。
击桨而歌的越女,你何其有幸?能够得遇心内所喜,再为他所喜。
笛音,只比这月色还清淡,更比那清风还婉转数寸,于这静夜中,绕过那繁茂的碧树,盖过那幽怨的蝉鸣,直沁入人心去。
但,即便它再悠远袭人又怎样?即便它能绕梁三日又如何?可惜,它飞不过离恨天长,越不过沧海水阔,也是徒然。
敷儿,当然有泪,敷儿,当然会有怨。
既然不能落泪,也不可埋怨,就让满腔的女儿心事,不过随着素手之上的一支玉笛,直飞入洞庭。
我一连吹了两遍,才因着胸口的急促而停下。
我扶着廊柱,望着那熠熠的灯火,想必能够住在彼处的,都是大户人家,非富即贵。是谁入夜竟不曾歇下,那烛火如此温暖如此执拗,晕染了漆黑的夜空。
我站得有些累了,云英见我脚步不支,赶紧上前几步扶着我,送我回房。
接下来,一连数日,我每夜必至这听风亭,每夜,必是戌时整,用手中的玉笛划破这寂寥的暗夜,洒下曲凉如水。
到第七夜,笛音刚刚暂歇,其实是敷儿的身体尚未恢复,已经不能连续吹奏数支曲子,才奏到第二遍,体力已是不济。
我只得暂倚着那廊柱喘息。
就在这四下无人的寂静中,忽闻一把陌生的男声,于墙外蓦然响起,声线朗朗,清越异常。
“在下蔡文澜,拜见墙内高人。君之笛音,清澈如水,意境高远,令听者,无不潸然。在下已经一连数日难寐,每每叹服倾慕不已。今日斗胆求见,虽冒昧,实是心之所致,还望君施教!”
我不答,只默然听着,原来,一连数日,敷儿的笛音并非没有知音,知音,竟然近在咫尺墙外。
听他的声音,年纪并不甚老,应该不过三十多岁去。只是,男女有别,敷儿又失语,不应也罢。
我扶着云英的手臂才要走,却听墙外人又道:“高人莫要怪罪在下唐突,文澜,字应海,虽只是宫内一位籍籍无名的官修史记,却也算得略通音律。高人,若不嫌弃,在下愿与君以文会友,以音传信,做一对相逢对面不相识的伯牙与子期,不知君以为如何?”
我忽然间止住丝履,原来,他是一位官修的史官?
我轻轻挣开云英的手,转回身,扬声应道:“奴家,秦氏,愿与官修,以物易物,以笛易物!”不知哪里来一股神奇的气力,竟让平日词不达意的罗敷,勉强说出了心意。
我话音刚落,墙外似传来一声喟叹。只听那位史官高声叹道:“想不到奏笛之人,竟是一位佳人,应海着实唐突了!”
我咬牙道:“不碍!”
他的声音中立刻透出一丝惊喜:“果真?”
“是。”
他含着恭谨又再接腔道:“好,姑娘既不拘泥,应海欣然受之!”声音之中,并无半点狎昵轻浮之意,听来,确实似一位难得的真君子。
他沉声再问:“应海一连受了姑娘数日的琴音,不知,秦姑娘有何赐教?请但讲无妨,在下定不辞领教!”
闻听他如此说,我看一眼云英,她默然而立,眼中并无丝毫动容。即便她此刻有动容,我也不会应之。
我即刻接道:“奴家,愿以,笛音,交换——”我一阵喘息,几乎说不出下面的字句。
他朗声问道:“姑娘欲与应海交换何物?”
我挣扎着再道:“史记。”
“史记?”
“官修的……史记。”
“不知姑娘何意?”
“我,只要燕王……史记。”
他登时沉默不语,良久才道:“姑娘因何独要燕王之史记?”
我吸一口气,应声道:“奴家……有正用。”
短短数字,他信我便是信我,不信,便是不信。此事,事关天家,而他即便真是一位籍籍无名的史官,所书所著,一字一句,也将永载史册。
敷儿,虽身无长物,如今,更仅剩这笛音,但,文如其人,乐也如其人,自古而如是。如果,他果真是位真君子,自会懂得其中真意,如果,他果真是敷儿的子期,自当信我无疑。
果然,不过停顿了片刻,他的声线随之再次响起,这一次,是满满的肯定和郑重之意。
“好,应海今夜便与姑娘相约,以文换曲,成就一段千古佳话。但,姑娘须许诺应海一桩事!”
“官修,请讲。”
“应海给予姑娘的每一个字,姑娘读过,必将其焚毁。应海只此一项请求,姑娘应便是应,不应,也恕应海万难从命!”
我当然明白,他将官史交予我传阅,他此身所担的干系,自是极大。我再吸一口气,强撑着高声允道:“奴家,应允。”
他随即应道:“好。姑娘今日想要燕王何时之史记?”
我沉吟片刻,轻道:“四月,至今。”
“好!明日戌时,姑娘请准时于此处恭候应海,届时,应海必将姑娘所需奉上。
我一个趔趄,想不到得来竟全不费功夫,一颗心在胸腔内,只如声声重鼓击下,我咬紧自己的唇瓣,不再吭声。
一双眼睛,只死死望着云英,如今,只剩下她一个障碍。如果她能容得下敷儿这最后一点生趣,敷儿虽死而无憾,如若她不许,再向上逐级禀呈,则敷儿所有的期盼,便要付之流水。
云英被我望着,直隔了有良久,才轻轻颔首,轻道:“姑娘放心,云英虽是殿下差遣,但,云英也是女儿家。”
“姑娘也放心,殿下临行前只交待不许姑娘出这宅院,其余,姑娘皆可自夺,即便是莫尘与管家,均不会相拦。”
她一言既出,我虽侧过小脸,泪水,终是落下,隔了数月之久,才缓缓自腮边盈落。
她向我再福一福,未再多言一字,只上前几步,扶着我,步下凉亭,向着敷儿所寄居的庭院行去。
敷儿并未向那墙外之人辞行,既是一对相逢不相识的伯牙与子期,便,无需拘泥于这些俗碍。
翌日,戌时刚过,我的笛音,便于这听风亭内如期响起,一声声,若生出蝉翼般透明的羽翼,向着那高处飞越。
才奏了半阙,忽闻一声清晰的声响,分明是有物事自墙外被人掷入,再坠落于地之音。云英未待我出言,自是步下台阶,走至墙角去捡拾。
等到她重又登入亭内,我的笛音并未停下,视线触及她所握之物,果真,是一只小小的卷轴,不过女子的手掌长短,以青色的丝绦束着。
墙外,再无其他多余声响传来。
我直等到吹完了最后一个音,才走至廊下所系的宫灯之下,接过云英手中的卷轴,解开那丝绦,再轻轻展开。
就着不算微弱的灯影,看去。
素白的纸上,短短数十行,百字不到,以极细的羊毫挥就而成,字体端正恭肃,却又隐隐透出清隽灵秀。
敷儿才看了数行,不过寥寥数语的开篇,书柬,便已如断翅的枯蝶,缓缓自指尖坠落。
“魏国公达长女,幼贞静,好读书,人称女诸生。帝闻其贤淑,召达谓曰:‘朕与卿,布衣交也。古君臣相契者,率为婚姻。卿有令女,其以朕子棣配焉。’达,顿首





![[重生]主公要臣死 作者:南山有台封面](http://www.cijige2.com/cover/53/53416.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