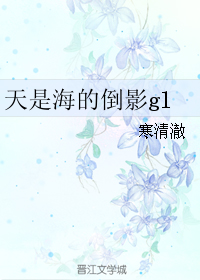在昼而为影gl 完结+番外-第7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水底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把她往下拽,她快要窒息了,她用尽全力地伸出手想碰到水面上的光。
那是希望,那是唯一的希望。
可是她已经渐渐失去力气,手脚灌了铅一样沉甸甸的,她离那束光越来越远了。
“哗啦——”
又是巨大的水声,不知道过了多久,水面渐渐平静下来小船不再晃动,陆林钟渐渐从惶恐中恢复了意识。
她伸手够着船尾的救生圈,扔到水面上,紧紧地扒着船沿。
安槐序焦急地将船靠近许终玄落水处,看见陆林钟脸色惨白死死抠住船沿,她微微张了张嘴,黯然地把将要脱口而出的话咽回去。
“哗”孟秋托着许终玄浮出水面,抓住了救生圈。
救生船来得及时,工作人员给她们放下了救生梯。
“先上船。”
许终玄浑身湿透,坐在甲板椅子上,孟秋蹲下身给她检查有没有伤口。
安槐序往前探了探,压低声音问许终玄:“怎么样了?我们马上去医院吧?”
孟秋冷冷地看了她一眼,背过身去,走到远处。
许终玄冲安槐序勾唇,“我没事,不用去医院了,直接开车回家吧。”
安槐序上前一步对孟秋愧疚道:“孟秋,对不起。”
“你可没有对不起我。”
晚风拂来,已经不是下午时的温柔从容,夹杂着夜幕的凉意,吹在湿透的衣服上着实刺骨。
陆林钟从船舱里走出来,手上拿着两条薄毯,朝安槐序递过去。
安槐序犹豫两秒,别扭地接过毯子,小声对陆林钟说了句“谢谢”。
她把薄毯披在许终玄身上,许终玄朝孟秋扬了扬下巴,给安槐序递了个眼神。
“孟秋,你别生气了。”安槐序把手里的毯子向前伸了伸。
孟秋扭头看着安槐序:“你平常再怎么乱开玩笑我都能接受,可是当刚才的情况有多危险。”
安槐序低下了头。
“我问你,如果今天我不在这里怎么办?如果终玄不会游泳怎么办?”
安槐序哑然,手拿着毯子垂在两侧。
“你知道陆副总会不会游泳?还是你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不让终玄出一点意外?”
安槐序下意识地看向陆林钟,用力捏紧了毯子一角。
孟秋冷着脸看她:“所以你玩水枪的时候根本没考虑过后果对不对?”
陆林钟挡在孟秋和安槐序中间,把安槐序挡在身后,皱眉沉声道:“孟秋,可以了。”
孟秋看了一眼陆林钟,最终别过脸望向岸边。
直到天色完全暗下来,安槐序确定许终玄没有大碍后,才开车从许终玄家驶回澜庭名墅,陆林钟坐在副驾驶上,掩唇轻咳了两声。
安槐序刻意放缓了车速,从后视镜里偷偷看陆林钟,从船上下来之后,她苍白的脸总算渐渐恢复了血色。
安槐序目不斜视地盯着前面的路况,问:“着凉了?”
陆林钟懒懒摇头,“还好。”
车里又安静下来,安槐序的嘴唇轻轻翕动,总是话到嘴边又不知道该怎么说出口。
“你,在船上······”她用力握紧了手里的方向盘,趁着右转的机会侧过头瞧陆林钟。
陆林钟别过脸看着车窗外,“已经没事了。”
安槐序沉默了一会儿,追问道:“真的没事了吗?”
“嗯。”
汽车在楼前停稳,车内不大的空间里飘着两个人都未曾察觉到的旖旎,像极了春日里拂过柳枝的柔风,总叫人难以寻觅它的踪影。
第76章
陆林钟打开副驾驶座的车门; 安槐序紧随着她走进屋里。
陆林钟顺手把包挂在玄关; 小声说:“我去做晚餐。”
羊皮软底拖鞋踩在瓷砖上的声音听起来让人安心; 陆林钟抬手按下厨房里的顶灯,将她褐色的长卷发晕出一圈柔光。
安槐序驻足在玄关看了几秒,走进厨房; “一起做。”
陆林钟没有拒绝,从冰箱里拿出一包咖啡豆,吐司,番茄,切片奶酪和培根。
安槐序走过去,把咖啡豆放回原处:“晚上喝牛奶吧。”
她蹲下; 从碗柜里拿出两个玻璃杯,用量勺往杯子里舀了15cc脱脂奶粉,等水壶里的水烧沸。
陆林钟挽起衬衫的袖子; 水囫囵地吻过她雪白秀美的手腕; 圆润的番茄在她的手里像块宝石,一红一白; 对比鲜明。
空气里萦绕着淡淡的玫瑰香; 是陆林钟经常用的For her; 最开始是花瓣初绽的烂漫,随着时间推移,花瓣颜色越浓烈,花朵周围也长满了带着细微尖刺的深绿色枝叶,向来客告知她隐藏的炽烈和危险。
厨房的灯光像玻璃罩一样覆盖着馥郁的玫瑰丛; 她是其中最抢眼的那朵。
陆林钟打开燃气,安槐序主动走过去拿起硅胶刷,示意陆林钟往后站:“我来做吧,有油烟味。”
陆林钟退坐在吧台凳上,倒了一杯凉开水。
溏心蛋,香煎培根安槐序都做得比以前熟练,吐司片沿着对角切好,表面刷了一层薄薄的蛋液放入烤箱里,等个五分钟就可以吃了。
安槐序侧头看着陆林钟,这样温馨的场景勾起了她的记忆,同样暖黄色的灯光,同样的地点,同样是已经过了吃饭时间的晚上,还有用来盛食物的碗碟也还是原来那套。
陆林钟的眼睛看向了别处,像岸芷汀兰蒙上了一层薄雾,带着一抹浅愁。
厨房里的空间本就不大,安槐序能感觉到陆林钟此刻心绪的波动,但是从前就横亘在她们之间的诸多不快,让她有些无措。
或许这时候她该走到陆林钟身边,从背后抱着她,下午在船上看到陆林钟那么害怕,她其实愧疚又心疼。
或许她又该坐到陆林钟对面,握住陆林钟秀白的手,用自己手心的温度温暖陆林钟一贯冰冷的指尖。
或许她们应该多说一点什么,比如她主动关心陆林钟在忙些什么?
安槐序盯着烤箱里的食物,三明治的蛋液变得焦黄,温实醇厚的香气很快就压过了陆林钟身上淡淡的香水味。
陆林钟拿起烧水壶往玻璃杯里注了四分之三的温水,两杯牛奶,两份一模一样的三明治摆在吧台上。
“牛奶好了。”
“三明治也好了。”
窄长的吧台更适合单侧就座,安槐序从烤箱里端出三明治偏巧就坐在陆林钟正对面。
两个人坐得很近,同时伸出手握住了同一杯牛奶。
安槐序的目光停留在陆林钟粉嫩的指尖上,心又像从前一样扑通扑通。
陆林钟先缩回了手,浓长的睫毛微微掠动,抬眸看着安槐序。
两个人的目光碰在一起,尴尬,躲闪,不舍,暧昧,流连······在这气氛柔和的夜里,情感是易燃品。
陆林钟低下头用刀叉把三明治切下来一个小角,慢吞吞地吃了一口。
安槐序余光扫了一眼陆林钟皎白的脸颊,随意绑起来的长卷发松松垮垮,有几丝不听话的已经滑落在身前,她没有再犹豫,抬手就帮陆林钟挽好了头发。
陆林钟停下动作,静静地看着安槐序。
“我,脸上有东西?”叉子在安槐序手里转了几圈。
“没。”
“哦······”这种感觉,让她有些恍惚,安槐序拿起杯子,喝空了杯里的牛奶。
窗外不知什么时候开始飘落起淅淅沥沥的秋雨,打在玻璃窗上,一声一声,填补着她们之间的沟壑。
“快吃吧。”陆林钟刻意放低声音,仿佛柔过了窗外的雨。
吃过晚饭,安槐序把用过的碗筷放进洗碗机里,有条不紊地收拾起厨房。她不时抬手,揉一揉有些酸疼的脖子。
陆林钟从二楼侧卧里找出一身干净的睡衣放进浴室里,柔声说:“去洗澡吧,我给你涂药。”
“嗯。”安槐序答应得很利索。
陆林钟疑惑地望了一眼安槐序的背影,低下头打开五斗柜,找出医药箱。里面用来治疗跌打损伤的药并不多,只有一套气雾剂和一瓶红花油。红花油是前年买的,已经过期不能用。
陆林钟打开盒子的塑封,从里面找出说明书,一字一句地看用法用量——外用,喷于伤患处,一日3~5次,按摩3~5分钟,若剧烈疼痛可间隔1~2分钟重复给药,一天使用不得超过5次。
“适合人群:闭合性损伤者。”陆林钟晃了晃喷剂瓶,在手上试着喷了一点药剂,一股浓烈的药味儿在客厅散开,她忍不住皱了皱眉。
安槐序洗澡的速度算快,半长的头发扎成一个小揪,露出细长的脖子,像软嫩的白奶油做成的雪糕,陆林钟看了她许久,问:“回房间上药?”
“嗯。”安槐序迈开步子走在前面,在主卧和侧卧门间犹豫了一会儿,还是走进了侧卧。
她抬手打开了床头灯,靠着床头的那面墙被灯光照得发暖。
“躺下吧”
安槐序抬手掀开被子一角,脸侧向枕头趴在床上,睡衣的领口本就宽大,几颗扣子还被解开了,嫩白的肌肤暴露在空气中,再往下便恍若芙蓉半遮面。
陆林钟坐到床沿上,安槐序背上原来那几道红痕变成了青紫色,怪不得刚才在厨房里,安槐序总是有意无意地伸手去揉。
肩上,背上交错着好几道,连后颈那也有一块淤青。
是被人用什么伤成这样的?木棍?铁棍?如果伤到头伤到颈椎脊柱了怎么办,她想想便觉得后怕。
陆林钟眸光骤冷,手暗自用力握紧喷剂瓶。
“怎么了?”安槐序侧过脸,勉强能看清陆林钟的侧脸。
“没······”陆林钟用一块小方巾遮住安槐序的脸,“药味很重,遮一遮免得喷到脸上了。”
安槐序细细地嗅着方巾上的香味,是属于陆林钟的玫瑰香,她眷恋眼前的片刻时光,眷恋这种感觉,她们之前好像没有过矛盾和争吵一样。
陆林钟是温柔的,耐心的,沉静的。
屋里的灯光是温暖的,安然的,平和的。
陆林钟把喷剂喷在手心,放轻力度把它抹到安槐序背上的淤青上,柔声问:“疼吗?”
“不······”丝巾遮在脸上,安槐序放心地拧了拧眉,即使龇牙咧嘴,陆林钟也看不见,“不疼。”
陆林钟挑了挑眉,其实她已经从缝隙里看见安槐序皱眉了,鲜活清秀的五官皱起来不算难看,反而很俏皮。
陆林钟的嘴角弯了弯,一双明亮的眸子好渐渐汲取了屋里本就不够明亮的灯光,熠熠又柔和,她轻柔地按了几个来回,想了想,又往手指上喷了一点药剂。
就这样,也很好啊。
趴在这里安静等她上药的安槐序像只受伤了的小猫,乖巧听话,说话的时候还带一点点鼻音。从前她希望安槐序能够尽快地变成熟,做事条理清晰,为人八面玲珑,但是现在她却有些不确定了。
成长是一个不断往上的过程,当孩子变成大人,最直观的是身量变大,身高增长。而在心理方面,逐渐会有自己的想法,判断,也会不再需要一个人在她身边不断纠正和提点。
她不是喜欢以一个年长的身份自居,而是担心或许很快安槐序就不需要她来引导纠正一些言行。
她是矛盾的,既期待有一天眼前人变得强大,又担心真正到了那一天,自己会无所适从,她一向骄傲惯了,怎么能容忍自己去依靠别人,即使是亲密如伴侣,也是一样。
药剂润滑,陆林钟沾着药膏的指尖灵巧,在安槐序的背上上下游走,最后摸到安槐序腰上的那道紫瘢,顺着腰侧往下抚摸。
安槐序不自然地颤了颤,陆林钟还陷在茫然无端的情绪中,全然意识不到自己做了什么。
“嗯?”安槐序撑着手起身,握住陆林钟的手,本想对她说又占自己便宜,却看到陆林钟脸上神色黯然,灯光下她的侧脸线条优雅匀称,从额头到下巴,每一处都好看得让人挪不开眼,眼角微微泛红,嘴唇有点泛白。
陆林钟垂眸,不动声色地抽回手。
安槐序被这样低落的神情狠狠刺了一下,套好了睡衣主动抱着陆林钟。
她其实想告诉陆林钟,她是可以让她依靠的,只要,陆林钟信赖她。
几个叠在一起的靠枕平放在床头,安槐序搂着陆林钟,指尖还绕着一缕卷发。
“你很怕坐船?”
陆林钟侧着身子,背对着安槐序,漫不经心地“嗯”了一声,想了想补充道:“但我不怕坐海盗船。”
安槐序会意陆林钟的意思是怕水。她见过不少的人怕水,但是到陆林钟这种程度的很少见,是不是陆林钟从前经历过什么,才会留下这么深的心理阴影。
在一个人面前提起从前的伤痛,很多时候并没有太多的安慰效果,反而会让那人又回想起当时的感觉。
安槐序没有再问,只是语气郑重地说,“对不起。”
原来“对不起”这三个字,也没有那么难说出口。
“六六,以后不会再发生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