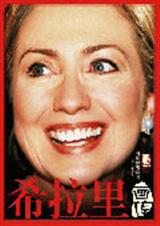沙汀画传-第5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做你的读者要有很高的条件,不少人可能因此而退却了”。“你书里出现的劳动人民给人的印象是不鲜明的,而且和那些反面人物容易混同起来”。“你的讽刺还缺少一种刻毒的力量,不能激起读者足够的愤怒”。
反复思量着这些话,他感到兴奋和惶惑。对丑的调侃不应只是一种色调,社会讽刺为什么不能有表面不太“刻毒”的呢?他想不太明白。但知道,他的讽刺的笔法在今天已没有多少用武之地。保持对生活精细观照的能力,来写新的农村,可能是他应走的路吧。横贯欧亚大陆的漫长旅途给了他思索的时间。
(这一段的思索是重要的。你的讽刺艺术从此便弱下去了。赵树理对农村还能保持一点锋芒,我在一部分创作思想上比他萎缩)
他们到了莫斯科,然后转赴东柏林。这个作家代表团太小了,小得不引起注意。驻苏、驻德的使馆之间联络不畅,他们两次呆站在外国首都的车站大厅里,等不到接待的人。东德大使当时是纪鹏飞。
新中国的文化使者在1952年11月那个年代,到社会主义的东欧来主要是认同,而非求异,沙汀地域性的自足心境不容许被打破。在莫斯科大旅舍下榻,住一百卢布一夜的房间,吃十卢布一盘的凉拌卷心菜,就觉得浑身不舒服。他告诉使馆的人员,返程再经过这里,但求住普通的房子,喝红菜汤就可以了。到了柏林,发现为出国特备的驼绒大衣太暖,只好买呢大衣。他带头挑半毛料质地的,认为纯毛料的太贵。
这有什么办法,只有节俭才愉快,他改变不了自己。访问的日程排得满满的。声援中国革命的剧本《怒吼吧,中国》的老作家弗里德里希·沃尔夫,使人感到亲切。屋子里陈列着金山寄赠的他的剧本在中国演出的剧照。老人特别喜欢在战争环境下成长的马烽。在诗人库巴的家里同东德作协主席安娜·西格斯会面,沙汀读过她的名作《第七个十字架》。他觉得修养高深的女作家不如工人出身的库巴好接近。他们还特意访问了脱产刚三年的矿工作家泰渥·哈利希,听他仔细介绍自己的经历。他们访问过各种工厂,造船厂、化工厂、冶炼厂,在工人住宅区与群众接触,参加过清除战争废墟的义务劳动,甚至得到一份劳动证书。
在他们的再三要求下,好不容易参观了一个农业合作社,但没能与任何社员接触。按照他的理解,东德的和平土改使农民普遍存在“变天”思想,要比中国土地上发生的一切来得差。
不过他在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看到的古典文明是灿烂的。去凭吊过魏玛的歌德故居、墓地和席勒故居。在绿蒂的坟茔旁,他对德国人讲述中国五四时期的”维特热”。在德累斯顿谈鲁迅介绍柯勒惠支的版画,在莱比锡法院听当年季米特洛夫讲演的录音。他仿佛是拿东欧的社会主义来加深认识自己国家的社会主义,并肩负着将一个真正的中国介绍给对方的使命。
在参观土林根省的玩具博物馆时,他就纠正了外国朋友的一个“错误”。他在琳琅满目的展品中发现丁一件中国的黄杨雕刻,雕了一个拖辫子的男子与一个小足妇人面对面躺在烟榻上吸鸦片。这个旧中国丑恶的小摆设,引起他生理上的不快,他控制着感情,向那位引导参观的馆长解释,这绝对不是一件什么儿童玩具,历史上中国从来没有这样一种玩具!但是先前在北海造船厂访问,曾有过一次小小的发作,他没能控制得住自己。对方是一位接待人员,三十年代加入海军,驻防过上海,似是个“中国通”。这个昔日的德国水兵并无恶意地询问沙汀:
“上海现在还有‘燕子窝’吗?”
沙汀告诉他,早经查禁绝迹了。可他不信。再三地说明,仍摇头说:
“听别人讲,鸦片烟一旦上瘾是戒不掉的呀!”
倒好像是沙汀在强辩。终于惹得他的脾气上来,脱口说道:
“据我所知,世界上只有一样东西戒不掉:面包!”他说这句话实在急躁,以至在用“面包”这个词以前,先就溜出一个“饭”字。
马烽在旁边,禁不住笑着接过话来打趣他:“哪里听说有什么‘饭包’啊!”
这样总算缓和了一下空气,没有造成更尴尬的场面。其实他知道,德国朋友的固执己见,是因为交流太少。他的反应是习惯性的。他无法允许别人随意地破坏他所“经验”的一切。
(你跑到万里之遥的外国,吸收到的知识很有限。你不是在用外面来充实内面,更谈不上冲击内面。我注定是一个“土”人,经验型的人,出国仅仅是用外部的世界来证明一次内面的世界而已)
年底结束访问,原路回国。在北京逗留期间,中宣部文艺处的林默涵、严文井找他谈话,让他到“文协”将成立的创作委员会工作。他回四川写作的梦做不成了,推托的话刚出口,林默涵便一本正经地说:“已经决定了。你不干,我们发调令调你,看你干不干?”他只好答应做一两年看看。陌生的工作来得很急切。1953年4月,创委会成立,中宣部副秘书长邵荃麟当了这个机构的主任,沙汀为副主任,实际主持日常工作。4月5日,他还在重庆的西南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会议上致开幕词。10日闭幕,他刚刚被选为西南文联的主席,便赶往首都去接任新职。起初没带家眷,过一段时间才将玉颀和小儿子刚宜接来。四川的岳母及其他孩子,好像是他故意留下供撤退用的后方。
全国文协所在的北京东总布胡同二十二号(今五十三号),是个堂皇的宅院,沿第二进院两侧游廊拾级而上,进入第三进,迎面是一幢带飞檐的二层楼,说明它原来的主人中西合璧的趣味。这座楼底层东面的外屋为会议室,有讲究的地板,依靠中部的活动拉门可调节室内的空间。里屋便是沙汀领导的创委会。楼上分别住了邵荃麟、艾青、丁玲几位。
第二院的东北角开有小门,连着一个侧院。院内的一座楼更加小巧,楼上便住着沙汀、张天翼两家。二十二号斜对面的四十六号大院(今六十号)是“文协”宿舍,也是三进的深门大院。住的人就更多了,严文井、刘白羽、罗烽、白朗、赵树理等作家都聚在那里。
解放初期的机关,气氛较为活跃。创委会十几个人,秘书、干事大都很年轻。“文协”的领导都是他三、四十年代相熟的作家,这一点使他满意。最早的党组书记是周扬,党组成员,除邵、沙之外还有丁玲、冯雪峰、萧三。邵荃麟、葛琴夫妇是1944年从桂林疏散到重庆时认识的。起初他们住在沈起予兄弟开的旅馆里。邵很瘦弱,当时便常常有病,但一谈起话来便劲头十足到不可收拾。邵荃麟懂得文艺,有理论水平,带病指导创委会工作,出席会议讲话,声音细小如秋虫、如游丝,到了最后,如沙汀说的,简直是演“无声电影”。邵充满书生气,完全不会照顾自己。他抽烟,常忘带火柴。向别人借来,用毕便装进自己口袋。刚吸了一支,急急地走了,会把烟整包地掉在别人家。这个人对人是很好的。
认识艾青是在北碚,把他介绍给周恩来,促成他赴延安。艾青是诗人气质,沙汀曾对曹禺笑着抱怨过,说艾青见面握手,不止握得紧、重,还要拿起别人的手来摩挲,不知算哪国的礼节。
至于张天翼,自抗战胜利前在郫县专程访病以后,这还是两人第一次见面,又是相邻而住。天翼这时尚未再婚,身体恢复得不错,谈吐聪明,常来邀沙汀喝啤酒、散步,然后谈苏联小说,谈《红楼梦》,研究别人的创作经验。也谈过周扬与冯雪峰的那笔旧帐。天翼对冯有好感,对周扬的评价不如沙汀高,但也很尊重。这一段,两人的关系大大增进。二十年后天翼脑血栓半瘫失语,沙汀每次去崇文门新居看他,一两个小时,沙汀讲,天翼动作,可以谈得津津有味,大约就是这个时候打下的友谊基础。
创委会的工作是指导全国的文学创作,这是从苏联学来的。沙汀一到北京,从4月下旬到6月下旬,便遇上组织四十多个作家、批评家学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是创委会出面做的第一件大事。邵荃麟身体欠佳,委托冯雪峰主持,沙汀只是当助手,并负责编辑《作家通讯》。这个内部刊物从这年6月创刊,到第十一期,都是他领导束佩德等人编写的,一开始就是编发这次学习的情况。
系统地接触马列文论在他也是难得的。阅读二十二种必读文件,还包括马林科夫、日丹诺夫的有关报告,十四次讨论会分别讨论了现实主义发展历史、典型、党性与人民性、创作现状等四个问题。在大的场合沙汀很少发言,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唯一正确的创作方法,他当然做为正确理论无怀疑地接受。
后来是筹备召开二次文代会。会后,“文协”改为“作协”。创委会内外结合,成立了诗歌、小说散文、剧本、电影、通俗文学、儿童文学等创作组,组织讨论杨朔的《三千里江山》,诗歌形式,苏联波列伏依、安东诺夫的作品,陈白尘的《宋景诗》,王亚平的《张羽煮海》。沙汀这时显得热心、活跃,小说散文组讨论《三千里江山》时,沙汀到北京大学请了吴组缃来做主要发言。吴对小说的粗糙处批评得较多,引起了一些解放区作家的议论。有人来问沙汀:“为什么要完全否定?”
他很惊奇,说:“现在不是打起灯笼火把在找它的优点吗?”
可是别人还不满意,说:“为什么要打起灯笼火把找哇?就是写得好嘛!
吴组缃是有独立见解的人,他觉得自己的评价已经不低,用不着一味赞美。事情变得复杂起来,沙汀的位置分外地受到压力,后来没有全力支持吴,是至今仍引以为歉的。但是在心里,他对这位十几年的畏友的耿直品格与很高的文学修养,十分钦佩。纪念吴敬梓,《中国文学(英文版)》需要向外国介绍的文章,是他去特邀吴写的。星期六全家去颐和园游玩,有时便在北大的吴寓下榻,第二天才返回城里。一度还请吴组缃到作协书记处任过职。两个性格绝然不同的作家,长期保持了友情,凭的是双方的真诚。
要说留恋创委会时期,大概就是这些琐碎的人和事。1954年,指导全国的工业题材创作和工人参加创作,艾芜从鞍山带回《百炼成钢》的毛坯,住在沙汀的小院里修改。起初是个中篇,只十来万字。创委会组织内部讨论,因为第一稿的粗糙,艾芜几乎失掉信心。沙汀找他谈后,决定重返鞍钢“补充生活”,重新写起。
陈翔鹤一直郁郁寡欢,他是知道的。“三反”时陈在川西文教厅被错当作“老虎”打过。在川西文联为了印发倒霉的《柳荫记》原本,一而再、再而三地检查个没完。现在经陈白尘介绍,调到全国作协帮助郑振铎负责古典文学部,与沙汀都在东总布二十二号一个屋檐之下,经常能见面。等沙汀决定离京返川,陈翔鹤很伤感地对他说:“你回去搞创作好,千万不要在‘文联’住起,那里住不得!”
批评路翎时,沙汀是党组成员之一。在我记忆里,他发言很少,更没有什么重要发言,办事认真到有些拘谨的程度。
他基本上是个创作家,组织领导,不是他擅长的事。
他读材料,用红蓝铅笔划各种道道,还要用毛笔添上许多眉批。对我送他审查的文章总是详加推敲。
黄玉颀在作协做秘书工作,有朋友到家里去,他们总是热情招待。这时他就变得健谈起来。平常他是很随便的。记得陈森去鞍钢,创委会为了送别,组织大家去西郊游园。在颐和园买门票时,他悠闲地坐在大门旁抽烟,还抽空抄起一本杂志来看。我曾为他偷拍了这张照片,不知现在还能不能找到。他自己穿戴极平常,灰布干部服,不那么熨帖,夏天是一件发黄的绸衬衫,冬天喜欢围一条短围巾,落下来就一甩。
1954年末,黄玉颀先带孩子回南方,沙汀成了独身。
我也没结婚。星期六傍晚他总是从后面院子踱出来,到大门口西厢我住的屋门前大喊一声“束沛德”,用的是浓重的四川口音。我是凭感觉知道喊的是我,便出来一起到外面饭馆吃饭。吃饭的地方有东安市场的“五芳斋”,西四的“恩承居”,新开胡同的“马凯”。那时“马凯”没在鼓楼。总是他掏钱的时候居多。1955年他走后我结了婚,他来北京开会还特意补送我们一块绸子台布,做为礼物。①
还是围巾不离身的季节,他已经时常流露出要离开北京到下面去创作的情绪。他去着周扬、邵荃麟、严文井,不断地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