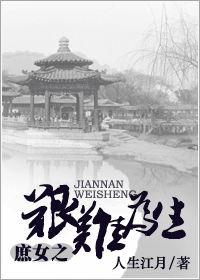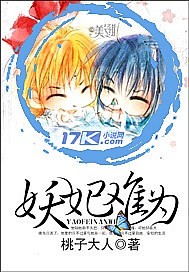表妹难为-第15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儿媳也实未想过,有朝一日竟能嫁给世子。若不是在太后宫中听太后提及,是再想不明白为何有这福气的。”
昀郡王又闭上了嘴。这件事他能说什么呢?完全都是秦王妃一手促成的。
“自你进门,却也无甚行差踏错。”许久,昀郡王又叹息般地说了一句,“只是在你心中,除恒儿之外,并未将其余人等视为至亲罢?你方才所说的一家人,怕是连你自己也做不到罢?”说着,他眼中露出一丝讥讽,却又带着几分伤感。
这真是诛心之言了,绮年低头想了想,站起身来重又跪下:“请父王恕儿媳之罪,儿媳确实做不到,因为不敢。”
昀郡王眼睛又眯了起来:“为何?”
“儿媳千般防范,仍然在二弟的喜宴上出了御赐酒器之事,若儿媳未做防范,更不知今日将会怎样。”
昀郡王再次沉默了。绮年觉得话说到这里已经可以了,再说招起昀郡王反感就糟糕了,便道:“世子曾对儿媳说过,家和万事兴,儿媳是个没见识的,只觉得这话实在有理,也想着好好伺候世子,安生地过日子,如今这事儿一件接一件的,儿媳心里实在是没底儿,究竟要怎么做,还要请父王做主。”
昀郡王几乎要被她气笑了:“让我做主?你还用得着让我做主?”
“儿媳没头苍蝇一样乱撞,手上又没有多少得用的人,只仗着从前跟皇长子妃的一点儿交情去求了庇护,除此之外真不知该如何是好了。”绮年听昀郡王连“本王”都不用了,估摸着自己说得差不多了,便只管低了头站着,如果不是演技不够纯熟,真想挤两滴眼泪才好。
“你先出去罢。”昀郡王摆了摆手,“说什么无人可用,外头站的那些难道不是?你也不必在这里——去罢。”
“那儿媳告退。”绮年爬起来,又小心地补了一句,“儿媳不孝,惹得父王烦恼,只请父王保重——儿媳想秋日天燥,早晨就叫厨房给父王熬了莲藕排骨汤,父王要不要喝一碗?”
昀郡王对她简直是无话可说了,只得道:“端过来罢。”摆了摆手让这儿媳妇出去,只怕再多看几眼又不知该气该笑了。
秦王妃在书房旁边的院子里等了半天,才见姚黄进来:“世子妃回自己院子去了。”
☆☆;
☆‘87book‘☆;
☆‘87book‘☆;
☆‘‘☆;
☆‘小‘☆;
☆‘说‘☆;
☆‘下‘☆;
☆‘载‘☆;
☆‘网‘☆;
“可有什么异样?”
姚黄摇了摇头:“奴婢看见世子妃脸上似乎还有笑意呢。”
秦王妃站起身来便往书房走去,若是这样的机会都不能让绮年除掉,哪里还能再寻到更好的机会?
昀郡王在屋里看着一地的东西正出神,就听外头侍卫禀报:“王妃到。”抬头见秦王妃进来,便道:“你怎过来了?”
秦王妃看着地上乱七八糟的东西,心里实在想不明白,既是如此生气,怎的绮年出门时还会脸上带笑呢?
“妾身听说王爷这里有侍卫闹事,是以过来看看,因王爷跟世子妃说话,就在旁边等了一会儿。”
昀郡王点了点头,却没接这话,只坐着仍旧出神。秦王妃等了片刻,试探着道:“王爷这是怎么了掀了这一地?可是又为着世子妃外头的事发怒?王爷也该注意身子,任什么名声也没有王爷的身体重要。”
昀郡王抬眼看了她片刻,还是点了点头:“外头的事你不必管了,再过几个月就是妤儿及笄,你只给她好生操持着便是,务必办得风光些。”
秦王妃听得心里一紧,低声道:“那世子妃这事……”
昀郡王没有抬头,淡淡道:“世子妃怎么?”
“如今外头这样的传言,可要如何是好?”
“毕竟是恒儿的妻子,还能如何呢?”
秦王妃越听越是心凉,思来想去,终究是舍不得这个机会,道:“妾身早说过了,断不能因她连累了世子,连累王府,不如王爷去宗人府递了折子,将她——”
昀郡王抬起眼睛盯着她,将秦王妃的话盯了回去。他看了秦王妃一会儿,低沉地道:“家和万事兴,这话你可曾听过?”
秦王妃心里暗恨,低头道:“妾身正是为着家和才要如此——”
“不必说了。”昀郡王一摆手,“你回去罢,只管打点妤儿的及笄礼,它事休问。英国公府不是也来议过婚期了么,妤儿的嫁妆也该好生整理起来了,只这些事想来也够你忙碌了,不必再为它事分心。”
秦王妃咬着嘴唇,满心的不甘,想了想又道:“那方才那些敢于冲闯王爷书房的侍卫,要如何处置?”
昀郡王终于不耐:“此事自有本王处置,二门之外,王妃休要插手!”
绮年直到走回节气居门口,才觉出两条腿不光是膝盖麻疼,还软得有些使不上劲儿。如鸳如鹂将她扶到床上坐下,卷了裤腿一瞧,膝盖上两大块隐隐的青色。
“快去取拔瘀膏来。”如鸳心疼地皱着眉,“明儿定然要青紫了。”
白露连忙去翻出拔瘀膏送过来,嗫嚅道:“世子妃,王爷——”
绮年觉得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了,淡淡道:“去瞧着立夏那边,若是王爷要处置他们,立刻来报我。”
白露没有得到答案,也不敢再问,答应一声,同着小满小雪一起退了出去。这里如鸳如鹂忙着扶绮年躺下,终于也忍不住问道:“世子妃,王爷到底怎么说?”
绮年把手伸进袖里,捏住那张薄薄的纸条,嘴角微微翘了起来:“尚好。世子虽然远在渝州,却还惦记着我。”
如鸳如鹂一起松了口气,如鹂拍着胸口道:“阿弥陀佛,真是神佛保佑。”
如鸳推她一把,笑道:“什么神佛保佑,是世子爷在保佑才是。”
绮年也笑了。但是她万万没有想到,赵燕恒对她的惦念还不止于此,三天之后,菱花像被狗撵着一样狂奔进屋子:“世子妃,世子爷回来了!”
绮年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几乎是半信半疑地走了出去,然后就看见一身风尘,走路都有些并不拢腿的赵燕恒从院门处走了进来,对她一笑:“我回来了。”
☆、117 难解父子三尺冰
我回来了。这轻轻一句话;瞬间让绮年红了眼眶。
从她飞鸽传书去渝州;即使赵燕恒接到信便往回赶;也不过是六七天的工夫。鸽子长着一对翅膀,也不过比他早回来三四天。当初她从成都到京城,先坐船后坐马车;足足走了近二十天;赵燕恒是怎么用六七天的时间赶回来的?
“怎么哭了?”赵燕恒头发上衣服上落了薄薄一层黄黑色的土;嘴唇都起了一层干皮,嘴角还生了细小的燎泡。他伸手想摸摸绮年的脸,手伸到一半又缩了回去。绮年一把抓住他的手,翻过来一看;手掌已经被马缰磨出了一层血泡。
“你怎么——”绮年低着头,眼泪扑簌簌地落在赵燕恒手上,哽咽着叫如鸳,“去烧热水,拿外伤药膏,拿干净衣裳——要旧衣裳,厚软的!去小厨房立刻熬山药红枣粥来!不,要绿豆红枣粥,去去火气,捡清淡易克化的点心赶紧做四样来,要三咸一甜,不能太甜!”
如鸳如鹂加一个菱花被支使得团团乱转,白露等人都已经站在了廊下,个个都是眼圈通红地看着,小雪猛拍了自己额头一下,也哽咽着道:“奴婢去找衣裳。”转身跑了。
白露情不自禁往前走了一步,却被小满拉了一下:“我们去厨房吧。”将她一路拉进小厨房,才低声道,“没看见世子眼里只有世子妃么?你——”五六年的姐妹,也有些替她心酸,“还是另做打算的好。”
绮年总没注意其他人都是什么反应,伸出手去拍打赵燕恒身上的尘土:“快进屋去!”
“得先去见见父王。”赵燕恒微微一笑,把她的手拉下来,“怪脏的,一会儿脱掉了就好,别扑打了。”
“我陪你一起去。”绮年拉着他的手不放,两人一起出了节气居,迎面就撞见了秦王妃和赵燕平。
“王妃,三弟。”赵燕恒微微含笑,一手还拉着绮年的手,只对秦王妃稍稍躬身。
“大哥这是——”赵燕平一脸的惊讶,“送嫁回来了?怎么只有大哥和一个小厮?”
“都在后头慢慢走。”赵燕恒微一点头,“我还有事要与父王相商,待闲了再与三弟说话。还有些渝州土产,都在后头车上,待到了便一一相送。”拉了绮年就走。
绮年根本没注意秦王妃和赵燕平说什么,一心只放在赵燕恒身上。赵燕恒走起路来两腿都有些不自然地向外张着,想来在马鞍上颠簸这六七天,大腿还不知磨成什么样了。她偷偷抹了把眼泪,忽然觉得这些日子的焦急烦恼都值得了,有个人肯跟你一起分担,还怕什么呢?
昀郡王书房外的守卫拦住了绮年:“世子妃还请不要进去了,王爷说只见世子。”
“那我在这里等你。”绮年替赵燕恒整整衣襟,目送他进了书房。
今日天气极好,阳光透过窗户上糊的高丽纸照进书房里,亮堂堂的。昀郡王在明亮的光线中面窗站着,听见背后门响也不回头。赵燕恒将书房门关好,然后撩起衣襟就跪了下去:“给父王请安。”
昀郡王一动不动,赵燕恒也就跪着不动。良久,昀郡王忽然一甩手,把手里的一叠东西摔到了赵燕恒眼前,怒声道:“你还当我是你父亲么?真以为我就会袖手旁观,或者直接处置了周氏?”
赵燕恒捡起那叠纸看了看,磕了个头:“多谢父王,周氏若看了这些,必然能体会父王一片苦心。”
“一片苦心?嘿,一片苦心!”昀郡王冷笑起来,“我要她知道我的苦心做什么?你才是我儿子!”
赵燕恒沉默良久,轻声道:“儿子并不视周氏为外人,父王呢?父王当年也是这样看待母妃的吗?”
昀郡王怔了一怔,猛回身指着他怒道:“你也跟周氏一样,竟然胆敢来——”却见儿子眼中微微有一层泪光,直直地看着自己,后头的话竟然是说不下去了,半晌缓缓将手放下,颓然道,“总归是为了你坠马的事……”父子之间的隔阂就永远存在了。
“并不为那件事。”赵燕恒几乎是不眠不休地策马狂奔了六天六夜,就是打盹都是临时搞一辆马车边走边睡一会儿,醒了再上马背狂奔,全仗着一口气。如今人到了家,看见绮年无事,这口气一松,真有些顶不住了,身子一歪几乎要跪不住。
“起来说话。”昀郡王心里说不上是什么滋味。他对绮年确实很不满意,一个六品文官的女儿,嫁进来做正妃简直是辱没了赵燕恒。嫁进来之后又容不下后院那些侍妾通房,还因为一个胭脂与丈夫争吵,哪里有个贤惠的模样?如今又因为陪嫁铺子出了那样的事,给郡王府惹了一堆麻烦。所以他才说让绮年自己去想办法,秦王妃说要休弃绮年的时候,他心里的确曾经闪过那么一丝意动,却在接到儿子急信的时候完全怔了。这是几时?几时儿子竟与周氏这样的夫妻情深,甚至不惜用终身不娶来威胁父亲?
赵燕恒站不起来,索性侧身坐在了地上:“我坠马之事,有一半原因是自己恣意妄为,不知如何收服管束下人而起。”
昀郡王看着他:“你既知道,那又是为了什么?”
赵燕恒垂下眼睛看着地面,缓缓道:“倘若父王与母妃素来情深,我便是恣意打死府中奴仆,也无人敢怠慢我。我不为坠马一事,为的是坠马之后,才知道害怕。”
“害怕?你怕什么?”昀郡王猛地提高了声音,“你一满十五岁我便为你请封世子,你母亲去后我为她守孝一年,你这些年在外头风流浪荡,我都不曾动过废你世子之位的念头,你怕什么!说到底,你还是怪我没有当时便将那累你坠马的奴才活活打死!”
赵燕恒觉得无数的话一时都涌到喉咙口,他想理一理思绪再说话,但那些话却自己争先恐后地往外冲:“父王为母妃守孝一年,是真的思念母妃,还是为了续娶王妃名正言顺?为儿子请封世子,是真的喜爱儿子,还是只为了儿子嫡长的身份?或者——是为着对母妃的愧疚?若当年父王不因怕皇上猜忌郡王府与吕家的关系,力谏皇上派兵援助,是不是外祖父与舅舅们就不会全部战死沙场?”
“你——”昀郡王抬手指着他,手指都颤抖起来。
赵燕恒苦笑:“儿子有时也想,若当年祖父母不曾为父王聘娶母妃,如今父王与王妃也就无这些烦恼了罢?”
这句话像针一样,昀郡王如同被戳破了的皮球一样泄了气,在椅子上坐了下来。父子两个默然对视,半晌,昀郡王才摆了摆手:“你远道赶回来,去歇着罢。”随手指了指地上,“那些东西你都拿去吧。”
赵燕恒没有伸手:“儿子只怕有些事不堪深究。”
昀郡王的肩膀微微垂了下来:“你是当真不愿深究,还是怕究了,我也不会听?”
这话诛心,赵燕恒也只能低下了头。昀郡王疲惫地摆摆手:“去罢,你是世子,将来这郡王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