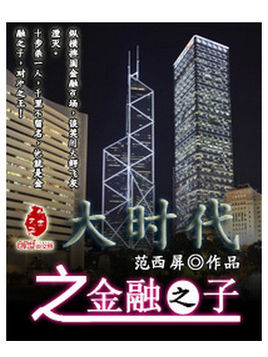溶月与祝融-第11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帐外的昏暗弱光照见旁边衾枕上的订本,他看着它扶额,抿嘴咽下心涌的一缕叹息。
手指准确而熟稔的从头翻到尾,最后一页的承载,无论是画图还是文字,任是阅过之后的再看,还是有些刺激鄢祝融的大脑。
轻轻一声‘啪’响——
鄢祝融合上了画本,他阖眼去睡,脑中明亮的一片白雾,像是纷乱疲软终于布起了安静,可过了不久,意识就跳出清晰轮廓,像风卷的潮汐被推至他心口。
顶着一簇软发的小女孩,还有聚着一双深眼的小男孩,她望着他们咬笔苦恼,口中念念有词;
“宝贝,是你!还是你?”
留刃第三次来到小城江源,溶月的郁闷多了无可奈何的无力,她踯躅片息,使了半夏去问;“施大人来,所谓何事?”
半夏很快就折回后院,快步走到坐在木棉树下学做黑陶的皇后面前,回话的声色带了一丝不易忽略的激动;
“皇后娘娘,皇上下旨让您即刻回京。”
烦什么来什么!
溶月人懵,手中的泥胚就捏坏了陶边,她鼓了鼓嘴叹气;“你去问问施大人,西南气候宜人,本宫能否修养一两年再回?”
皇后竟不想回去!
半夏听的有些瞠目结舌,她忙掩下吃惊的表情,应声而去。
留刃自然做不了这样的决定,他斟酌措辞,传书去了京城。收到请示的鄢祝融,捏着信笺,没有表态。
晚膳时他让留金叫来了大皇子,父子两个默言饭毕。听到一些蜚短流长的桢佑心怀忐忑、问起了爱米;
“父皇,母后不回来了吗?”
喝茶的鄢祝融眉头微挑,放杯问道:“你想让母后回来吗?”
小家伙连连点头;“嗯!嗯!”
他掰指默算一阵,语气落寞的嘟囔;“我已有七个月没看到她了……我很想爱米!”
稚言童真,感同身受。
鄢祝融心意皆软,他抬手摸了摸儿子的头,没再说话。
芳菲渐谢的四月尾巴,溶月做好了第一个成品黑陶,是个颈长的花弧。就是在那天,留刃带着凛凛仪仗和车驾再临茶园。
溶月接过半夏呈上的薄皮信筒,在新种了大片月季的田埂上往复的踱走,在日头最盛的正午,她才打开被浸出汗渍的纸墨,是熟悉而久违的字体,来自皇帝亲笔。
“细思量,惟吟不可忘。”
溶月目扫一行,就合叠塞回信筒。
她仰头把整张脸都暴露在烈日之下,皮肤上的汗腺被光热烘出通红的晕,如此作为的感觉有种介于受虐和享受的舒坦。
初春时,溶月心想,无论哪个世界,都有它既定的脚步,自己卑微渺小且不过沧海一粟。她只想拥有自己的壳,静静数着光阴到生老病死。
可是峰回路转的跌荡,屡屡的被动,摊开的真相,除了世事无常的冠冕堂皇,更多不过是她的身不由己。
侍女们都被安排去收拾行装。
溶月手拿水瓢,亲手浇灌含苞待放的徘徊花,而今她的沉寂确有些过于明显,既无特别迷恋之物,更无强烈厌喜之人。
她这种状态,实在与喜(…提供下载)欢热烈生活的前世,相去甚远。如此的变化,未免裂变的过多,但亘古以来,谁又能阻止改变!
如果溶月以前的抱怨,是为思维太过沉湎的活跃,而今面对毫无涟漪的平静,她还是不能浸身欣然,脱离困惑。
相比激越的热情,回归淡然其实并没有高深的沟壑需要攀越。不过人之徜徉,总归是贪心的望天兴叹,抑或立地而惆。
翌日一早,溶月在云烟缭绕的薄雾中,挥别了宁静如花的小城,一行人在午后抵达昆川俯。已出月子的宋氏丰腴不少,早早就侯在门口翘首以待。
溶月看她面色红润,不作多余客套,让半夏跟她详细讲解以后的善堂计划。她则从娘娘怀里抱了司徒衡臣的次子端详。
孩子长的虎头虎脑,黑豆子一样的眼睛,滴流乱转,溶月看的称奇,自顾抱着走到窗边逗他玩。不是指着窗台一盆碧绿的盆景上的红缎带给他看,就是嘴里吟着清唱给他听。
有溶月的催眠曲,小婴儿很快在她怀里安然睡着。她看着孩子粉嫩嫩的脸蛋,心里不能自抑地滑过一丝触景之涩。
母性乃天性,溶月惧怕成为母亲,但她又忍不住对孩子心生欢欣。更何况现在的她,已在沉长的懊悔中体验到作为母亲的悲喜交加,尤其这体味背后隐藏了一个生命的殇夭之印。
溶月现今的意念很多时候,都像是潜修冬眠的忍者。
现在,惟有孩子的失去能搅起她心乱的飓风,它们总是猝不及防的造访,在她心中绵密的翻滚,即使不是非(提供下载…)常激烈,感觉也还是不能好受。
这样的时候,溶月的言语成了固执的不可能,她仓促带了半春回房浴洗。直到晚饭时分,她才面色平静的交代宋氏诸事章程。
溶月登船北归的那天正是端午,半夏给她绑了五彩丝在手臂。
喝完药,她就倦睡舱房。直到暮色渐显,溶月才恍惚醒来,她推开榛木扇窗,扑入眼目,恰是云山苍苍,江水泱泱。
***……***……***
【本章结束】
☆、第141章 无话
作者有话要说:周末被家里人拖出去,
逛到了临近的小城。
2更的计划泡汤了!
PS,终于买到了李锦记的耗油~
相对来时的路,溶月的归途既没憧憬也无饮憾,也许正因如此宁静的轻淡,旅程显得尤为风平浪静、晃眼过月。
靠岸的前夕,溶月望着静静的江水睁着眼睛,默默与自己对视,隐秘而深远。
她吹着夏日暖风自忖半晌,叫过半夏吩咐;“你去告诉留刃,本宫体弱,暂时不便回宫,还是先回别院吧。”
半夏听的诧奇,她呆愣了片息,才敛去惊讶的神情,应声而去。
留刃没有资格提出异议,他满腹无措、只得先把皇后护送至别院。溶月让人把备给桢佑的礼物,托他带回京城,没有过多叮嘱直接使他回宫。
鄢祝融见到留刃已是掌灯时分,对皇后的作为,虽在意料之中,但对她只字不提的无话可表,他还是高估了自己的接受力,满心失落的气结。
桢佑被叫来御书房,手舞足蹈且惊呼连连的打开各种礼物。鄢祝融看着雀跃的儿子忙的不亦乐乎,目光恍惚的且喜且忧。
摩挲着据说是皇后亲手做的黑陶笔筒,他思绪起伏,从心底渐涌一股久违热望,冲破犹豫同纠结,分明显出发现的肯定。
暗自沉吟,一点点的来回推进,鄢祝融心中不由振振;论是怎样、论是如何,她都是令他欢喜的那个人!
溶月应对疏远或陌生了的环境,比较擅长的方式仍是昏天黑地的睡觉。酣梦既是种逃避也是种放松,这种时候,她不在意过程,她只在乎结果。
第三天的自然醒,窗外艳阳高照,溶月起床洗漱,草草吃个苹果就出门往许久未见的果园行去。
鄢祝融彼时抵达别院,问过错愕懵怔、毫无准备见驾的黄总管,径直去了苍穹院。留金看着皇上急去的背影摇了摇头,对着几个贴身内侍嘱咐数句,他才慢腾腾地朝果园晃去。
鄢祝融大步流星,一路奔走,待忽觉脚下的路像是凭空变长,他才意识到当下的情绪,可称尤为迫切!
体味着这字义,鄢祝融脚步略略收顿,他看眼森木郁葱的前方,心明皇后就在那里,某颗树苗的旁边!也许正有某片叶子遮了她的面容或身影?
这种具象细节的揣想,像空气烧着的粉身碎骨,连灰烬都蹿的发烫,鄢祝融不由自主,脚步再次大迈出去,锦服的袍角在风中疾闪,起起落落的湍急,像极再也停不下来的出发。
视野在满眼的碧绿中搜寻,一寸寸的排除,鄢祝融在遇到他的皇后之前,是听觉首先发现了她的踪迹。
他闻音变缓,寻声站定,是皇后擦着云絮在婉转浅唱;
“等待晚上,迎接白天。”
“天涯海角,心血来潮。”
“有人在吗,有谁来找。”
“不晚不早,千里迢迢。”
“哪里找啊,哪里找啊。”
“一切很好,不缺烦恼。”
“我曾见过,一场海啸。”
“却没看过,你的微笑。”
“我捕捉过,一只飞鸟。”
“却没摸过,你的羽毛。”
“要啊不是,那个清早。”
“我说你好,你说打扰。”
“要啊不是,我的花草。”
“开得正好,开得正好。”
“哪里找啊,哪里找啊。”
……
要不是无意回头看见身后的半春跪在地上,拔草的溶月还不知她多了个听众。
望着三丈开外的皇帝,她暗自叹了口气,慢条斯理把手上的杂草递给侍女,示意让她们下去。
宫娥悄无声息的退远,鄢祝融看着立在花丛中的皇后;白绿绣竹叶的蜜合色披帛,艾绿撒花绸裙正被细风掀起一串涟漪,像个漩涡,微微的晕眼。
那么多叠加的昼夜,只感觉翻来覆去像极了魂牵梦绕,而今相近在即,鄢祝融反滞顿,心间纵生情怯之感。
他望见皇后没有笑容的脸上涂满了淡远,纵使隔着距离,鄢祝融也能看见她眼中莹莹碎波的波澜不兴,那是她镇定时惯有的维持。他对此了解颇深,那是她从容的气度,但也是她与人疏离的流露。
参透这些,让鄢祝融心底不由泛起酸涩阵阵,像是有风浪的助长,排山倒海的撞击,情绪里的落寞让他有收拾不住的恣意横流。
鄢祝融深吸口气,目不转睛的注视让他期想,就这么望着吧,直到她露出记忆中的笑靥、露出血热的衷肠。
最好她能跑来拥抱,跟他再说一回相思的弥漫!
溶月看皇帝视线定定射在自己身上,她不适的偏过头,心思宛转、犹疑多出的平淡让她踯躅,最终原地踱步,保持进三步退两步的速度、向他徐前。
溶月走着走着,眼看皇帝眼眸中的波澜壮阔愈渐清晰,她心尖微怵,视线下意识地撇开他眼睛,掠过他削瘦的面庞、衣袂金线的菱纹,一路散漫滑向脚边的青蕊嫩草。
虽然不易,但搜罗奇花异卉还是比制造刻骨铭心的传奇来的简单。
溶月思量,眼下如此模样的重逢,尽管有风和日丽做依美的布景,但终究延展不了更多,以致成为不朽。
溶月思想隐隐的复苏,自作主张地拉开有限的架势,偏在这样的时候低吟,过去的风韵或余伤,总归已成了过去!
只记得,灵魂遥远。
只记得,聚散本是无常。
只记得,回澜拍岸后的宽宏大量。
只记得,哪里的现实圆满无缺?
只记得,人世间本是处处有情!
即使缓慢,也没有走不完的路。溶月驻足,她站在皇帝面前的距离,不远也不近。
“给皇上请安!”
鄢祝融看着屈膝见礼的人,愣了下才醒神道:
“免礼。”
话落,两人皆无再语,静默很快就给气氛染上了尴尬,溶月垂眸蹲身继续拔草,鄢祝融看眼她落在地上的裙摆,视线落在了紫蓝花瓣衬得格外盈白的手指上。
“以前没见过……”
他不着痕迹的凑近两步,声音低搭绵绵清风;“这是什么花?”
“它叫飞燕草,不算是花。”
溶月拨出一簇厥草,声音显得没有起伏的平和;“臣妾喜(…提供下载)欢这东西,让黄总管找来种的。”
鄢祝融颔首,眼睛看着她被阳光照出透明的耳垂。
“它有何特别之处?”
不过因它花语是自由自在。
这理由,溶月却不想说,她想了想轻道:“它可以治疗牙疼。”
鄢祝融看出她的犹豫,听到她的答案,更确定了她的敷衍,他不由凌然追问:
“皇后齿恙?”
溶月懵了下,语气多了丝不耐;“现在没有,兴许以后那天会。”
鄢祝融看着她蹙起的眉梢,嘴角有了丝苦笑;“皇后的防患未然,果然面面俱到。”
这种漫说,实在无谓,而且大有无聊的倾向。
溶月实在不想持续它的乏味,她丢开手中满把杂草,站起身,望着皇帝吁口气道:“皇上这次把臣妾召来,到底为了那般?”
没有想到皇后如此直白的发问,鄢祝融微怔,是词穷也是空白,他一时不知如何作答。
对他的反应,溶月了无意外,她说话的语气更是比脸色还要郑重;“皇上对臣妾多有了解,知我秉性实在不堪承担国母之风范。与其诸多挑剔的不圆满,不如想想选个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