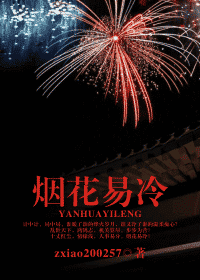烟花三月by绪慈-第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会前来。
偌大京城繁华升平,他与他在这城中共处了三年,然而每回见著慕平他却只能躲著。
慕平成婚后,变得稳重许多,他汲汲营营家中酒肆事,为妻为子努力过活。楚扬自知不该再打扰他,即便慕平在酒肆内偶尔露出的笑让他的心
有多痛,他都无法说服自己再为一段不该有的私念让慕平痛不欲生。
只是……只是……这夜慕平彷徨无助,抱著妻子的尸首在街上落泪,他再无法压抑满腔思念,无法忍受见著他却无法与他同忧同悲的折磨,而
来到了他的身前。
楚扬缓缓抱起慕平,将他放入了沐盆之中。
氤氲热气间清水被染成了血红,那是绣娘的血,灯火下水光上,淡红摇摇晃晃让人触目惊心。
楚扬将慕平的衣衫退下,在水中抽离,他不断提来烧好的水一再一再注入,直至水面清澈澄明再无他留下。
慕平瑟缩著身子,慢慢地、慢慢地将全身埋入水底,让热水烫著他所有肌肤,烫著他的脸、他的眼。
许久许久,久到楚扬觉得恐慌,他慌乱地搭住慕平颈项,将他拉离水面。
慕平不住地咳著,呕出几股呛入喉际的热水。
“你这是为何?!”楚扬难掩心伤,红了眼眶。
“楚大哥……你觉得……我是个废物对吧……”慕平空洞的眸中除了不断落下的泪什么也不剩了,绣娘的死带走他仅有的一切。
“你怎会是废物。”楚扬在沐盆之外蹲了下来,相同的高度,他望进慕平的眼,熟稔的容颜,是他这生最瑰美的遗憾。
“我救不了绣娘的爹,害死了绣娘。我败光慕家所有祖产,辜负爹娘冀望。这辈子一事无成,是个废物。”慕平说著。
“你不是废物。”楚扬抚著慕平苍白凹陷的脸颊,心痛莫名。
“楚大哥……对我好的……就只剩你了……”
“只要你肯点头,我这生这世都会守在你身旁。”楚扬如此说著。
然而楚扬此言一出,慕平却别过了脸。慕平涌上心头的泪不肯停歇,即便他闭上了眼仍无法阻止。他心已碎,再无法全。
楚扬的誓言让慕平想起那年情境,楚扬从来执著、从来勇敢,一段不能启齿的爱恋,楚扬开口对他说了。
心之所系,唯君而已。
他想著,却只能落泪。他没有像楚扬般的勇气承认一切,他只记得他为男子,无法接受楚扬的心意。
“我累了……”慕平说著。
许久许久,楚扬退出了房,但他没有走远,仍在屋外守著。
慕平觉得自己负了两个人,一是绣娘、一是楚扬。
从来从来,他的心便只让楚扬占据,然而他却娶了绣娘,而后离弃了那年的扬州,将一切抛落了下。
他从来怯懦。
绣娘下葬后,屋子里更显冷清。没有下人打理的宅第,才几日光景,便生了杂草藤蔓。
冬里的一场雪,无声无息落在荒废了的庭园中,屋子里,即使白昼仍然幽暗,风起时,刺骨的寒呼啸著,然而无论卷得多大声,却无人相应。
楚扬由不再上锁的大门走入,提著个竹篓,踏著皑皑白雪,进了没点上灯的内院。
慕平穿著袭白衣默默地站在阴暗空旷的屋里,望著屋外不停落下的雪,未有言语。
“平儿。”楚扬始终忧心慕平如此异样神情。慕平的心里,只有早已过世的妻子,慕平的漠然,使得他这处理绣娘身后事的外人无奈难堪。
“楚大哥……我听见绣娘的声音……”衣诀翻飞、扬转如云,慕平的白衣是为妻守丧之服。
楚扬的心一再一再地受慕平所创,他始终不懂,为何慕平心里惦著的不能是他。
“楚大哥……”慕平回过了头,淡淡地凝视楚扬。
楚扬不明白慕平那一声声的叫唤里,还有什么存在。每回、每回,慕平总是这般呼喊著他,但那声如旧呼唤,却只让他神伤。
他只能想著慕平,慕平却将心思给了另一个人忘却他的存在,每当此时,他为慕平倾心付出所作的一切,就反过头来狠狠地嘲笑著他。
楚扬在庭阶前止住步伐,胸口疼得让他无法动弹。
然而,慕平却看不见他,慕平朦胧了的眸子早已空洞,他迎面而来,与楚扬擦肩而过,他仍寻找著绣娘。他的眼里不愿存下楚扬。
“我……我为你带了点东西来……”发颤的手执不住竹篓,在慕平对他视若无睹后,楚扬手中的篓子掉落了地。
当慕平伤痛,只要慕平希望,他会用尽一切气力为他,只盼他能开怀。但慕平却从未由那一头,走至他的身旁。
慕平走后许久许久,楚扬才得弯下腰,拾起地上竹篓。
他深深吸了一口气,些微颤著的双唇强忍伤痛,扬起那对蓝眸,在这荒凉的宅子内,继续寻找慕平的身影。
从来从来,他就没间断过对慕平的思念,自回京城,他便总是远远地凝视著慕平。酒街、酒肆,一切慕平出入之所,他都曾经踏足。
他本打定主意远远地,只远远地,不想打扰到慕平。然而上元灯节他却见到了慕平的泪。他心疼、他制止不住,于是唐突地在慕平眼前出现。
他想对慕平说他始终还是惦记著他的,但慕平从不抬头看他。
于是,他的心更疼了。
于是……于是……他后悔起自己那夜过于突兀的出现……
过了些时候再回到宅院时,慕平倒在庭院石亭之内双目紧闭,神色苍白身形消瘦。
一壶烫好的酒由楚扬手中滑落,瓶身碎裂酒洒了一地。楚扬慌乱奔至慕平身旁,猛烈地摇晃著他。
“平儿……平儿……”楚扬探著他的鼻息,以为慕平将离他而去。
慕平睁开了双眸,而后又缓缓垂下。
楚扬的心如同被狠狠槌了一拳,慕平静止不动的身影,让他以为他猝然远离。差些他便欲抽出怀中匕首,随慕平而去。他经不起这般的吓,那
太为骇人,他无法承受。
紧紧地揽住慕平,楚扬发颤著。
稍晚,楚扬由家中收拾了些细软再回到慕平身边,如今能看顾慕平的人唯有他了,他只能留在慕平身边紧紧跟随著慕平,不让慕平有任何意外
。
只是,慕平有意无意仍闪躲著,即便楚扬如何悉心慰藉,慕平就是迂迂回回,将楚扬拒于心门之外越退越远。
数日之后,与慕平同住于京城的姐姐慕十儿跨门造访。
十儿一张素颜未上胭脂水粉,无血色的容颜,失了当日慕家里的娇嗔霸气,为人妇的她垂首敛眉,神情肃然。
十儿见了慕平模样,叹了口气,亦知朝中朋党之乱累及了他,使他丧失所有,甚至赔了妻子的一条命。
十儿由怀中拿出一封家里来的信,放在桌上递给慕平。“娘捎来的,爹自京城回去后,郁闷成疾发病倒地。大夫说爹时日不久矣,娘意思是让
我们几个姐弟尽早回乡还赶得及看爹。但娘言语中提及了你,爹却又再发火,激动得几度晕厥。”
慕平静静听著。
“我与几位姐姐联络好了,打算一一回扬州。你呢?”十儿问著。
慕平不语。
十儿等了许久,等不著慕平的回答,她叹了口气,举步离去。
临走前,十儿说了:“慕家如今会落得如此,你十姐夫难辞其咎。他在你几度拿钱营救丈人时从中图利不少,我被蒙在鼓里,待上元夜后才全
然发现。为了这事,几番争执下他休了我,没察觉他是如此狼心狗肺之人让你受骗上当,十姐难辞其咎。爹那头,十姐跟几个姐姐会为你求情
,叫爹别那么狠心与你断绝关系,让你在外头漂泊回不了家。我们相约回扬州,船期也定了,初十那日渡口相等,你看是要卖了这宅子还是怎
么著,初十往渡口去吧。”
十儿离开时恰巧见著了入内的楚扬,她惊讶地看著楚扬愣著了。
楚扬只是淡然瞧了十儿一眼,便往慕平身边而去。
“已经很晚,你该歇息了。”楚扬对慕平说著。
慕平仍是睁著一双茫然的眼望著他,开不了口对谁说些什么。
“你是楚扬?!”十儿喊著。她虽知楚扬亦在京城之内,然从不知此人便在慕平身旁。
楚扬只对十儿点了个头,没有太多情绪浮现,接著低头对慕平道:“我晚些再来。”他转身往内堂走去,对这座宅第了若指掌的他无须任何人
指引,自个儿离了去。
十儿难掩心中震惊,回到了慕平身旁。难以置信的她,语出惊人对慕平道:“你可知朋党之争,带头为东厂铲平异己的是谁?”
十儿指著楚扬离去的方向,怒道:“便是楚家人。”
慕平的眼只眨了一下,他泪早已流乾的心中,早不复任何爱恨。
人都已死,是谁又有何谓。
夜里慕平突然转醒,谁家猫儿的叫声传进了他的耳里,那像极了婴孩的啼哭。
他的孩儿。
无法入眠的他坐在屋外台阶上,不久楚扬来了。楚扬凝视著他的眼中有著浅浅笑意,却泛著薄薄泪光。
突然间,慕平顿悟了。只因他一人,却害惨了两个爱著他的人。
他的罪孽在累积,楚扬越是痴狂,越是掏心掏肺,他越是在害楚扬。他不过是个鄙下之人,从无长志、亦无长才,楚扬爱著他,换来的只会是
世俗不容,他知道自己会毁了楚扬一生。
楚家声望正值如日中天之际,朋党之争后又要是另一番辉煌功业开展,楚扬居于扬州时空有一身抱负无处舒展,如今楚家人好不容易接纳楚扬
,楚扬日后定能大展抱负在官场崭露头角。
然而该为将来拼命往上的楚扬,现下一双眼瞳却只是痴然望他。楚扬全身陷下了,没有起身的打算。
慕平明白,自己的存在只会碍著楚扬。他是个泥窟,在他身旁的人,见不著清明一日,绣娘已是如此,他不愿楚扬如是。
楚扬若留在他身旁,这生便将与他一般扰攘平庸地过。他的泪无声无息之际又再落下,他不想害惨楚扬。
“我……买了些清粥来……正热著……”楚扬站在慕平身前,他不能靠慕平太近,他怕靠得太近,慕平又会转身自他身旁远离。
“楚大哥,你还弹琴么?”慕平昂首仰望楚扬。
“……许久未弹了。”楚扬回答。
“我想听你弹琴。”慕平说著。
那夜为了慕平一句话,楚扬返回家中携了不知是谁的琴,往回好些时辰路程,仓促地回到慕平身边。只要是慕平所希望,他皆想为他完成。
厢房内,窗敞著,风有些冷。
一张音色陌生的琴,一壶温热的酒、一对色泽温润的青瓷杯,一对异地相逢的老友。
慕平坐于窗台之上,饮落陈年花酿,听著慕平十指下轻柔声调。时光似乎又回到了当年的扬州城,那道墙下,那个小亭内,偶尔掺杂著福伯前
来探视却止于远处的细碎脚步声。
那年的无忧无虑,令人心安平静。
楚扬沉稳的笑颜缓缓展露,楚家的宅第内,是慕平唯一能放心停歇之所。
而后当夜深他睡了去,楚扬每隔一阵便会摇醒他提醒著时刻不早,该是回自个儿房里歇息的时候。每当他在众人沉睡时分安然回到幕府内没被
发觉,他与楚扬无人阻碍的交情便愈益浓厚。
多少年情谊滋长,楚扬的琴声变了,那一曲一调中开始有著惆怅,有著他所无法理解的情愁。
“曲子……叫什么名字呢?”多年前慕平曾问过,但楚扬不答。
正抚著琴的楚扬停了下琴音,时至今日,那曲的名他仍是无法开口。自在京城遇见了慕平之后,楚扬虽得以留在慕平身旁,然而慕平的闪躲再
再说著他仍记得新婚那夜他对他所作的错事。
曲的名,他真是开不了口。
那代表太大的奢望,一个无法成真的妄想。
“楚大哥的琴艺,这些年怎么竟有些退了。”慕平亦停下手中酒杯。
“不弹了。”楚扬淡淡回答。
“为何不弹?”
“我这曲,只弹予你听。离了扬州,没了琴,便再无心了。”
我这曲,只弹予你听。
楚扬说出的一字一句,在慕平胸口来回碰撞,令慕平疼著。
“你的酒量这些年间倒是好了。”楚扬说著。
“是啊,好许多了。”慕平执起钟爱的青瓷杯,浅酌花酿。
桂花的香在厢房里飘著,浓郁深沉甘甜润滑的酒液,清而不浊犹若白水,然而一旦入喉,却化得凶猛,如同蜂针刺入以疼,如同烈火烧尽肺腑
。一口一口,纵叫人痛不欲生,却也甘愿。
情爱的浓,就如此酒。伤过了,痛过了,除了那些余韵,就再无其他。
只是明知伤身无益,为何还有人要往火里跳,尽管飞蛾扑火焚烧殆尽,却也执著,从不肯放手。
累了,慕平卧回床榻之上,昏昏沉沉地阖上眼睡去。
楚扬再度扬起琴声,细细绵绵,皆是温柔声调。
慕平听在耳里,叹息在心底。
是夜深沉寂浓时,琴音静止了。楚扬停下因久未弄弦而被琴弦所伤的十指,坐于慕平曾坐上的那处窗台,喝著慕平方前饮下的花酿,让落喉的
猛烈炽焰焚烧他五脏六腑。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