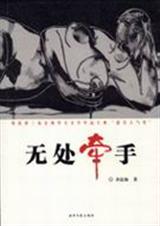无处躲藏-第1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吴月认识一些字,可是他写了什么她不知道,只知道他写了一本又一本的笔记,笔记上全是图和复杂的数字。据说蒋士明的父亲是大学里的教授,而他是大学生,学问很好,天上飞的,地上跑的都知道。谟族的女孩子决不扭扭捏捏,天生就有股爽朗利索的气质,就像数学算式一样明确。她跟所有姐妹大声说,我就要嫁给他。
年轻姑娘主动表明心意,很难有人不被打动。父亲被打成了右派,眼看着回城无望,身边的人陆续和当地的姑娘结婚,生孩子,蒋士明也渐渐死了心,顺理成章的接受了吴月的心意。
毕竟,她是一个怎么都挑不出毛病的女孩。蒋士明之前从来没见过那么漂亮的姑娘,她身上有着一股天然的不经雕琢的美丽;而且聪明得让人震惊,他借给她看的书,她很快就能看完并且背出来,基本上过目不忘。
如果没办法回城的话,和她在一起过日子,似乎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在那个时候的吴维以的印象中,对父亲的印象并不像后来那么冰冷。父亲读书很多,非常斯文,总是微笑着的,对谁都彬彬有礼的样子。他带着眼镜,薄薄的镜片后是一双聪明睿智的眼睛。有什么事情,所有人都会来找他商量。
很多个晚上,父亲把他抱在膝盖上,教他认字,较他算术。他很快的得出答案之后,他就亲他的脸,说:果然是我的儿子,这么聪明。
三岁的孩子通常不会记住那么多,可他偏偏记得。根本忘不掉。
那是他跟父亲相处的最后一段时间。
记得那时候,父亲非常忙碌。他背着很多工具天天上山,深夜才回来,中午也不回来吃饭,母亲就给他送饭去,母亲很高兴的抱着他说:他在设计引水渠的路线。有了引水渠,我们就有更多的水田,种更多的稻子,大家就不会再挨饿了。
父亲每天晚上都不睡觉,在桐油灯下画画写写。母亲心痛得直哭,却不敢让他看见,背过身去,悄悄往水碗里再加了一勺白糖,然后端给他。
他画出来的图弯弯拐拐的,但是很好看。大队队长看了不满意,说太费人力物力;父亲据理力争,拍着桌子说:不能改,再改的话,水流太急,会决堤的!
第二年开春前水渠终于修好了,大片的田地被开垦出来。母亲还来不及为他骄傲,他已经接到了返城的消息。本来都已经绝望,中央的命令层层下达到沅西,高音喇叭一座山一座山的喊过来:……知青按照工作调动处理,分批予以调回。调动遵循以下的原则……
大返城开始了。
一个人的命运和一个国家的命运比起来不过是沧海一粟,但对于很多人而言,这就是一辈子的生离死别。
父母是怎么生离死别的吴维以不可能知道,只记得父亲临走时说:我会回来接你们。
母亲没有像别人那么哭,她仿佛早就预料到了,微笑着回答:好,我等你。
这一等就是两年半。信写了一封又一封,电报发了一份又一分,去二十里地远的镇上打电话,走了一趟又一趟,最后终于得到一个模模糊糊的地址。
有了地址就好办了,仿佛前景光明一片。谟族姑娘最不缺的就是勇往直前的勇气。两三年攒下来的钱当作路费足够了,还可以换上两件新衣服。
吴维以平生第一次坐了火车,绿皮火车,车厢散发着新漆的味道。从来没有见到过那么多人,大家提着笨重的行李,穿着同样颜色的衣服,但说话的口音却各不相同。
从西到东绵延两千多公里的距离,中国的风光一览无余,真是山河壮丽。
从来不曾出过远门的年轻女子带着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千里奔波,无论如何都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什么都要钱,偏偏最缺的就是钱。听不懂别人的话,自己说话别人也听不懂。城市那么大,街道太宽,路灯太多,商店太多,每样东西都没见过,墙壁上贴着大幅海报,听说那是电影;平时偶尔才能看到一眼的汽车现在满大街都是;小箱子里自动传出来一串一串的声音,据说那是收音机……起初觉得新鲜,一天走下来,看花了眼,迷了路,脚也开始酸疼。母子俩抱头坐在路边的公园里,沉默地看着夕阳缓缓沉下去。
和这个城市格格不入。不知道明天该怎么办。
吴维以开始害怕,拉她的衣角,轻声问:阿妈,找不到阿爸怎么办?
不会的。能找到。
这个时候,他们看到了他。怀里抱着一个婴儿,一个女人挽着她的手。从容的从公园中的小路上。那种从容是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完全表达了“我是这个城市的人”的那种姿态。
那是意料之外的一幕,母亲没有说话,死死盯着他,下一秒就冲了过去。吴维以傻傻看着。他们衣着光鲜,和他不一样。那是一个群体和一个群体之间的差距。他不知道母亲和父亲说了什么,只看到父亲伸手推开她,和身边的女人一同离开,背影消失在夕阳里。母亲蹲下去,捂着脸哭。
漫长的等待时间里,母亲从来没有哭过。她不是一个爱哭的女人。虽然寨子里人人都在私下议论说“命真苦,男人不要她了”之类的感叹,但她没有掉过一滴眼泪,只是埋头做自己的事情。她不是那种任人轻贱的女人。
可如今她在哭。她瘦削苍白的面庞没有泪水,嘴一张一合,却没有哭出声音,那是绝望的干嚎。她仿佛一瞬间老了十岁。
那种无助和撕心裂肺,至今记忆犹新。
母亲瘫坐在公园冰冷的石板上瑟瑟发抖,和他一般高。吴维以抱着她:阿妈,别哭了。你还有我。
母亲忽然不哭了,反手抱着他,亲他的脸:是啊,我还有你。我早该知道,一个人的人心变化起来,是连禽兽都不如的。阿妈不哭了。
第二天他们在他单位外又遇到了他一次。曾经的那个父亲从有着门卫的大院子里出来,嫌恶的看一眼站在路边的他们,只说了三句话。
我没这个儿子。我跟你们一点关系都没有。你们从哪里来回哪里去。
他们在这个大城市里逗留三天后,没了钱,不得已回了沅西。足足两天两夜的火车,她一句话不说,一口饭没吃,甚至连水都没喝一口。
没有人知道她怎么撑着回了沅西。当天晚上她发起了高烧,什么都糊涂了,什么都说。最后终于累了,最后昏迷不醒,半夜的时候她在月光下,把正在熟睡的吴维以抱出了屋子,放在树下的大石块上。她倚门而坐,最后去灶台拿了把火,往屋子里一扔。她躺回床上去,看着火苗舞动起来,烧掉了屋子里所有的书,曾经是他的书。房屋的木架在她眼前轰然坍塌。
木质结构的屋子见风就燃,那场火没有控制住,烧掉了整个屋子,他在睡梦中差点被烧死,还是邻居家发现得及时,救回了他,却没有救回方圆三百里内那个最漂亮的姑娘。
清晨的第一束阳光洒进山寨,均匀洒落在每个角落,包括那间依稀看得出本来结构但已全部毁灭的小屋子上。
只有黑乎乎的残垣断壁和置身其中孤零零的小男孩。他伸手出去,碰了碰那张碳化的木床。
有东西轰然垮塌。炙热的烟尘迎面扑来。
什么都看不清了,什么都——没有了。
'二十一'
旧年一过完,工地上就进入前所未有的繁忙期。导流洞也提前半个月施工完成,验收过关。辛苦一年的众人拍手相庆。一个项目结束自然要喝酒庆祝,干脆就在洞内干了大碗酒,宛如古代的英雄侠客,豪气干云。等不到众人四溢的酒香散去,爽朗的笑声回音传来,大江截流的准备工作也逐渐展开。
这一代是所谓的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受东南亚季风影响很大,春季湿润,夏季多雨,每年的汛期大致从四月中旬开始。汛期来临之前截流江水迫在眉睫,工程组进行了几番资源调整,大量的人力物力都调配到了截流现场。
因为斯瓦特河面较窄,施工难度不大,设计中采取河床一次拦断的方式。大量的石料运来,几千立方米的石料石渣在江边堆积如山,并且还以高密度不停的运送过来。实际的测量工作也穿插着展开,吴维以每天在工地现场和实验室来回数趟,几十立方米的混凝模块倒入江中,再捞起来,测量记录数据,一个不拉的全部要看,随时做好应对的准备。
一辆大型的运输车沿着路过来,吴维以退后了两步,待车停稳后同开车人打招呼:“老袁,现在身体好点了吗?”
袁祥从窗户里探出头来,挥舞了下手臂,一张脸上全是灰:“没事,早没事了。我现在好得很呢。”
吴维以颔首:“那就好。”
“吴总你让一让,我准备倒车。这里乱七八糟的,到处都是石头,磕磕碰碰的,小心受伤呢。”
“是的,安全重于泰山。”
边说边转抬起目光,下意识的去寻找江边高台上那块注意安全的高大警示语牌。牌子自然是完好无损的,旁边正在修缮的厂房也基本上完工,厂房前有两个熟悉的身影在附近的树荫下交谈。走得近一点,果然是陆筠和周旭。
印象中他们两个人,只要有时间总在一起的。陆筠似乎在笑着说些什么,点头之后又摇头,把手里的文件夹交给了周旭然后转身朝另一个方向离开;周旭在她离开后却没有动,低着头颇为认真的看手里的东西。
吴维以若有所思,静静看了二人片刻,沿着石阶走了上去。数步之远时叫他:“周旭。”
因为现场施工的机械声非常大,吴维以刻意扬高了声音,可声音没传到被呼喊者的耳中,吴维以摇摇头,来到他对面,再叫了一声。周旭这下子听得真切,抬头看见来人,立刻笑着招呼:“吴总?我刚想过去找你。”
他把手里的文件地给他,吴维以看了看,是一些水电站的资料,密密麻麻的都是英文和公式,空白处有一些铅笔写好的批注。
“陆筠给你的?”
周旭说:“这是以前的一些老的水文资料,原始文件太多,当年也没人仔细看。我昨天从纸堆里找出来,我看一下,觉得有点意思,不过里面有几个小地方我不太明白,小筠就帮我翻译了一下。”
“帮你翻译是吗,以后翻译之类的事情也找我帮忙,”吴维以表情难以察觉的一变,随即正色看他:“这段时间你跟陆筠经常在一起,每天都会见面?”
周旭有一瞬间的砂岩。通常情况下,吴维以找他都是为了公事,难得这样说起陆筠。工地上已经有了不少关于他们俩的玩笑,没有什么恶意,多是闲聊时的玩笑,不外乎“吴总对待小陆真是难得的好”、“两个人走在一起挺配的”云云;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往往也是实情。他对她,的确不一般。周旭一默,怪异的酸楚浮上心头。心知跟领导争辩起来不是个明智的选择,可忍不住一句话还是出了口。
“我们是见面很多。小筠说她这段时间比以前轻松,愿意帮我的忙,我自然求之不得。我跟她相知相交这么多年的感情,无论怎么说,是我们两个人的事情。吴总,你那么忙,实在没有必要过问这种小事了。”
尖锐的回答是意料之内的,吴维以无意在这个话题上继续下去,示意周旭跟他一起去厂房里看看;地上全是水管和一捆捆的电线,两人绕过去后他才缓慢地,字斟句酌地开口:“这番话你听了会迷惑是正常的。不过我有我的考虑。我希望你多她在一起,她在什么地方,她在做什么事情,甚至日常生活中的小事,这些你都要看在眼底。”
周旭完全拿不准他的意思,但感觉得出来他话里的分量:“你不说我也会注意的,不过你为什么跟我说这个?我不懂。”
“我也同样不明白,”吴维以抬头静静看着天空。没有空气污染,这里的天空碧蓝而纯净,宛若出见世面的小姑娘,“刚刚我的话是请求。”
话里有着明显的深深的焦灼,如果是另外一个人说出来,给人的感觉恐怕是忧虑到极点;既然是吴维以说的,那就不可能。他看上去镇定一如往昔,除了紧抿唇角和微蹙的眉头,别人什么都看不出来。周旭迟疑片刻,勉强笑了笑:“请求?”
“当成我给你的任务也可以。总之,不要忘记我的话。”
纵然有千百个问题想问,但猜到他不会回答,便一如平时接受任务的状态:“好。”
吴维以宽慰似的一笑,又说,“陆筠的性格你很了解?”
周旭笑起来:“了解啊。小筠她啊,是那种别人找她帮忙都不会拒绝的,只要有任务拼了命也会做好的性格。大学的时候出去野外考察,她摔了腿,不愿意影响进程,她愣是要着牙坚持,半句喊痛的话都没有。后来到了小镇上找了医生一看,小腿肿得像大象腿。现在还有后遗症,没办法很好的掌握平衡,崎岖的山路走起来有些困难。”
“她很不容易。”吴维以薄唇微微一压,几近叹息的一句话就从唇角飘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