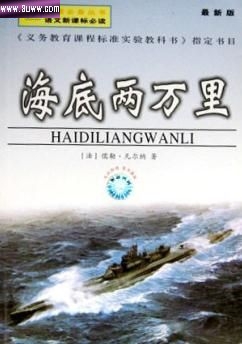�������� + ����-��3��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ϣ�����������Ҷ���磬����һ����˽�½��˽��ߣ��Ա����ֶ�ǿ��������ֻ�����ܺ����Ծ�����ǹ����ˡ�˭��Ҷ���羹���������ļƣ�ƫ���ϵ������������°���������ƽ��֪����
�������˶��Ǵ����ˣ�ǰ���������о���һ�����ף���ֱ˵������˺�����棬��ȴ���ǵ�һ�Ρ�
�������ǰ������գ���֮��Ҷ�����������ðε������ⲻ�⣬ʵ�����ܣ������͵�ֱ�����������Ʒ��Է�ϸ�������ӣ�ѹ�ڴ��ϣ������ɶ��������߶��ߴ�Ϣ��������֪���ͺá�������Ϊ�ҵ����������������Ȥ����ƽ���ֽ�Ӳ����Ů�˵IJ�Զ�ˡ������Ҿ���Ҫ���㡭���ߣ����������صij��ӣ������������͵�������������Ǹ���ר�õ��ͯ������
�����ڰ��У�Ҷ�����߬ס������˫���Ѿ����ף�������ҧ�ƵĴ��䣬Ѫ�黺�������䡣��ʼ���գ���ֻ�Ǹ���ǿ�������ӣ���δ���ⳡ�����еõ��κο�У���ʹȴ������ɽ��������ӿϮ��������˼�������մ���Ĺ���Ҷ���羡�����Դ˿������ϱ���������µ�ʹ�࣬����һת����֪������������ҹ��ʱ�֣������������IJɻ��������
����������ʲô���ԡ�����ʱ�������ָо����ɵ��������ﲻ�ԣ���ôҲץ��ס��Ҷ��������˼���������������һ�����������Եؾ�Ҫֱ�����������ã���
5
������������ѹ���Ϸ�����Ѫ�����������������ȣ���Ҷ����ͻ������һ��������һ�����յͺȵ�����������ʲô��������δ�䣬����һ�ȣ�ȴ������������������һ��һŤ����Ҳ���Ͳ�ס����һйǧ�����ֱ��ȫ�����˳�����
������һй���������ױȵ�����������ֻ���û���������Ͱ�����������������ز���ǿ��Ҷ����ѹ��ԭ�أ�������ŭ���ѵ�ʧ̬�������������Ĺ����µ�������ס�
����Ҷ��������֪�����ǵ�������˼��һ��ֻ�ǹ��������¶ˣ����ǵij��ȱ�����ʱ�������������ڣ���ʹ�������˵����۴�������ˣ�Ҷ���練�������˿���������������ˡ�
��������ʹ�ƿ����ǣ�Ҷ�����䵭����װ���£�����ү���Ա㣬�¹ٻ��й���������ʧ���ˡ���
�������������̵�����������������һ�죬�������������εؽ�Ҷ����һֻ�����ס��Ө�༡������ӡ��������ۣ�����û˵�ߣ���������뿪����
����Ҷ�����ͼ˦����ǰ��������˵Ľ��ƣ���ȴ��ץ�ø���������һɹ������������ƽ������������ү���У����߲��ߣ��ƺ��в�����ү�ϰա���
�������������˵������ȴҲ֪��ǰ������˾��ǽ���֮��������Ҳ��������ڴ˵أ������ǵȺ���֮�١��ļ���������ֻ����ƽ������̾����������ֻ������ҪԽ�������ʲŴ������������û���Ƿ��˵ļ�������ѿ���ֻ�������ڶ��ѡ���
���������ڼ����������ϼ���ѹ��סҶ��磬��ʱ�龰Σ����Ҷ���Ҳû��ϸ�룬��ʱΪ��ת�������������ַ���ʹ�࣬��ȫ����ע����һ��֮�£����̷��֣����ϵļ���ԭ�����������ھ��У�������Ҳ���Ʋ���ƽ����ǰ�������ǰ�ٶ����������ѽ��������Ҷ���������ʱװ���������ѡ�
�����ѹ����û�ٰ�ܾ�Ҷ����ĺ��⣬������ϧ�����ᱡ������Ϊ�ı��ǿ�Щ��Ҷ���缤�ߣ���ʹ�����������ܡ�
����һ��ͨ�˹ؽڣ�Ҷ������������ס�����η���Խ����������֪������ҲҪ����ģ��ο���Ҷ������ĸ�����������������Ц�������ѵĵ����Ϸ�����
�������ҿ�����Ϊ������ա���������Ц��Ц�����ָ���Ҷ����ľ��������һ���ٺ죬����������������
���������벻������Ρ���Ҷ�������ѿ��������ƣ���ȥ�����ۼ���������һһ���𣬴��ݵ�������ү�ھ����¹��������ҳ��ɷ���������������ү���Dz�֪����
��������������˵û���������Ǵ��ˣ���������������֮��
6
��������һ�����ѽ����е��忡�����ٶ����ػ��С�����Ҷ�������в������ţ��־���ŭ����ɫ������ͻȻ���������á�
���������������������������ɥ�������ڹ�ͥ����������ϲŭ������ɫ�Ľ���Ǹ��������Ȼ�ᣬ�۵������˻���֮�䣬��������˭Ҳ�������ϡ�ʮ������������ٹٷ����������Եģ�������ı����磬����������뾡���Ӷ�һһ����ȥ�����ﰵ���֪ɨ���˶������У�ֻ��ʱ�����죬��Ҫ��ر��������ҵĽ�ɽ��
����ƫ�ڴ�ʱ������Ҷ���硣���¼�ʿ��Ʒ�����IJŷ��������ѵõ��Ǽ����������ù��ң�����һ������ӿɱȣ����DZ��ǰ���֮�ˣ�һ����ϲ�����������̽���ؽ�ύ���뽫Ҷ�����������£�˭֪��Ҷ����ȴ�������ͳ���������У�ֻ֪�Ҿ����֣���������ʾ�⣬��������һЦ���ƽ���Զ��
�������ղ��ˣ���ȻҪ����ȥ�������������ĺ���������Ҳû�������϶�����ԥ�����ձ���֯��������Ҫ��Ҷ���������ء�˭֪����ѧʿΪ�˻�����˼�������û��ϳ��ţ�����һ�����˼��ξֶ���ʧ�ܡ���һ�����Ǹ��Ӵ�ŭ�������ײ�������̫���ԣ����Ҷ���磬Ҳֻ����������
����
��������Ҷ�����ŭ���������Ǽ��ǿ��⣬��Ц�ţ�һ�ָ����������嵭Į��������������ºۼ��İו����ӣ���Ҷ���簡Ҷ���磬�����Ǵ��´�����С�º�Ϳ�ˣ�����Ϊ���������һ���ں��ǵ��ӹ���ô�������������뱾�����кθɣ�����ΪʲôҪ���»����������ȥ����
�������㲻���Ѿ�������Ҷ�����峺��˫Ŀ�����˲㺮˪��ŭ�������ǣ��վ���Ƥ����û������������˵���ڡ�
�������ǵ���ô�������Ƽ�Ҷ�����ǿ��ŭ��������������Dz�������һ�ȣ�����Ѹ��ͦ�������������Ƕ���û������Ů���ˡ�����һ��˵��һ�ߴֱ��س�ȥҶ�������£����ɷ�˵�������ڴ��ϱ����¿�ʼ��
����Ҷ���������������ۣ��ܳŵ�����ȫƾһ�ɰ�����ͻ�������ֱ���Ϯ����ŭ����ߺ�������һ���������������һ�Σ��ʹ˻��˹�ȥ��
����
��������Ҷ�������������Ǵ����������������ϱ������ң��ۼ���Ȼ���������Dz�֪��ʱ����Ȼ��ȥ�����ڿյ������ް����Ӱ��
���������������𣬲�һ������������һ�����ĵ�ʹ����Ҳ���۶�һ����ʹ���ϰ��������Ҷ������Ȼһ̾���ٴε������ϡ��Dz���һ�����绢�籪�����ӣ��վ�����Ū�������ѡ�������Ӧ���Ļ�����ʱ���й������ˡ�
�����������������ϲ�Զ����һ�����壬�̹�ӨӨ�����������Ӵ�æ��������ʧ�ġ�
�������Ӷ˷�����������
�����ǵ����������dz���ʱ���Ա����������ᣬ����������Ȩ����һ���������������ԴǷ�Ȥ�ж����䣬��������һ��������µ�Ӣ�䣬�����������ˣ������ٻ���������ѹ����ȥ��������֮����Ȼ������ȴҲͬʱ��֪�����˾��dz���֮�������Ȼ�����س��κ����˾���Լ���˻��⣬���ý�ɽ���������䱾�����κ��������������������·��������������࣬���κ�ɽ������ס����̫������ֻ�ϻ��භô������Ҫ�����û����˱���ȥ����������Ϊ�ѣ�ȴʵ��û�����㡪��
����Ҷ��������������ס���壬�����ӹ�һ˿��Ц��������£���ɣ�Ҫɱ��������������֮�У�����Ҳ��������Բߣ�Ψ��������֮�£�������ʩ����ȴ�����ϲ�������Ҫ���������ò�����Ҷ���繶�ջ���գ����������ˣ��ܴ˳ͷ�������Ҳ�����⡣
����
����˼��������һʱƮԶ�����β�ͻȻ�ѹ����������������DZߣ���֪������Σ�����Щ��֣�����û�����������ѣ�ƽ����ʱ�������Ż����Ӽ��Ĺ�Ա��ͼ���һ���ˡ���
���������Ż����������������Ϥ��Ц���������˻�û��ô������������������ˡ�����
��������һ����Ҷ����������ʹ������ȴ�鶯�糣��ǰ��һ�ƾ���֪���ߣ���̾һ���������������Ѿ��������ˣ���ô����
�������⾲��һ�������������Ρ�������������Ī������������ת��
����
����������Ҫ��ҩô���ұ��������룬��֪��β����ø����ˡ���������ĬȻƬ�̣�Ҳ̾������̹Ȼ���ϣ����糿����������������һЩ����Ҳ�ޣ�������������ǹ����ˣ����´����������㺰���������ҵ�������ʱ�����������ش���ſ��Ž�ȥ��һ��ȥ������ˡ������˷��ģ������������Ҳ��֪������
����Ҷ���������죬��ס�DZ�����Ȼ����������˵���ɣ���һ��һ�⣬���˿������������á���
����
����֨ѽһ����ľ�ž����ƿ������������˽����������������ϣ�Ŀ��б�ӣ���ҩ���ڷ���������ϡ�
����Ҷ�����Ц�����������α���ˣ���������Σ����õõ������ҩ�������Ǿ�����̫�����ˣ���Ը����ô����
�������������ء���������ȫ��һ������æ����ҩ���𣬵ݵ���ͷ���۹ⴥ��Ҷ�����Ȼ�����������������̬�����dz��������Ҽ�����������Ů�ˣ�����һ�ɷ�����������£�����һ�𣬼���ת����ȥ��
���������DZ��������ɡ���Ҷ����ӹ�ҩ���ڱ������м��ѵط��ϣ���ǿЦ������������ͬΪ���ӣ��κ�����ģ������ʵ�����ڼ��ˣ�������Ҫ��Ц����
�����������������£���Ҷ����ǿ��Ц�յ����飬�̲�ס����һ������ˣ��⾿������ô���£���˭�ҽ����������ͷ�ϣ�������ʶ���㣬һ�۱��Ƴ�Ҷ�������DZ��ȣ�������Ը��
����Ҷ����˼��ǰ�����������Ȼ��������£�����֪���ˣ�ֻ�»������������֮�֡��������Ȼ�Ѿ����������Ƕ�������
�������������˵�ͷ��Ҳ���Ծ������Ҳµ��ˡ���Բ������֮�ڣ�Ҳֻ�����ң����ᡣ���˷�Ǹ��ң�ȴΪ�β����������ɵ������裿��
��������������Ը���ѡ���Ҷ���羲���������������������ڻ�����ת�������������ƾܲ�������������ƴ�����Dz����ԣ�����û���ã�Ҳ�Dz�мΪ������Ҷ�������ж����ѵ��������������ϣ���һ����Ů�����ţ��ܹ��ô����
��������������һ�٣�����������������֪�������������ģ��������ʥ�ϳ谮��Ϊ�β���Ѱ֤�ݣ�˽�����࣬�ö�������δ�ᣬ������������
����������ı��֮�⣬����ºεȻ��ܣ�Ҷ���絹�ϲ���������Ҳ���֪���Ҹ�ֱ˵������������ע�������ۣ�������������ѵ����£�������������������Σ���Ҳ֪����������������һֱδϢ���м��������Ǩ��βС�ˣ�һ�������Σ�һ�������ɣ����������������ε�Ů����Ҳ����������������Щ�����������ԭ����������ҷ��𣬾�˵��ǰ������֮�ң���������ʱ���ɣ������˸��������֮���¡�����Щ������һ�����ĺ��̺��壬̫ƽ���£�����֪�Ӻ�˵���ˣ�����������Ȼ���Ҳ��Dz�֪��Ҫ��֤�ݣ���Ҳ����̫�ѣ���������
����
������˵�ü�����Ҷ��������������ʹ����Ҫ����һ����ʹ��ҡҡ������������æ��ס�������˱��裬����Щ�䣬Ҳ�˲����ˣ����ڴ��߷��£�Ҷ������ּ����������������ˣ�ı����������½�����������ȫ֮�������������ж�λ�����Ҵ�ʱ��֤�����࣬ʥ�ϱض���ŭ����ּ�顪���ⲻ�Ƿ��Ƶö�������ô�����߶���������������ʥ����̫Ѝ����������δЪ����������ţ����������â���£�˭Ӯ˭���䲻��֪���������ҳ�һ�ţ�ȴ�DZ�Ȼ���ɣ������֣�����ô�����ܿ������¾�����һ�ԣ���������Ѫ���ɺӣ���������ô����
����˵�����Ҷ�����������ƣ�룬����ĿС����������Ĭ�����������ã��ŵ�������һ�䣺���Ǵ��˾���Ҫװ����֪�����ۿ��Ŷ����Ƴɣ���ȡ��λ�ˣ������Ҳ�����ڰ�����������
����
���������ǡ���Ҷ���������۾�����ס���ߵ�Ļ�ţ�ҡ��ҡͷ������֮�������̣�ֻ�Dz�Ը���¼��Ƶ��������֮����ʥ�϶��Ҷ�����ɽ���������ѱ�����һ��������Ҫʱ������������Ȩλ������ᾡȫ�������������˴�ʧ�ˣ���չ���á����������ϵ���ʱ���������ɣ��������⣬����Ҷ�ӷ�����֪�����������ް���������������أ���˶��ѣ���
�������ø�����������أ�����������Ȼ��ɫ�����ſ�Ҷ���磬վ�ڴ�ǰ����������Ҿȥ������ʶ����һ�����࣬ƽ��ֻ�������Ǹ������ĺù٣����ղ�֪�����ػ����£����Ȼֺ꣬���������ǧ�����Ըһ��������ˣ��������ǣ������Ҳ���ϧ����
����Ҷ���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