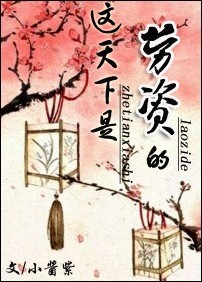这天真蓝啊(穿)-第1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说累了,坐在坡地上,身边的少年轻声哼唱,我闭上眼睛享受着秋日午后的阳光,耳边是悠扬低缓的
歌声。
交待鹿土一些事情,他便先回去,我独自坐到天黑,脚下的村落闪着点点烛灯的光。
慢慢往回走时,前方忽然闪出两个身影,一高大魁梧,一矮小瘦弱。我轻手轻脚隐于一棵古树后,凝
神屏气注视,借着月光,但见魁梧者右手持一把锋利怪异的刀,刀在月下发出青色的光,无形的杀气流动
于刀锋上,“好刀,只是此刀做武器真少见”,我心中暗忖。矮小瘦弱者赤手空拳一身黑中有白打扮。月
下,逼人的刀光映入矮小者的眼睛,那眼中闪现不甘、恐惧,嘴里不时发出绝望的低喘。持刀壮汉前进一
步,矮小者瑟缩后退一步,终无路可退,壮汉欺身向前,刀身反出月光,杀气更盛,只觉寒光划过,我痛
苦的别过头心里默念“永别了,兄弟。”惨叫声过后,一切恢复平静,地上蜿蜒出艳红的血。
我终忍不住跑了出去,大声说道:“卓大叔你这猪杀的不错,一刀毙命。”别人都是绑猪痛杀,他是
放猪追杀,老卓这猪杀的有个性。
卓城提着把大菜刀笑道:“大侄子过奖了。
月朗星稀杀猪夜,我抬头望着头顶的月,“以后写本杀猪纪实,就叫它菜刀明月猪。”
第二天,我起个大早做了一锅香喷喷的清焖|乳猪肉。
做好后,我盛了一大碗端到苏芙蓉的屋里。
“草草,不知你口味如何,所以我把肉清焖了,不腻,快吃。”
“小雄儿,你……做的?”
“草草,在下的长处多着呢,日后有你知道的,对了,味道如何?”
“是猪肉味。”
“草草,我原打算做出驴肉味。”
“你把……哪一个杀了。”
“黑豹。”
“舍得?”
“早就想杀了。”人都强养,还养猪。
“我……原以为你……很喜欢猪。”我就这么容易让人误会和猪是近亲?
我纠正道:“错,是很喜欢吃猪。”
他低头吃肉,吃的很慢,未再说话。
我的手艺把卓家人唬的一愣愣的,四口人转着圈的夸我。
天上密布着灰色的云,秋雨要来。
吃过饭,我自报奋勇和卓新去隔壁的张家送清焖肉。小肉球在啃过猪尾巴后和我前嫌尽释,两胖子手
拉手去了张家。
“张大叔、小玉,娘让我送肉来了。”卓新未到屋门口便喊。
一个四十多岁中年汉子迎了出来,接过装肉的坛子。小铅球从偏屋跑出来,两个小家伙一见面就热络
的扭打成一团
“小新,多谢你娘。”中年汉子又侧头看我,“这位兄弟是?我记起了,你是那日问路的公子。”
难怪我也觉得他面熟,急忙拱手“那日多谢相告,在下英浩,现借住卓大叔家。”
“不必客气,在下张炯,英公子屋里请。”张炯中等身材,留着黑色短髯,一身庄稼人的打扮。
“张大叔,请。”
“小玉说,小新家来了位胖大哥,想必是英公子。”张炯边倒水边说。
我站起来接过水碗,“张大叔,你还是叫我英浩,或是叫声大侄子也成。”
“哈……哈……,好。”
扫了一眼屋子,摆设略显寒酸,一张缺角断腿的桌子配了两把破凳子,床上的被是补丁连着补丁。
张炯坐到我对面,“那天的病人身体好了吗?”
“已好。”
带着水气的风从半闭的窗户吹起来,在喝光五碗井水后,经过我的迂回打探,张家的情况,我了解个
大概。张炯,四十有五,中年得女,前年丧妻,仍未再娶。
话从他家聊到他。
“张大叔,你会化金子?”我睁大眼睛问。此趟送肉竟遇如此高人,真乃天助我也。
他答道:“早年学过,如今,化金子的傢什还在偏屋放着。”
“如果此时有人找大叔化金子,大叔可化得了?”
“化得了。”
“太好了。”我激动的忘乎所以。
“大侄子你?”张炯脸带疑问。
我在怀里摸了又摸,掏出金锁,推到他面前,“大叔,这是我小时所带之物,无奈家道中落,想把它
化了,以做度日之需。”凭张炯和卓家的关系必不会拐了金锁,如此偏僻地更不会有人识得此锁。
他拿起看了看,”好金,手工也精细,想是大侄子祖传之物,真要化它。”
我毫不迟疑的回答:“是,留它已无用。”
他掂掂金锁又问:“大侄子信得过我。”
“张大叔哪里话,信不过,何必相托。”我盯着他说。
“大侄子说的好,但不知想化成何物?”
“金豆。”
“好,大侄子,明日此时,来取。”
“一言为定。”
明晃晃的拿个金锁出去容易招惹事非,我一直惦记着如何神不知鬼不觉的让它物尽其用,能流通的才
是好东西,今天算遂了心愿。
自张家出来,天上下起了雨,一场秋雨一场凉。
苏芙蓉依在卓家正屋的窗前,我打声招呼进了正屋,屋里只有卓城和苏芙蓉。
“英大侄子,回来了。”
“是,回来了。”我靠到桌子上。
“英浩,我想……我们……明日一早回去。”旁边的苏芙蓉说。
我看向他,“明日?芙蓉,太急了吧,你的身体还没全好。”得为我的金豆着想。
卓城跟着附和,“英大侄说的对,芙蓉多住几日。”
“多谢……大叔,我……已好了,打扰多时,该回去。”他说的不容反驳。
“大叔要多住几日,芙蓉一定要走,如此,后日一早走,可否?”我提出折衷。
他们二人想想,点头应允。
“大叔你会吹笛子?”我一抬眼看见对面墙上挂着个黑色木笛。
“不会,装饰之用。”
“大叔,我可否一看。”说此话时笛已在手中。
笛子很普通,看不出是何木所制,笛上刻一个小小的“柳”字,已经磨的有些模糊。
“大叔,我可否一吹。”说此话时笛子已贴上我的嘴。
试吹了一会儿,好像听见李白的惨叫声。苏芙蓉的嘴抖了抖,身子向门口挪了挪。
“献丑了。”我四下点头说。
两人跟着点头没说话。
“芙蓉,你也吹一曲?”
“不会。”
“吹一曲吧。”
……
“好。”他有些犹豫的接过笛子。
“英大侄子我先出去了。”卓城有些落荒而逃的架势。
“英大叔,听芙蓉吹一曲再走。”我盛情挽留。
“我忽然想起有急事。”他一刻未停闪出屋外。
“小雄儿,我……吹了。”
“吹吧。”我坐在椅子上翘起二郎腿。
……
“救命啊……。”卓家的正屋响起惨叫声,其中还伴着用语言无法形容的声音。
谁说的,长的美就一定会吹笛子。
第 22 章
傍晚,雨停,风凉,炊烟起。
我搭在东屋的窗沿上,窗下小肉球逗弄着一只花鸡。
“小新,你家的鸡?”
“是我养的,原来还有一只,可几日前不见了,娘说送人了。”
“唉,可怜!”我叹一声,为送人那只,更为眼前这只。
“小新!”张家的小玉隔着篱笆喊。
小肉球饶过手里的鸡,脑门顶着新添的伤,乐呵呵的跑出去。院外两个小东西的手拉在一起,蹦蹦跳
跳玩着简单的游戏,单纯的心快乐而幸福。
“小雄儿,看何?”苏芙蓉在我背后拍了下。
我没回头,轻说道:“看幸福。”
……
瘸腿的花鸡在篱笆边啄食,几片树叶无声落下,少年静默看着依窗边而站的胖子。
盼了一晚,终盼到手捧金豆儿。
“一、二、三、……十五。”我用手指把一个个金豆子打着滚的摸过。摸完,拿出两个欲放到张炯的
手里,“张大叔,这是小侄的心意,还望收下。”
张炯慌忙推辞,“大侄子,你这是何意,此物我万万收不得。”
“张大叔,无须客气,您老帮我个大忙,这两个豆子全当报酬。”我说的诚恳。
“此报酬太重,太重,收不得,收不得。”他急出了汗,一再摆手推辞。
我把金豆按在他手里,正色道:“大叔,我意已决,不收也要收。”
朴实的汉子低头直叹气,“唉,这……这真的是太重了,大侄子,真的是太重了。”
“大叔一人拉扯小玉不易,日后难免会有用钱的时候,好生收下吧,不为自身想,也要为小玉打算,
何况这本是您应得之物。”我环顾陋室说道。
“英公子,你……你让在下……如何是好。”他有些哽咽。
“张大叔,只不过区区两个金豆子而已。”我笑着拍拍他的手,说声告辞,转身离开。
张炯,看着掌心之物,手缓缓握紧,抬头望去,那人已出了院子。
刻着“富贵齐享,福寿俩全”的金锁化成了金豆子,那坠锁的双股红绳不知丢在何处,红绳上用银丝
线绣出的“秋”字,不曾有人留心看到。
怀揣金豆回到卓家,向鹿土娘借了她家中最细的针、最韧的线。
门窗俱关的西偏屋,我坐在床上,脱下长袍里外端详,最后从前襟处扯下一块补丁,拿起事先备好的
针线对准那块补丁。四五盏茶的工夫,一个做工粗糙但绝对结实的小布袋提在我的手里,袋子上缝着“黄
金白银滚滚来”几个字不说,没人能认出来。小心翼翼的将袋子放入里怀,我躺倒在床上,看着手上带
血的针眼,“这女人的活做起来不易啊。”
一会儿,“这天真蓝啊,这天真蓝啊……。”屋里传出没完没了的歌声。
院里瘸腿的鸡,走的愈加不稳。
东屋的少年趴在窗边,脸带轻笑听着不成调的歌,一片树叶悠悠飘下,少年伸手接住,“秋也该来了
。”
“烟,轻唱一曲如何,很久未听你的远思呤。”正屋里的男人对坐在身边的彩衣女子说道。女子的头
靠在男人宽厚的肩上,轻轻唱起,宛转的歌声只唱予此生相付之人。男人轻揽女子入怀,低头看去,不知
何时她已生了白发。
“城哥,我唱的还好吗?”女子低声问。
“好,和我当日初见烟时唱的一样好。”男人的手抚着怀中人的发。
“烟已老了。”
“烟永是我的烟。”
女子闭上眼睛安静的靠在男人的怀里,院中的柳枝随风轻扬。
“小新,胖大哥在唱歌,我们也唱吧。”
“好,小玉,那我先唱。”
“不行,我先唱。”
“我要先唱。”
“我。”
“我。”
院里肉球和铅球滚在一起,双双变成泥球。
柳树下坐着的黑衣少年,对每日必上演的双球之战视而不见,他将手中的黑木笛在嘴边放了几放,终
吹起来。
“小孟!”
“不要吹了!”
“救命啊!”
“呱呱……!”
卓家喊声四起。
“有这么难听吗?我觉得比英大哥和苏大哥吹的好。”黑衣少年皱眉自语道。
天上不时有云飘过,李白停在树顶叫的神气。
“草草,先别熄灯。”来的早不如来的巧,我抱着枕头窜进东屋。
“小雄儿,时……时辰不早,还有……何事。”
“晚饭吃多了睡不着,这卓大叔真是好客之人,做的如此丰盛。”我边说边往床上摸。
“今日,心情……甚愉悦?”苏芙蓉一条腿搭上床边。
“草草,你看出来了。”我动作自然的越过床边的腿,爬上床,然后一伸脖,嘴里吹出凉风。“这点
灯说话太费蜡。”说完放好枕头躺下,黑暗里看不清苏芙蓉的表情。
“何事……如此高兴?”他躺在我旁边问。
“也没什么,只是今早一起来,忽觉天蓝,豆黄,你很白。”
“哦。”
“草草,你不问我今晚为何与你同床。”眼睛习惯了黑暗,旁边的他侧身看着我。
“为何?”他脸上似有笑。
“不为何,想同床就同床了,哈……哈……。”
……
“哎哟,苏草草!为何打我肚子。”
“不为何,想……打就打了,呵呵。”他翻身背朝我,肩直抖。
我摸摸肚子忍了,谁让咱是男人呢。
夜深时,胖子闭着眼睛流着口水抓住少年的手直啃,边啃边说:“这猪蹄,肉少了点。”
少年被啃醒,好笑的看着,轻轻抽出手,拿过自已多日未洗的布袜塞到胖子嘴里。
这晚,我睡的又香又美,梦里吃了一顿又一顿,早上醒来枕头上俱是口水痕迹,“这嘴里是什么味?
”我边咂嘴边纳闷。
清晨的风有少许凉意,牵着白虎,扛着破被,怀揣卓城起早烙的饼,和苏芙蓉离开鹿土家。临走时小
肉球颇有几分不舍,我捏住他的脸,密授几式打架致胜的绝招,他听的跃跃欲试,卓城则在一旁和苏芙蓉
说着话。
“我要吃猪,我要吃猪……。”我唱着穿过村子,转过小山包,走过上坡路,经过巨石,踏入离开多
日的山谷,身旁的苏芙蓉只笑不语。
回去的路经过离仕潭,秋风吹皱的一潭碧水映进眼里, 一个男人赤足坐在潭边,一袭粉衣,黑发飘
散。
苏芙蓉站定看向男人。
“苏,我回来了。”男人对着潭水说道。
“哦。”苏芙蓉缓缓走过去。
男人站起来回过身,挑眉一笑,扬起左手和苏芙蓉的右手重重相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