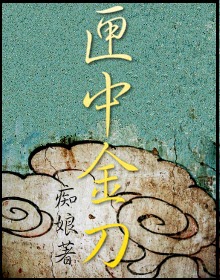笑解金刀-第2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有几句话爷要问问你。”姓帅的附在她耳边上说:“或许还要你帮上个小忙……
当然,事情成了,还要重重地谢你。”
“真的——”小鹤睁大了眼睛问:“啥事儿呀?您说吧,只要能帮上忙的,一定帮。”
“小声点!”姓帅的摸了一下下巴,向着凭舷面水的公子锦看了一眼,声音越加的小:“刚才跟你说话的那个人,真是你的老相好?”
“你是说他?”
“别指!”姓帅的赶忙压住了她的手,又为小鹤机灵地抽了出去。
“对啦!”他说:“他是干什么的?”
小鹤说:“你是问杨大爷?”
“他姓杨?”姓帅的脸上带着怀疑:“你没弄错?我是说……他真的姓杨?”
“当然没错。”小鹤说:“杨大爷是干绸缎生意的,买卖可大啦,有钱着呢?”
姓帅的“嗯!”了一声,半天没有吭气儿。
“咦——帅大爷!”小鹤好奇地问:“你问他干嘛呀?你们认识?”
姓帅的说:“你就别问了,姑娘——你帮我个忙,把这姓杨的在扬州的地方摸清楚了,告诉我——”
嘴里说着,手势前送,又是一锭银子送了过来,小鹤照收不误,一时眉开眼笑。
“那还不简单?我现在就告诉你。”
“啊——你已知道了?”
小鹤点点头,小声地说:“城南有一家福庆坊绸缎庄,你可知道?”
姓帅的愣了一下,说:“当然知道,怎么,这个姓杨的竟住在那里?”
“对啦——他们是亲威……杨大爷每一回去苏州都住在那里!”
“你没有弄错?”
“当然不错!不信你现在就问他去?”
“不不不……”姓帅的冷冷地说:“他到底姓不姓杨,回头我们就知道了,这件事你不要跟他说,而且,我还要提醒你,这个人你还是少接近的好。”
徐小鹤一脸迷惘,莫名其妙的样子。
姓帅的哼了一声,笑了笑,站起来说:“没事儿——”又拍拍她的肩说:“相好的,咱们苏州见了!”便自晃晃悠悠地往一边去了。
公子锦在船上转了一圈儿,着实地注意了一下,徐小鹤曾说共有三个人在盯着自己,可是除了那个抽烟的老头以及方才与小鹤说话的那个马脸汉子之外,那第三个人到底在哪里?着实令他大感纳闷,看了半天也没有一点头绪,待要向徐小鹤暗中打听,却不想目光望处,小鹤已离开座位,又复与那个马脸汉子凑在一块,不时指点口上谈个不休。
旁人眼里自当是“婊子无情”,只以为徐小鹤这个妓女,在忽然搭上了马脸汉子这个新客人之后,立刻把公子锦这个老相好甩开一边,却也在情理之中。
此行公子锦使命重大,决计不能出任何差错,原来还有些担心自己人单势狐,万一遇见了强敌,或是众寡悬殊,有些力不从心,难得中途出现了徐小鹤,凭她的机智聪明,总能助自己一臂之力,倒是始料非及。
倚着船桅柱子,耳听着帆橹的欸乃声,虽说是日上三竿,却是就着和煦江风,丝毫也不觉得炎热,算计着还有些时候才可到达,公子锦干脆摒除杂念,闭上眼睛打上一个盹儿。
一阵哄笑声,却又把他由梦里惊醒。
渡船上人声嘈杂,爆笑如雷,原来是船途无聊,几个脚夫为打发时间,竟自摔起跤来。
一个黑壮的胖子,脱光了上身,只着一条短裤,胸脯上全是黑毛,正与两个骡夫扭在一团,虽是以一敌二,却毫无败象,反因力大无穷,把对方两个骡夫屡屡摔倒在船板上,发出沉重的砰砰声响,引逗着全船旅客不时爆发出叫好欢笑声音,热闹得紧。
公子锦转个身子,半倚船桅,还想继续再打个盹儿,目光掠处,却接触到一张满布皱纹的老脸,分明直逼眼帘,就在面前。一惊之下,忙自坐好了身子,顿时睡意全消。
“相公爷可要买花?白兰花,香啊——”
嘴里说着,这婆子面带笑容,把一束串好的白兰花,直送到公子锦面前。
一阵扑鼻清香,随着那婆子手中白兰花直袭过来,香得离奇,几令人不堪承受。公子锦心里一动,本能地即时闭住呼吸,同时右掌猝起,顺势以拒说:“干什么?”
老婆婆几乎站立不住,身子一晃,几乎坐了下来。
“哟!”
似乎是吃惊不小,老婆婆睁大了眼睛望着公子锦,半天才回复笑脸道:“相公爷,买一把花吧!”
公子锦摇摇头,不悦地道:“不要,不要,哪有男人家买花的?”
老婆婆咧嘴笑说:“买了给那位姑娘戴啊!”说着,向那边的徐小鹤看了一眼,原来二人先时的邂逅,打情骂俏,大家都看见了。
这么一说,公子锦倒不得不多看上这婆子几眼了。
实在是毫不起眼的一副卖相,总有六十好几近七十岁的年纪了,一件黑夏布褂子,挽着两只袖子,露出黑瘦黑瘦的一双胳臂,一头白发,乱草似地蓬着,身子既高又瘦,看上去却很硬朗。
这样的一个人,原是极其寻常。却因为公子锦心里机警,却也另有所见。
公子锦抬头再次打量对方,不期然便与这婆子的一对眸子迎在了一块——那却是震人心神的一霎。怎么也没有想到,眼前这个貌不惊人的卖花婆婆,竟然会凝聚着如此内烁力的目神,这一点,公子锦凭着自己精湛的内功,几乎一眼即可断定——
“是了,就是她了!”
现在他几乎可以完全断定,暗中监视自己的那第三个人就是她了。
也就在他忽然有些警觉的同时,一阵头晕目眩,使他几乎难以自持,随即使他顿时有所明悟,虽然他一上来千般小心仔细,亦不禁为对方所乘,百密一疏地着了对方的道儿。
那意思也就是说,对方婆子对自己弄了鬼——那一束白兰花里,必然埋设有诡诈勾当,多半是慑人心魄的迷幻薰香,使之混淆花香之内,使人淬然无防,一嗅之下,便着了道儿。
公子锦有此一悟,心知不妙,却不欲让对方婆子看出端倪,一面举手挥动,让对方走开,却把视线转向一边,不再向婆子多看一眼。
这一霎,公子锦调聚真神,提吸丹田,强自镇定,不使真力溃散,却是先时一嗅之下所中的“花毒”,极为强烈,虽然至微,却是花性强烈,几乎难以自恃,当场昏厥。
他心里明白,自己此刻虽未昏厥,当场不省人事,却也仅此而已,事实上全身疲软,举手不能,此时此刻若是对方老妇人甚或任何一人意欲加害自己,都简单之至,毫无对抗之可能。
卖花老婆婆似乎对于公子锦的未曾昏迷大惑不解,一副芒然不解神态,忽地身子一转,绕到了公子锦正面身前,睁着一双三角眼,目不转睛地向他看着。
“相公爷……你怎么啦?病了?”
说时脚步移动,试探着已逼近到公子锦身前站定,公子锦其时已完全确定,对方这个卖花的老婆婆必将不利于己,只是他此刻除了能虚张声势地睁着一双眼睛,表示他并没有昏迷之外,其它一无可为。
老婆婆似乎已由对方呆滞的面部表情里看出了所以,登时胆力大增。
这时全船旅客,为现场的摔跤角力所吸引,爆笑叫好之声,不绝于耳,谁也不曾注意到船角一隅,发生在公子锦身上的细小琐事。
卖花婆子嘴里怪笑着,俯身而近,就着公子锦耳边说:“相公爷,你这是怎么啦?”
嘴里说着,这婆子竟自探手向公子锦怀内摸去——却是就在这一霎,一缕细小的尖锐破空声直袭她脑后,力道之尖锐犀利,使这婆子不敢等闲视之,嘴里“啊”了一声,身子霍地向左侧方一个打转,疾若旋风般闪了开来。
那是一枚极为细小的竹签,或是人们用来剔牙的牙签吧!即使留神细看也难以看清。
卖花婆子自非等闲人物,一望之下即知道,对方发射暗器的这个人,必然具有非常杰出的身手,设非有极为精纯的内功造诣,万万难以施之于如此细小草芥物什,即所谓“落叶飞花,伤人于百步之外”。
老婆子心里的震惊,自是可以想知,却是此番震惊,也只能存诸内心而已,眼看着那小小竹签“嘶”地飞落船外江心,自是难以追寻。
卖花婆子即不愿显示其本来面目身份,便只能哑巴吃黄连心里有数而已。经此一来,自不能再向公子锦出手,却是暗中向自己出手的这人又是谁?
一船人乱糟糟的,正自围着两个摔跤的人笑闹得不可开交,老婆子把心一横,正侍第二次出手,向公子锦身边偎去,忽然,一根旱烟袋杆横出,拦住了她的去处。
“来,老婆婆,我买你的花,拿过来让我挑挑!”
——正是先时坐在高处的那个抽旱烟的老头儿。
卖花老婆子愣了一愣,赫赫笑了几声,一双三角眼,频频在眼前老头儿身上打转。
“老婆子真正有眼无珠了,怎么连谢老太爷在这里都没看见?失礼,失礼!”
老头儿徐徐地喷出了一口烟,转过身子来,一面咳嗽,慢慢蹁向一边。
卖花婆子跟上去,阴阳怪气地道:“怎么,今天是什么风,居然把你老人家也吹动了,老人家一向可好?”
谢老头就着江水“噗”的一声,吹出了烟蒂,脸上神色阴晴不定,鼻子里哼了一声,哈哈笑道:“怎么,卢九婆,你也要插上一脚?这可就太热闹了!”
卖花婆子一笑说:“这话怎么说?谢老太爷你倒是说说清楚呀!怎么你来得,我老婆子就来不得?”谢老头一面磕着烟袋杆子,却把双细长的眼睛不时瞟向坐着的公子锦,后者一举一动,全在他的观察之中。
“咱们是老交情了。”谢老头嘴角挂着不屑:“有几句话不得不奉劝你,这个烫手的山芋,只怕你接不下来。”
“那可也难说。”老婆子呵呵地笑了,露着一嘴黑牙道:“如果你谢老太爷不存心跟我过不去,我倒想要看看还有什么人敢挡在我前头?”
谢老头哼了一声,冷下脸道:“那你就等着瞧吧。”
冷冷一笑,他又接下去道:“别的不说,就这位正经主儿,也不是好打发的,哼哼——你以为你那‘春风断肠绝命香,天下至毒,无人不惧’一经中人必将人事不省,可以任你宰割?却是眼前如何?”
卢九婆神色一震,待要恃强,反唇相讥,不意目光转处,心里大大吃了一惊。
原来先时他认为己呈瘫痪的公子锦,此刻竟然不在原处,显然消失不见。
这一惊,顿使她大起恐慌,只以为是眼前谢老头故意弄的手脚,一时怒由心起,方自把脸色一沉,却是目光转处,公子锦赫然又自出现眼前。
却听得锣声连响,敢情是渡船已到了尽头,大家纷纷向船头拥进,人喧马嘶,鸡飞狗跳,一时乱作一团。
卢九婆顾不得再答理谢老头,径自向船头挤进,却是怎么也快不了,总有个人在前面挡着,好不容易挤上了岸,再看公子锦,早已不知去向,非但公子锦不知去向,便是先时和他在一起的那个风骚疑似娼妓的年轻风骚少女,甚至刚才与自己说话的那个谢老头儿,俱都不见踪影。
这个卢九婆在武林黑道上,并非是无名之辈,说起来也是响叮当的角色,想不到此番为图重利,破例向公子锦亲自出手,竟自弄得如此灰头土脸,居然近在眼前,伸手可及的人也会跟丢了,简直是笑话。
码头上到外都是人,乱成一片。
卢九婆越想越气,更不甘心,两只手分着人群,向外挤出,一眼看见公子锦与徐小鹤双双跨在驴背上,正自驰向郊道,心里一急,不由分说,双手着力之下,身边人如何当受得住?顿时冲撞倒地,乱了个唏哩哗啦。
老婆子急了,心里更惦记着怕谢老头儿抢在自己前头,一时连“武者”不轻易施展武功的禁忌也顾不得了,嘴里怪叫一声呼地腾身而起,直向着公子锦策骑处追去。
一连三数个起落飞纵,扑到眼前这片稀疏树林,算计着只要抄过树林那一头,便可赶在公子锦上路的小道前头,却是呼地一声,一个人由侧面纵出,不偏不倚,又自拦在了她前面。
高高的个头,阔肩膀,一条大辫子巨蛇也似地盘在脖子上。这个背影对卢九婆来说,应该是绝对不会陌生才是,忽然间使她记起来从刚才下船开始,便是这个家伙一直就拦在自己前头,几次三番地作梗,使自己不能快速追上去,现在又来了,这是存心找碴,简直是跟自己过不去嘛!
卢九婆“嘿”了一声,脚下一个抢步,双手顺水推舟,猛力的直向对方背后击去;同时十指张开,宛若钢钩,似推又抓,力道极是猛厉,显然是内功中颇具实力的“大鹰爪手”,卢九婆心恶对方过甚,恨不能一下子就要了他的命。
偏